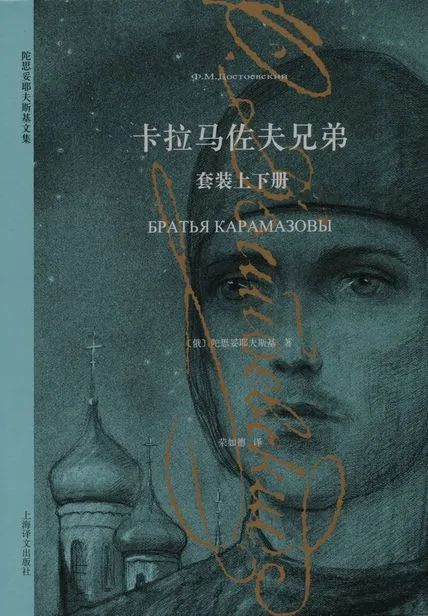有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人生就是一部奇崛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一个,他的一生是由奇妙而又生动的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活像是有人故意编造的,充满了诡异性、巧合性和奇幻性。他的人格、品性、思想、精神无不充满了矛盾。起码,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与他相类似的作家。
在生活中几乎很少有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女人不喜欢他那病态、凋萎的相貌,拘谨、猥琐的举止;房东不喜欢这个赖着不交房钱的房客;同行们不喜欢他那自负、各色、冷酷的性格;出版商不喜欢他急吼吼总要提前催要稿费的样子;斯拉夫主义保守派不喜欢他的高冷、故作斯文;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喜欢他对革命青年无端的嘲讽、谩骂;更有众多人把他当作一个痴癫的“圣愚”,甚至疯子。当我们把这些评价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更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的奇崛与各色、幽微与复杂。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
01.
将疾病当作一种感知工具
他出身在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所在的医院位于莫斯科最贫困的地区,是一个专门为穷人治病,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院。医院的旁边是一块墓地。这里埋葬的多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病亡者、流浪汉、自杀者、罪犯。墓地旁有一个弃婴所和一座疯人院。生活从一开始就揭开了其极其不幸与悲惨的一页,自幼始,灵与肉、生与死就成为作家思考一生的命题。深切的生命悲哀奠定了他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助推了他对生命存在的从未间断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个笃信宗教的双亲。《圣经·新约》《圣经·旧约》是母亲教他识字的读本,《旧约》中的《约伯记》更是让他终生难忘的故事。圣徒约伯敬畏上帝,毫无怨艾,忠诚不贰地接受上帝加予他的种种苦难的考验,感动了上帝,最终满足、幸福而死。
作家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读《约伯记》时,他每每会感到一种病态的愉悦,放下书后,常常要在房间里走上一小时,几乎要落下泪来。青少年时代,他还邂逅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宗教师长——漂泊四方、传播《圣经·福音书》的思想家兼诗人希德罗夫斯基,那是作家重要的宗教思想仓库之一,也是他的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梅思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中心人物阿廖沙的原型。
九岁那年,他跟随购置田产的父亲来到离莫斯科将近二百公里的图拉省。有一次,他在森林中迷了路,恍惚听到有“狼”的喊叫声,是一个正在耕地的农民庇护了他。这个名叫马列伊的农奴让他体验到了一个农民给予的温暖和热情。四十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单独的相遇,在一个荒僻的旷野,也许,只有上帝从天上看到了,素昧平生,一个粗鲁、野蛮无知的俄国农奴拥有如此深邃、开放的情感,充满了细腻的,几乎是母性的柔情。
世界上有一类伟大的思想家、作家,他们将疾病当作一种感知工具,用身体的痛苦将自己包裹起来,置身于“病态的精神弯隆之下”,审视经过他们思考、处理的现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与精神病患者尼采一样的思想家,与患哮喘病的普鲁斯特一样的文学家。几近失明让乔伊斯的听力大受裨益,他能听到像一枚海贝的黑暗的声音,而伴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癫痫病让他有了对生命幻觉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以至身体和灵魂常常会超越尘世的庸常,沉溺于无有休止的精神幻觉和灵魂思考之中。
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秘密聚会和公开诵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接下来是审讯,八个月后被判死刑,送上断头台。沙皇尼古拉一世精心设计、策划了一场旨在摧毁犯人心理的枪决,一名犯人当场精神失常。临刑前几分钟,才传来沙皇改判流放的诏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丝毫的慌乱,他把断头台看作“各各他山”——那个耶稣受刑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把赴死视作体验生命、死亡、灵魂永恒的一场宗教仪式。他说:“生命如同一颗落入泥土的麦粒,是不会死的,仍旧是一颗麦粒;若一旦死亡,那只会带来更多的果实。”
02.
人民远比贵族对自己、对世界有更多的希冀
在西伯利亚的四年苦役、六年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守护风中之烛一般,始终坚守着对生命和上帝的敬畏,未任那颗虔诚的心灵之光熄灭。途中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相遇,她们在道别时以《福音书》相赠的情景给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巨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十岁女孩对他说的一句充满怜悯的话也令他牢记终生:“不幸的人,收下这一个戈比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此间,他在流放犯中看到了崇高的人性,对俄罗斯人民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正如他在小说《死屋手记》中所写的,人民对上帝有着远比贵族、上流社会的人更多的虔诚,更多对自己、对世界的希冀。立足“乡土”,回归人民,回归东正教,实现沙皇、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和谐成为他最高的社会理想,成为他倡导的“根基主义”学说的要义。
1859年,结束了流放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在与兄长创办的月刊《时报》和《时代》中,他既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理念,又激烈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他自己的“根基主义”。
1862年的西欧之行让他看到了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世界,凸显了其生活的荒唐与残酷的一面,却也激发了他那赌徒的天性。
对轮盘赌的酷爱像顽癣一般真实,他长期沉溺其中,一次次地西去狂赌,甚至置患病的妻子于不顾。他每每债台高筑,甚至身无分文、食宿无若,以至不得不躲债逃离,生活的碎片被扔在了西欧的各个城市。在德国,他在向屠格涅夫借钱遭拒后,生活已无以为继,不得不屈辱地从一位出版社编辑那里借钱,条件是在三周内交出长篇小说,否则此前的一切书稿版权归这位编辑所有。我们在他的长篇小说《赌徒》中,可以真实地看到这样一个充满忧郁、焦虑,灵魂无法安放的人物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在巴黎
不过,在混合着颓废与反叛、平静与焦虑的双重精神中,生命的挣扎与对生活的思考同时在进行。
西欧之行还强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文明强调个性价值弊端的认知,更让他看到了上帝信仰失落给社会带来的精神和道德灾难。他意识到,与西欧资产阶级的自说自话截然相反,俄罗斯人民创造的近千年文化完整地保留了崇高的基督理想。他坚信俄罗斯人民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拯救世界、人类的弥赛亚使命的最终完成者。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普希金塑像落成的庆典仪式的发言中,也成为他晚年几部重要长篇的重要内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经验绝妙地融入了他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逼仄而又苦难的生存场与浓郁的宗教意识被他的个人经验重新编码,使他的小说成为被时代隐匿的人独特的精神存在史,一个宗教思想家不无碎片式的精神传记。
人们称我是心理主义小说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一个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意思是说,我描写的是人灵魂的每一个深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
03.
表现人间痛苦的现实主义艺术家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大师众多,才情禀赋不同,成就影响各异,但能称为“文学奇迹”的不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不仅有观念和思想的创新,还有艺术形式的创新。他始终都在营构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或者说,他一直在小说世界中找寻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基点,找寻创作生命全力追求的精神表现方式与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精神的诉求并将其作为小说表现的本体,是他悉心追求的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叙事模式。在这一方面,他的价值和意义是其他作家难以超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们称我是心理主义小说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一个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意思是说,我描写的是人灵魂的每一个深处。”这种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在文学所表现的对象和对人的认知上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重大的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再现外部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创作追求,他无意于揭示人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机制,不表现人是如何被社会扭曲、改造的,而是以呈现人的思想意识的全部真实,人灵魂最隐蔽的深处为叙事的对象,人的思想意识及其灵魂才是作家观察世界和展开叙事的最终目的和最终指向。作家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是在人身上对人的发现”。所以他说:“果戈理是直接拿来整体,而我却是通过辨别原子、探求整体走向深处的,因此果戈理没有我这样深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生命个体的人才是历史的根基、中心、全部的意义所在。个体的人是独有的、不可重复的,一个完整的肉与灵的世界,人的生命形态与走向是他自由、独立选择的结果。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神明,起码也要成为他自己精神的上帝。每个生命个体都对现实世界中的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人类命运的同一根链条捆绑在一起的。正是每一个生命进行时的个体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决定了人类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前行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是作家为人类提供观照社会的风俗演变和人的心灵变迁的最有效的方式。尽管他的艺术理念并非一成不变,但生命个体灵魂的展现和拯救始终是他小说创作的聚焦点。然而,他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又从来不停留在抽象的思想言说上,他从不让读者与他一起走进纯理性思辨或宗教神秘主义的桎格中,而总是把使他激动的信仰命题落实在世俗生活中,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纠结与争执、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勾连在一起。因此,他仍然是一个最贴近社会现实,零距离地接触生活本身,表现人间痛苦的现实主义艺术家。
04.
“俄罗斯的莎士比亚”,却写起了小说
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小说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张力,然而,他们往往又很难将对作家思想的理解、认知讲得很清楚。作品之所以令人着迷,读得艰难沉重,而又难以释怀,就是因为书里人物的心灵中有太多说不透的东西。作家笔下的人物充满了迷茫、忧伤、痛苦、悲哀,也有静谧、温暖、幸福、顿悟等各种情感,有十分丰富的潜意识活动,还不乏深邃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情怀。这就造就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世界的苍茫和浩大,遥远与幽深。
与普希金常常用诗进行文学思考的方式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思想一情感”来思维的。作家告诉我们,思想小说也能写得生动活泼、引人人胜、畅快淋漓。这得益于他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小说的叙事方式,突出表现在情节结构、时空观、人物构型这样三个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紧张、激烈、神秘、幽远的艺术氛围的营造首先得力于其非同寻常的情节结构。他的几乎乎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紧张、密实的情节,大量令人眼花缭乱、复杂多变的事件和场景扑面而来,呈现出一种多重故事并置、不同叙事者讲述并置的叙事形态。有时,小说会因为故事情节之间连续性、因果链的缺失,造成叙事显得暖味和不确定。
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长篇小说的章节标题就是形形色色的事件、场景、人物的奇观。“不合时宜的聚会”“在仆人房里”“预审”“错误的审判”“老丑角”“一根葱”“宗教大法官”“虔诚的乡下女人”“信仰不坚的太太”“野心勃勒的神学校学生”“色鬼”“无可争议的旧恋人”等等。这些章节标题因为言说具体、表达通俗,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标题的,却硬生生地被置于小说的起承转合之间,奠定了小说叙事的外部框架。
这种跳脱固有思维的安排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这种画面感十足的故事结构会反复召唤读者不断地从文本中跳出来,稍作停顿、思索,再返回情境中,引发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读者起初很难在一个个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找到相互之间有机的勾连,但借助小说的思想主题以及人物形象的连贯性,借助作者精心构筑、高潮迭起的中心情节和重要的艺术细节(如一粒即将脱落的纽扣、三千卢布的纸币…),才让暖昧和不确定的意义获得相对的完整。
《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荣如德译/2015-2
此外,情节的错乱性、尖锐性、极端性导致了其叙事意蕴的模煳性、复杂性和歧义性。
在《穷人》中,贵族贝科夫与瓦莲卡、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安娜·费奥德罗夫娜的关系始终是扑朔迷离的。作者似乎并不想把贝科夫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并不想让这个恶人的人性彻底沉沦。
在《罪与罚》中,一种思想可以点燃主人公杀人的意念,却无法使其犯罪行动合理化。作者在将人性的冷和恶揭示出来的同时,也把一种深藏在历史深处的哲学思想的邪恶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探长波尔菲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三次环环相扣的,心理角逐、意志较量的情节引人入胜,其白热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作者竭尽所能探究犯罪心理,考量罪与法、罪与罚关系的过程。
《卡拉马佐夫兄弟》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高度紧张、激烈的家庭纷争中,父亲费奥多尔与大儿子德米特里尖锐的冲突为弑父情节埋下了伏笔。随者伊凡、斯梅尔佳科夫的加入,事件的进展不断有犹如闪电、雷鸣般的高潮迭起。到底准是杀害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真正凶手?情节线索的交代并不明晰。“复仇”在逻辑上支撑了德米特里杀父的动机和欲念,但在价值域上又似乎缺乏充分的理由。
情节的吊诡还在于,是费奥多尔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在伊凡·卡拉马佐夫的怂恿下心生恶念,杀死了父亲,似乎弥补了德米特里复仇依据的不足,但德米特里又最终被错判而遭流放,斯梅尔佳科夫则以自我结束了罪恶的生命,用这样的方式实现了情节故事的终结。作家将一种悬疑小说的手法融人叙事中,将故事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展开,以追索的方式或解谜的结构揭开人物行为内在深刻的心理动因。
这样的情节结构,加上小说中大量的长篇对话,这样一些戏剧文本的核心要素,使得他的长篇小说拥有了戏剧小说的品格。文评界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的莎士比亚”,并非妄说。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甚至说:“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
小说家精心设计的时空观为意蕴空间的丰富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可以清晰辨析的线性时间的整体叙事格局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多维的、交叉的,甚至是无限的时空观。
作品的叙事时间被高度浓缩,空间则被大大凸显、强化了。《穷人》呈现的只是男女主人公五个半月里的书信往来。《罪与罚》中,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念头的萌生到小说结尾,主人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灵魂仟悔与精神顿悟,全部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系列紧张激烈、波诡云谲的家庭动乱就发生在两周之内。有限时间中大量空间场景的急速变化不断叠加着各种事件,推进故事的延展,在不断增强人物心理活动的剧烈性、紧张性的同时,也在不断生成新的思想意蕴。
05.
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个施难者,也是一个受难者
更值得指出的是,基督信仰的精神理想和宗教哲学的主题为小说确立了一个意义丰饶的人文空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全都被理性的思想所吞噬,一个个沉浸在理念之中。他们依赖思想为生,沉溺于一种封闭而自足的精神世界中。他们生存在地狱与天堂之间、反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这样逼仄的空间中。前者是一种世俗时空、危机时空,呈现出忙乱、急促、狂热、漩涡般变化的景象,是一种充满闹剧、悲剧的生存状态,而后者是一种信仰时空、永恒时空,呈现出一种静谧、安宁、愉悦的精神气象,与世界、他人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它们分别对应着一系列的象征意象,交织于人文时空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在杀死老太婆的前后,确立基督信仰前的状态,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动乱生活都是世俗时空的写照,蕴含着人物和家庭巨大的精神危机。它们对应着拥挤、封闭、黑暗的场域,如杂乱的居室、储藏室一样的阁楼、厨房中的一角,那不是家,而是一个让心灵的漂泊者感到压抑、空虚、痛苦,缺失信仰理想的空间存在。
梅思金公爵(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在癫痫病发作前的那一瞬间,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来到广场向上苍、世间认罪的那一刻,他在西伯利亚草原和河岸边向索尼娅祖露心声的当口,德米特里在阿廖沙(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面前忏悔的时刻,格鲁申卡在阿廖沙面前自我检视的那个画面,都是信仰时空的展现,具有象征意义。
此刻,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无法按秒、分、小时、日子的时间来称量,生命定格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的、美妙的永恒中。散亮的大厅、生气勃勃的人群、开阔的广场、灿烂的阳光、辽阔的草原、绵延的河流对应着那光芒永驻的精神信仰和生命理想。
崭新的人物构型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小说的又一个重大创新。作家彻底颠覆了人物的“身份”概念,打破了人物塑造正反、好坏的传统原则,确立了人物塑造的心灵、思想、情感、理性的原则,开拓了人物塑造的新的领域。正是一个个各具精神特质的人物为作家的思想表达提供了生命经验的支撑。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形象粗糙、面目不清、性格模煳、身份不明,却无不是高度独立,不受制于环境、他人意识的思想型人物。作家从人物形而上的思想深处和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人手,力图破解人物波澜的内心、驳杂的人性,那是由一系列充满悖论、病态的感受,对痛苦和不幸极度敏感的因素构成的灵魂,走近他们如同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深处。
他们留给读者不可磨灭印象的是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巨大的思想活力。他们被作者称作“悖论型人物”,或是“情欲型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中,赤贫者、孱弱者、癫痫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癫狂者,甚至罪犯占有很大的比重。因为在作者看来,他们拥有独特的心灵“优势”:他们或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或备受疾病的折磨、精神的磨难,或犯下严重的罪行,从而失去了感知世界整体性的能力。而恰恰因为如此,他们面对上帝信仰时却具有了特殊的直接性。他们无不站在自由选择界限的边缘,迈出的下一步只有两个方向:天堂或地狱,天使或魔鬼。这些人物既是生命个体的灵魂史,也是人类群体意义上的精神类型史。
俄罗斯大批评家艾亨瓦利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个施难者,也是一个受难者,俄罗斯文学的沙皇‘伊凡雷帝’,他以其言说和汗水建构的残酷的绞刑在绞杀着我们。”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异乎寻常、令人震撼的小说艺术的精髓也许就在于此。
本文摘编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
副标题: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作者:张建华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3-02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