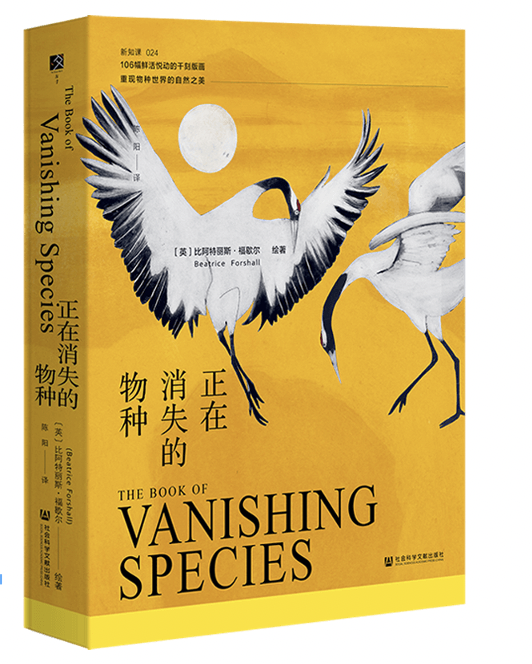考拉
幻梦时代,有个名叫库波尔(Koobor)的孤儿。他的族人对他很不好,不但总不给他水喝,最后还杀了他。他破碎的身体变成了一只考拉,只记得不多的几个人类词语。他警告杀害他的人:他们可以猎杀考拉,但绝不能在烹饪前剥去它的皮毛,如果触犯这一禁忌,就会引发可怕的旱灾。
数个世纪以来,这项禁忌一直保护着考拉,但到18世纪末,一个完全不了解库波尔禁忌的新民族踏上了这片土地:1919年,超过100万只考拉因皮毛而遭到猎杀。
考拉是澳大利亚的特有物种,是树袋熊科唯一存活至今的成员。考拉喜群居,但每只成年考拉都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往往与多只雌性的领地重叠。雄性考拉胸部的腺体会分泌一种气味浓郁的油脂,它们用胸部摩擦树干,以此标记领地范围。
考拉幼崽出生时没有毛发,没有视力,只有没剥壳的花生那么大。在气味和本能的指引下,它跌跌撞撞地爬过母亲的皮毛,钻进育儿袋里。它将在育儿袋内生活6个月。刚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时,它谨小慎微,紧紧跟在母亲身边,在母亲附近爬来爬去,学习如何爬树、如何通过气味辨别最可口的树叶。它们将鼻子凑在一起沟通信息。雌性考拉一般每隔一年产一只幼崽。
考拉的生存完全依赖于桉树林。桉树叶的营养并不丰富,所以它们必须大量进食,并一天休息18—20个小时。澳大利亚有超过600种桉树,但考拉只吃其中约30种。它们能分辨出营养最丰富的树叶和树木,而这些树叶和树木常常生长在人类偏爱的土地上。天气炎热时,考拉会肚皮朝下趴在树枝上,这能让体温下降 68% 之多。凭借这一特点,加之从桉树叶中摄取的水分,它们就不必频繁地从树上下来寻找水源:达鲁格人称它们为“古拉”(gula),意思是“没有水”,“考拉”(koala)一词便由此衍生而来。而这种动物的拉丁文学名的意思则是“灰色的、有口袋的熊”。
库波尔禁忌早在许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坏。20 世纪 70年代,气温开始上升,如今旱情越发严重,森林也更容易起火。在 2019 — 2020 年的那场火灾中,数万只考拉和数以亿计的其他动物受伤,或命丧火海。数百万吨二氧化碳被释放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桉树的生长速度加快,同时也使树叶更加缺乏营养。考拉无法通过进食更多树叶来弥补营养的缺失——它们的食量无法再扩大了。这是真正的危机:考拉可能因营养不良而逐渐消失。
截至 2012 年,澳大利亚砍伐了本国 40% 的森林和80% 的桉树林。尽管有 1999 年《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但如今,昆士兰州森林遭破坏的速度已是当初的 3 倍还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也不甘落后。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无垠的野火正沿北美西海岸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蔓延,同时也在阿尔及利亚、意大利、土耳其、希腊和西伯利亚燃烧。从卫星影像来看,浓烟已覆盖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并自有记录以来首次抵达北极。
亚洲象
在一片颜色灰暗驳杂的深色皮肤之间,澄澈的琥珀色眼睛闪闪发亮。这双眼睛形似树叶,眼周的肤色非常深,深到几乎看不见黑色的睫毛。褶皱和皱纹在眼周盘绕,之后便顺着躯干向下蔓延。
这头亚洲象的眼睛透过丛林纵横交错的枝叶向外凝望。它轻轻拍打耳朵,让流动的空气给血液降温。它转过头,摇摇摆摆地走下小径,4 条腿缓慢移动,显得十分端庄。
在它身后,是其家人们椭圆形的身影,体形大小不一,有的年少,有的年老。季风刚过,地面十分松软。它们的脚在潮湿的黏土里踩出深深的足印。水渗入足印坑中,形成微型池塘。数周之后,这些小池塘将成为蛙类的育儿所——这是它们在旱季的庇护所,没有鱼类等掠食者。大多数足印坑的周长不超过 60 厘米,深度也只有10 厘米,但已足够造就一个生态系统。象群沿路留下的足印坑让不同种群的蛙类能够找到彼此。
这些大象在森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将种子散播到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内,消化过程有助于种子发芽。它们最喜欢的水果之一是五桠果(别名象果)。大象采食树枝,推倒森林里的树木,为其他植物腾出空间,让光线得以穿透树冠,为小树提供生长的机会。
大象族群由雌性族长领导。雌亚洲象每4年左右才产下一胎,一次怀孕的孕期将近2年。幼象紧跟在母亲身边,它要跟随母亲生活好几年;而女儿们可能终其一生都留在母亲身边,比任何其他陆地哺乳动物都要长。整个家族会一起照料小象。
大象要花费许多年来学习。与虎鲸、某些鲸鱼、类人猿和人类相似,大象的大脑中也有在社会交际、情感和直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纺锤体神经元。大象是高度利他的动物,甚至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物种也十分无私。
大象可以感知到同类在32公里之外跺脚发出的振动。当一个象群遭到攻击时,其他象群也能感受到恐惧和痛苦。这或许可以解释亚洲象为什么拥有预知海啸的能力。为了让彼此感到安全和安心,它们会发出吱喳的叫声,用长鼻子温柔地抚摸彼此。紧密的社会关系意味着,家庭成员的惨死会给它们造成精神创伤。它们为死去的同类哀悼,用树枝和树叶盖住逝者的尸体,在尸体周围静默站立,并持续好几天。
有观点认为,大象大脑的化学组成与我们相似,因此,它们在失去至亲时也会承受和我们相似的创伤应激。它们拥抱或抚摸死者的骨头,对这些骨头表达敬意;小象宝宝用鼻子搂住死去的母亲的脖子,一连好几天都不肯离去。
为了捕捉年幼的大象,猎象人可能杀光它的母亲、姐妹和姨娘。在泰国,一只腿上拴着绳子的小象宝宝在棍棒的击打下,被人拖进一个宽度和高度都和它差不多的笼子里,造笼子的木头几乎和它的腿一样粗。年轻的男人们站在一旁围观。又有一些人加入其中,用尖头棍戳它的耳朵,猛击它敏感的长鼻子。一个人爬到笼子顶上,用一根形似冰镐的利器不停敲打它的头部,将尖端钻进小象的头骨。这就是被称为“精神摧毁”(Phajaan)的驯象过程,用饥饿、睡眠剥夺、干渴和疼痛——用刀和牛头刺刺激小象的敏感点——迫使年幼的动物服从人类指派的任务:让人骑在背上,进行马戏表演,或者供游客拍照。在“精神摧毁”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小象宝宝死于窒息或口渴,但有人相信,还有些小象是因心碎而死。在全球所有的亚洲象种群中,25%以上生活在人工饲养的环境里;其中许多都经历过“精神摧毁”的过程。
在亚洲象中,有象牙的个体远远少于它们的非洲近亲。尽管如此,买卖亚洲象其他身体部位(包括象鼻和阴茎)的贸易也在快速增长,这些身体部位可做药材。亚洲象和它们的幼崽被剥去外皮,脂肪被制成手串。偷猎者用含有杀虫剂的毒镖射杀大象,让它们在漫长的折磨中痛苦死去。
亚洲象如今的分布范围仅剩其历史范围的15%。它们生活的森林逐渐被人类的建筑和单一种植的椰子林、橡胶林、纸浆林和油棕林取代。所剩无几的森林也不断退化,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小片。大象族群遭到孤立。它们在水源和食物之间往来的古老小径被阻断。周围小片的森林不足以维持象群的生存,这让它们难免与农民发生冲突,而农民会杀死它们。在斯里兰卡的一个村庄,人们用歌声让大象远离村落,此举似乎颇有成效,但是其他村庄还在使用枪支、毒药、陷阱和装有炸药的南瓜——这会伤害大象的嘴巴,让它们饥饿而死。我们杀死了一部分象群、不断缩小它们的栖息地,这些做法让侥幸存活的大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让它们的出生率降低到了种群崩溃的水平。
正是如今的大象和猛犸象在象牙上的差异提醒了法国博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乔治· 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让他在1796年提出了“灭绝”的概念。但将这个新概念应用在18世纪的大象种群身上,对当年的居维叶来说一定是无稽之谈。即使对我们而言,虽然关于大象种群衰落的消息始终不断,但我们也很难接受“这种庞然大物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的想法,毕竟,这种动物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然而,自1950年以来,亚洲象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非洲象的数量更是减少了 95.5% 之多。它们是最后的食草巨兽。
来源:方寸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