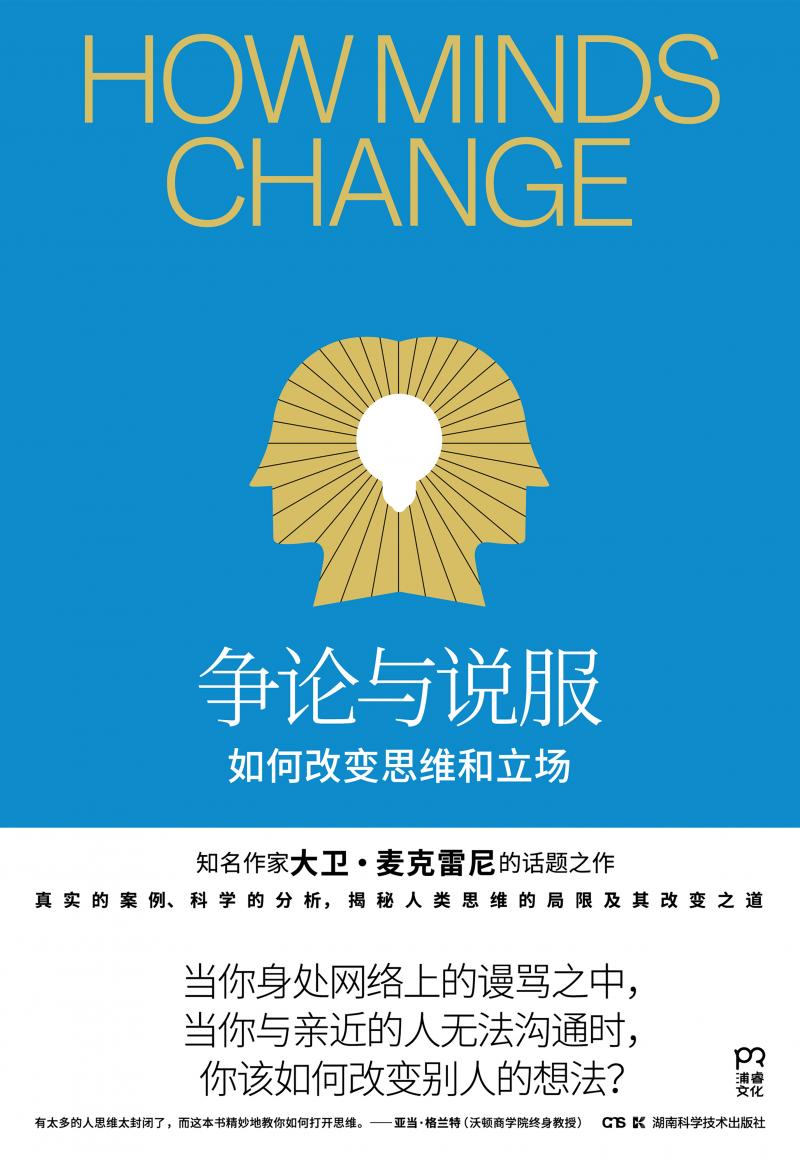到 20世纪80年代,关于说服的研究进展,说得轻一点,那是一团糟。
对影响力的心理学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焦点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都在研究纳粹是如何上台的,以及他们采用了什么策略来说服人们参与种族灭绝。
科学家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心智转向探索广告、营销和宣传的力量,其中许多人受雇于美国政府。尽管构建一个统一理论还需要 40 年的时间,但一旦心理学界意识到信念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心理结构,该理论的雏形就开始显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发现了态度的力量。当时,美国陆军委托好莱坞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拍摄一系列电影,以对抗德国的宣传攻势。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曾执导过《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和《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的卡普拉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重新入伍。作为“一战”的老兵,他在44 岁时被任命为少校,并受军方委派成立一个独立部门,负责制作影片,以期改变新兵在一些公共舆论问题上的想法,因为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这些想法可能会给战争带来负面影响。据初步估计,有超过 1200万美国人应征入伍,其中大多数是从未拿过枪的青少年。军方担心,到了战场,这些新兵还对果冻、汽车影院和车内热吻念念不忘,一旦思乡之情袭来,周围鲜血四溅,士气就会一落千丈。
凭借大量资金和一群被征召的社会科学家,卡普拉为军队摄制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电影,名为“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该系列电影的首部影片回顾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其中的说明性动画由迪士尼公司进行制作。摩西、穆罕默德、孔子,以及《宪法》中有关自由的语录在片中一一呈现,旁白解释道,这些思想如同黑暗中的灯塔,而纳粹正在努力扑灭全球的自由之火。接着,影片展现了纳粹的宣传场景:大规模集会、希特勒对民众的咆哮、步调整齐的兵队。这时,旁白道出,珍珠港事件并非你参军的原因。这才是我们战斗的原因。
这些影片还包含了一些信息,旨在消除普遍存在的误解,因为军方担心这些误解会破坏他们的努力。当时,美国的主流观点是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德军的规模小、军事实力薄弱。此外,大多数人还认为英国没有努力奋战,因此,在公共舆论看来,美国正漂洋过海、力挽狂澜。这些电影力图用事实纠正这些误解。例如,在描绘不列颠之战的场景中,他们展示了德国空军在战斗前的强大实力,以及英国在击退德军入侵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卡普拉强调了英国民众抗击纳粹的胆识和决心,也展现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形象。
美国陆军高层最初和大家想的一样,认为只要提供事实,人们就会改变看法。但是,当军方请来心理学家测试这些影片的影响时,与后来采用基于事实的方法来改变观点的心理学家一样,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这些电影在传达事实方面表现出色——不仅纠正了新兵的误解,也填补了他们知识上的空白——但是,一旦涉及观点问题,他们在看完电影后的回答几乎和之前没有区别。大多数人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哪怕 1 个百分点。
虽然“士气部门”的军官们情绪低落,但向他们传达这个消息的社会科学家们却喜出望外。他们意识到,信念与态度是不同的。
今天,心理学将信念定义为我们认为真实的命题。你越有信心,就越直观地认为某个信息与事实相符。相反,你越没有信心,就越认为某个信息是谬误。
然而,态度是一种评价光谱,包含从积极到消极的一切情感,在我们思考任何事物时都会产生。对于任何可以归类的事物,我们会评估它们的价值或重要性,而这种评估取决于态度对象显著时所引发的积极或消极情感。这些情感会让我们对态度对象产生吸引或排斥的感觉,进而影响我们的动机。最重要的是,态度是多元的。我们可能表达喜欢和赞成,也可能表达厌恶和反对,有时甚至产生两者皆有的矛盾情感。
总的来说,信念和态度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即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思想、问题和目标的层级结构。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态度”这个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科学术语,在核心的科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在那之前,大多数书籍都交替使用信念、态度、观点和价值观等术语。然而,认识到观点更受态度而非信念的影响,揭示了一块未被探索的全新领域。这促使对心理构造进行新的分类,并催生了“耶鲁传播与态度改变项目”(Yale Communications and Attitude Change Program)。该项目汇聚了研究“我们为何而战”的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旨在确定哪种信息会改变人们的思想。
随后的研究改变了整个心理学领域,很快,每所大学都在研究态度改变。然而,几十年过去,这些研究结果并未整合成一个宏大理论,尽管科学家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并产出了许多证据,但它们似乎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联系起来。在一种环境下有效的信息,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下无效;某个条件可能增强某些信息的影响力,但却削弱其他信息的影响力;某位演讲者的说辞可能让一群观众信服,但在另一群观众面前却不起作用。到了 1980 年,在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的重压下,态度改变研究似乎濒临崩溃。
但从 1984 年起,一个模型厘清了混乱的局面。两位心理学研究生理查德·佩蒂(Richard Petty)和约翰·卡西奥波(John Cacioppo)合作开发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最佳模型,名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用于解释人类是如何理解那些意图改变他们观点的信息并被其说服的。但他们开发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变心理学的进程,而是为了理解自己的教材内容,以便通过大学课程。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