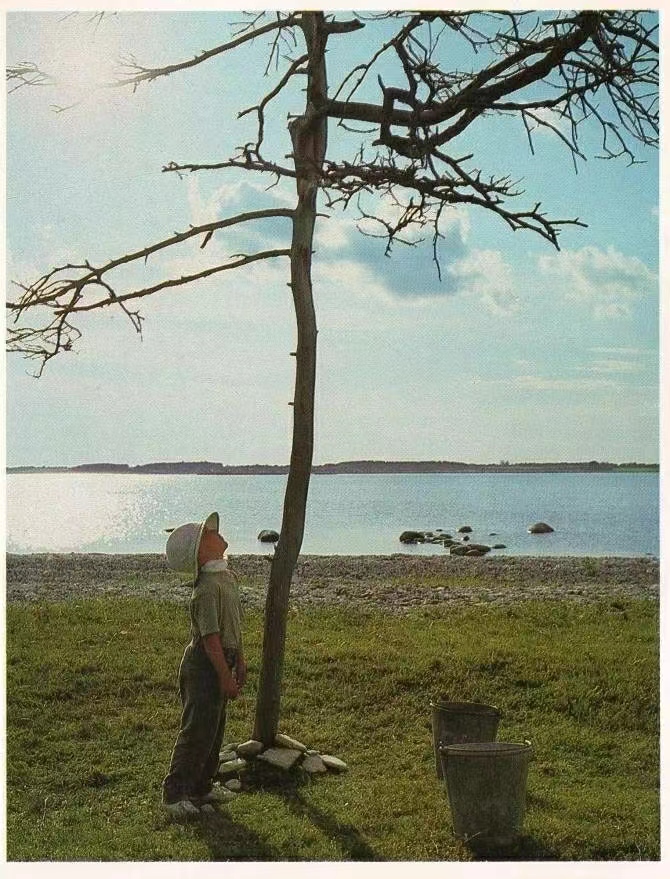
比《狗心》更乐观的《可怜的东西》
1925年,苏联作家米·布尔加科夫写了一篇小说《狗心》:医学教授将一个死去的流浪汉的脑垂体和睾丸移植到一只野狗的身上,不料实验的结果导致了狗的“人化”。狗不仅逐渐获得人形,还口出狂言,满嘴脏话,甚至开始攻击教授。最后教授不得已又将它还原成了野狗。
这篇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读者很难说清楚那些令人厌恶的品质是来自于“流氓无产者”还是“流浪狗”。比如,毫无羞耻感地告密、举报,对权力、财富毫不掩饰地追逐。讽刺的是,“人化”后的他竟然获得了“清理流浪动物科科长”的职务,并将这小小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因为识得几个字,就以为宣传册上的标语口号是自己的“理论武器”,而这武器只用来镇压除自己以外的人……
但这个故事中有一点常常被人忽略,那就是它也展示了一只流浪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苦情或苦难,以及作为一只狗的思想——它只会对苦难报以狂吠。恰恰是它在被改造成人之后,才学会了如此可恶。故事还潜藏着出身神职人员家庭的布尔加科夫对苦难的看法,即以人为神,并不能消弭苦难或不平等,且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欧格斯·兰斯莫斯的电影《可怜的东西》(2023)看起来则要乐观许多。虽然它改编自苏格兰著名作家(非常重量级的英语作家,但中文译介很少)阿拉斯代尔·格雷1992年发表的小说,但似乎很少有评论者提及他。倒是更多人乐于将这部影片直接对标19世纪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由此而来的电影衍生物《弗兰肯斯坦的新娘》(1935)。其实格雷的小说是不同的,里面没有那种哥特文学的气息:不是弗兰肯斯坦创造怪物,小说中的古德温本人就是科学实验造成的“怪物”。但他自己认为,这是科学的“必要之恶”。贝拉·巴克斯特也完全不是怪物,她显然是最健康的人。
《可怜的东西》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为背景,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期。兰斯莫斯读了小说原著后还专门去拜访了格雷——可以说导演和原作者有很多共识。作为一个哲学专业出身的导演,兰斯莫斯显然看中了作家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既离奇又真实(或者说,真实地写出了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悖谬处,反而显得有些荒诞感)的特点——这跟导演的创作(例如《龙虾》《狗牙》)是非常匹配的。而且格雷也是个画家、书籍装帧设计师,他的书都是“图文并茂”的,用文字和图像表达自己的思想。电影《可怜的东西》的视觉给人深刻的印象,其中也包括了作家本人的思想图像。
是否能靠“自由意志”拥有好的生活
那么,电影《可怜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思考”呢?鉴于和《龙虾》等前作的对比,我们当然也可以先入为主地“诛心”一下,认为兰斯莫斯现在有蹭女性主义流量,妄图从中获利的嫌疑。并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宠儿》的时候兰斯莫斯就有此遭遇。这样一来,“男性凝视”等指控也就成立了,特别是将它和《芭比》纳入同一个标准赛道,用关于“女性成长”的故事思维去理解它的时候。
但是假如事实并非如此呢?无论这位作家还是这位导演,都只能先将贝拉体验为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要知道,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可能只固守在自己的性别世界里,对立思维只会导致一种偏斜的判断。
这部作品首先要探讨的是“人”的问题。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科学决定论全胜的时代,大英帝国正是当时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老上帝早已没有了位置,科学已成为新的“神”,并且直接预言了20世纪的“人已死”。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天意”。或许我们可以说,这部作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取消了神的世界,我们是否能够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拥有好的生活?
显然作品提供了19世纪的几种主要思潮:“科学怪人”古德温(Godwin)即人僭越的神,他代表科学主义,也可以说是实证主义者,他不相信人有“灵魂”;邓肯是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者,他最接近于今日所谓的“最后的人”;将军显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哈利是怀疑主义-犬儒主义者;麦克斯代表依然存在的、相信有“灵魂”的基督教伦理。今日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也正是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贝拉·巴克斯特的“冒险”就是对他们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体验。然而,她在“冒险”之后,却发现只有“糖果和暴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女性的成长”,而是强者的生成
“可怜的东西”是什么?Poor我们可以有多种翻译:可怜、贫穷、可(怜)爱、贫乏。当然这里包括了对世界无边的苦难、受难者的同情、怜悯,但它总是指向一种因为他者的弱者地位而引发的情感。不过,对于被可怜者来说,这种情感未必是引人入胜的,相反可能相当令人不适。
对于古德温(上帝)来说,他最受不了的是别人看他的时候的同情。如果我们想到尼采的那句名言,“上帝死了,死于他的怜悯”的时候,就与这个“上帝”接驳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写道:“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同情者所做的蠢事更蠢的呢?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同情者的蠢事为害更大呢?一切有爱心者,如果没有达到超过同情的高度,那真是不幸!最近我听到魔鬼说这句话:“上帝死掉了;上帝死于他对世人的同情。”
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表达是很容易被误读的。他将人分成强者和弱者。强者体现了权力意志,他们创造、进取、勇敢、勇于承担;而弱者相反,他们胆小、保守、嫉妒心重、伪善。强者和弱者的区分并不在于财富或地位。传统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强调的是对弱者(因为他们遭遇苦难)的关怀,但尼采认为,“奴隶的道德”强调的谦卑和怜悯是弱者为了掩盖自己对强者的恐惧、嫉妒和自私。而“强者的道德”是鼓励创造、拒绝平庸、鄙视软弱。尼采的要义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反对将弱者的道德加诸强者。正是他预言了20世纪“奴隶的道德”之泛滥。
古德温(上帝)说,只有贝拉从未以怜悯的眼光看过他。这意味着,他明白贝拉是被创造出来的“强者”,这样的强者是不多见的。她具有先天条件,绝非弗兰肯斯坦用尸块拼接的怪人。她来自于自己的“母体”,也就是说,她自身正是一个“矩阵”(matrix),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女儿。强者的逻辑是肯定,是进取,是不断学习、提高自己,贝拉被设定为体现了这些特质——从强者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贝拉的“无知”,不然她的所作所为没法解释(当然导演的实际表达也似乎并未能令人满意)。
贝拉不是文学史上的“天真汉”或“白痴”。她被设定为有很强大的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因为她自己正是从苦难中重生。正如在船上,当哈利告诫她,不要相信宗教、社会思潮,因为人类这个物种“已经没救了”的时候,贝拉说:“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一个无法承受苦难的伤心小男孩。”哈利听罢低头承认。哈利尚且如此,邓肯就更不在话下了。贝拉的“冒险”,无论在里斯本还是巴黎,都不是“一个女性的成长”,而是一个强者的生成——她的冒险和“逆境中成长”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导演过多依赖了视觉奇观,以至于贝拉的精神内部没有得以充分展示。不过,“石头姐”艾玛·斯通的表演是好的。她本来就属于这样一类演员,她的脸,尤其是眼睛的表现很容易让人忘记她的身体,难以产生邪念。导演给了艾玛很多特写镜头,或许与蒙克的《呐喊》、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对屠杀中受难女性的处理有一些内在的联系——贝拉张大嘴巴的特写与前两者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一种“感人法”。不同的是,贝拉“无声的呐喊”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情境:对高潮带来的身体快乐的肯定,以及在亚历山大港目睹底层苦难的震惊所带来的怜悯。只不过这种怜悯不是廉价的,而是由感同身受带来的震惊。这种对他者的苦难感受与对自己的快感感受同等重要,构成了贝拉“强大”的基底。
她已经取代了“上帝”吗?
但是,影片进入巴黎的篇章之后,就逐渐走向了松散,“格调”一下子低了下来。按照原罪的观点,人性当中本来就有一种残忍的本质,或者说“恶”是本来就有的一面,无论强者还是弱者。
贝拉在开头的时候展现出破坏力,随手就把青蛙拍死——恶与苦难似乎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生活一起存在的。但为了好的生活,一个人应该具备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尽管我们是有限的、偶然的,但按照公元1世纪晚期斯多亚主义的说法,我们有“自由意志”,至少是一种潜在的自由的能力,让我们不受制于这个世界,并用这种方式来给予这个世界。当然,这需要我们不断进行“修炼”,就像歌德说的那样,才能获得智慧。
影片中汉娜·许古拉演的玛莎将歌德提供给了贝拉。贝拉的大脑因此迅速成熟,很快就能够用哲学来怼邓肯:你挡住了我的阳光——这是第欧根尼怼亚历山大大帝的名言。而唯有获得智慧,才能够识别出虚假的自由——邓肯和巴黎的鸨儿都用虚假的自由欺骗贝拉,但最终都被她识破了吗?导演其实没有给我们提供可信的证据。通过频繁地体验性爱,贝拉似乎也认识到身体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自由意志还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错误的信念中解放出来。
从理论上来说,“人都是可以改善的”——贝拉似乎也将此信条用于实践。但当最后对将军的“改善”是将羊脑换掉他的人脑之后,整个电影的味道变得暗黑了,出现一股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三联画《人间乐园》的“训诫”味道。虽然创作者可能带有几分幽默的意图,但是在这里,难道不意味着她已经取代了“上帝”吗?假如这就是“更好的生活”(或:Happy ending),那还真是有点令人泄气。
编辑 | 陈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