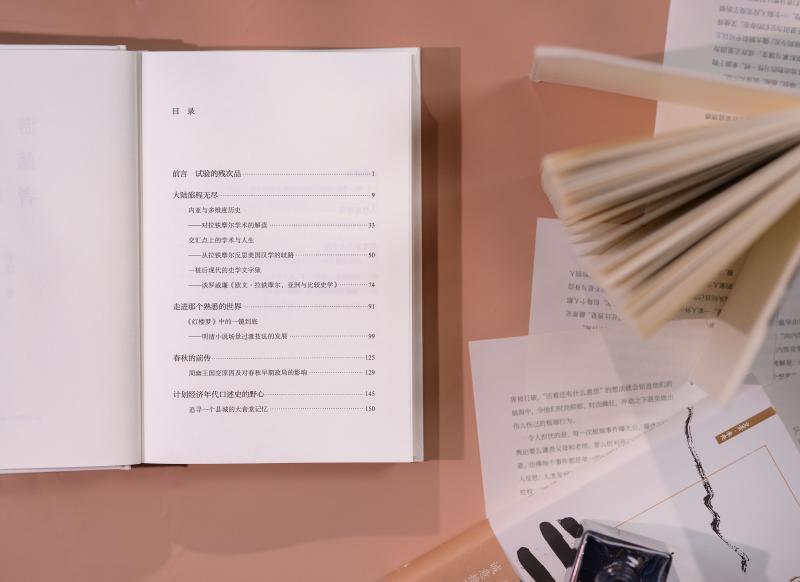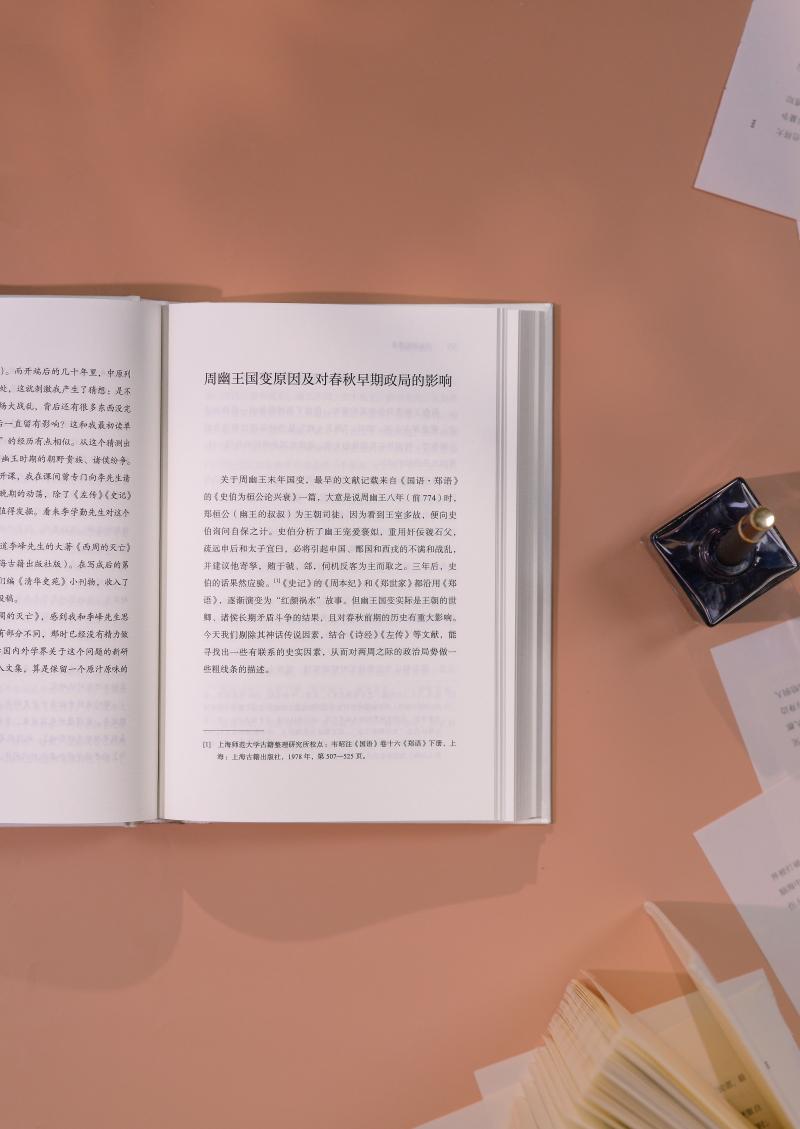2023年春,因病中断了巴基斯坦背包行走的学者李硕,在被医生宣布了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的情况下,回顾并整理了他自2005年以来思考并写作的文字,最终汇集成《历史的游荡者》,这本书近日由世纪文景出版发行。
2023年,因创作《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翦商》而被读者熟知的历史学者李硕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朋友们或陌生人……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了。目前有大学旧友们帮我料理生前身后事,一切完满具足,无劳挂念。”随即引发各界关注。在病中,李硕萌发了将自己过去二十余年里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编辑成书的想法。于是,有了这本名为《历史的游荡者》的自选集。
这本书收入的是李硕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他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在他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也不再收入本文集。)书中记录内容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东晋江南、华北蠡县、北魏洛阳、上古关中、玉门关外、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时代的不列颠;故事主角涵盖了帝王、贵族、士大夫、军官甚至“骗子”;涉及的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则包括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内容之庞杂,连李硕自己都感叹,“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简直是行为艺术啊!”“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李硕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文稿整理。
在书中,李硕用12篇导读来讲述自己的学术历程和酸甜苦辣。他觉得“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12篇导读也成为读者窥探李硕治学的一条路径。
此外,前言中李硕还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初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硕就被选入了文科实验班(“元培学院”前身)。这个实验班创办的目的,是破除学科壁垒,文、史、哲三系联合开课,学生自由选课。这段学习经历带给李硕两个影响:其一,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其二,“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
北大毕业后,李硕的工作也很杂。他依照自己的意愿,没有留校,也不回老家,而是南下。先在广州一家旅行社上班,后来进入深圳一家报社做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考上清华,正式接受历史研究训练,专业方向是中古历史。博士毕业后,他决定再次走出“象牙塔”,去西部地区游历。2013年,他赴新疆大学任教,利用假期,踏遍了少数民族聚集地……
李硕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他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前言中,李硕也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心得。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要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除了心得,还有“教训”。在一次读者交流中,有人问李硕,为什么能够这么奢侈,有条件到各处游历,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李硕回答:“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当时,他也披露自己四十多岁的人,没车,没房,存款也没多少。在《历史的游荡者》前言中,他评价自己的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附: “试验的残次品”
(《历史的游荡者》前言)
大约在2016年,曾有编辑朋友问我:是否考虑把单篇文章结集出书?我将当时已有的若干论文汇总起来,发现它们的主题过于分散、芜杂,涉及好几个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连归纳出一个书名都很困难。那位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于是编个集子的想法便搁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发急病,中断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国之后,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检测,会诊结果是已无手术可能,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
当时我想,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可以汇总成一本书。再看一遍这些论文的题目,感受却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简直是行为艺术啊!
也许,人之将死,看到的风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还有体能完成文稿整理。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收入的,是我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我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以及论文何时写作等等,涵盖了我从本科时代至今二十多年。所以这里就不再做流水账编年史式的罗列,只从“方法”上聊聊,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它们。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看书,想搞点关于人的“研究”,当然,那时看书条件太有限,只能是县城少年的自娱自乐。到1996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我想考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或社会学系,但不巧,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录里,这两个系都没有,斟酌一下,我觉得中文系离这两个专业还算近一点儿,于是就进了中文系。
开学报到几天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北大搞了个“文科综合试验班”,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都要学,这三个系的新生都可以报名。于是,我报名后参加了个小考试,好像有一段古文断句翻译,再写一篇作文。然后就进了文科试验班。
北大办文科试验班,我们是第三届,前两届都是保送生。到这第三届,有二十名保送的,还有十名是高考入学之后又考进去的。
后来听说,办文科试验班的创意来自季羡林先生。他说,现行的学科体制是模仿苏联而来,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们知识面都比较窄,当了学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学问。所以应该“打通文史哲”,号称要培养通才或“国学大师”,所以这个班也俗称“大师班”。
大学时候,时而遇到有人拿“大师班”打趣,或者羡慕。我解嘲说:大师都是基因突变出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出一个,怎么能像孵鸡一样,一窝孵出三十个?
文史哲三个系联合开课,其实也只是把三个系各自最基础的课程,像卤水拼盘一样放到课程表里,开课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培养所谓大师,和之前开课都是一样的讲法。
而对我来说,因为早早接触文史哲这几个学科,就觉得它们真没太明显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其他跟人相关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实质性的樊篱。因为研究作为社会人的人(而不是医学眼里作为生物活体的人),关注点、切入点都很接近。后来我做过文字记者,还曾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旅行,甚至尝试拍摄纪录片,其实都是对人、对人群的观察和记录。
简单说,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
我写的文字里面,可能缺少关于哲学方面的,其实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这还涉及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
西方哲学大都很抽象,制造和使用很生僻的术语,这风格也影响了有些周边学科,像文学理论、影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中,都有些学者喜欢用很专业的词汇,模仿西文句式写很长的句子,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够学术。但对西方哲学的历程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到20世纪他们也有反思,出现了“语言哲学”,专门研究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大词”能不能有效传达信息。
这方面影响我最深的,是所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它的大意是: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时,那些由少数人人为定义、制造出来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产生歧义,反倒是日常语言中使用越多的词汇,才越有生命力,传达意义越准确。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写东西就尽量使用日常语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学术词汇,而且尽量做个案的研究,用事例说明问题。
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算是“打通”。跨学科的通, 是一个维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和现实都要有点了解。陈寅恪书中常有“深思好学识古通今”之说,可能也是此意。
我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都是在读“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这也是本科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
本科时,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自己最近出的书,鼓励学生们去读。我们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钱志熙先生,有时到我们学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给我们一点指导。看到有同学在读本校老师的著作,钱先生说:“你们现在是本科阶段,还不应该读这个,应该读原典,读第一手的东西,把基础打好。”国学班的原典,就是四书五经、史书文献、经史子集等。当然,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中的原典,如《圣经》和希腊哲学对话录,等等。
钱先生这个告诫对我影响非常深。而且,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原典已经足够多,一个学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穷尽,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对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读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所以写出来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晚辈学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实可靠的想法和知识体系。如果没有对原典的直观理解,只读二手研究,很容易产生“误读”,甚至以讹传讹, 再写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三手”,除了引注的来源汇编,基本无价值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原典都问世几百上千年了,无数人研究过,我再读也读不出新想法,甚至读不进去,只能看现在大佬们流行谈什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阅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时代的新生活、新环境,这些亲身积累,都是我们阅读古籍原典的新“视角”,就像看一座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变了,视角变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就是文史之学能够常新的根源。
所以,关键就是自信一点,从自己已有的积累,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对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评的思维去审视。
关于这些治学的经验,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我就不多重复了。当然,严耕望先生治学的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思维严谨而专注,偏重史料的整理编排,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治学铺开的摊子也是不大不小,基本限定在一个领域之内。我思维比较发散,容易产生各个方向的联想,所以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风格的不同,不必强求一致,或者争论孰高孰低。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导读文字,也是解释我何以会想到那些问题,只要解释清楚,别人也容易理解。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的总结不正确,而是应该两者对照才会更深更全面。这些调研方法,其实前人已经有过很经典的总结文章,这里不多说。总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文史哲被称为人文学科,不算是科学,因为结论都很难验证真假。关于历史,现代人不可能穿越回去看看,而关于现实的论断,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如何衡量作品水平、价值的高低呢?我想过很多,但一直没形成答案,所以这里也不多涉及。
最后提醒一点,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些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我这里收入的论文,很多都没发表过,或者发表了也没变现出课题经费等实际利益,因为领域跨度太大,哪个圈子都不是,没空去拜码头、参与利益分配的排队。从这角度讲,季老“打通”的创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说时代变了。
病中力衰,诸事潦草,书中各篇论文,我多数没有精力重新审读修订一遍,这种工作别人也很难代劳,所以会存在很多错漏之处,希望读者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这部“二手”作品集子。
文/李硕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