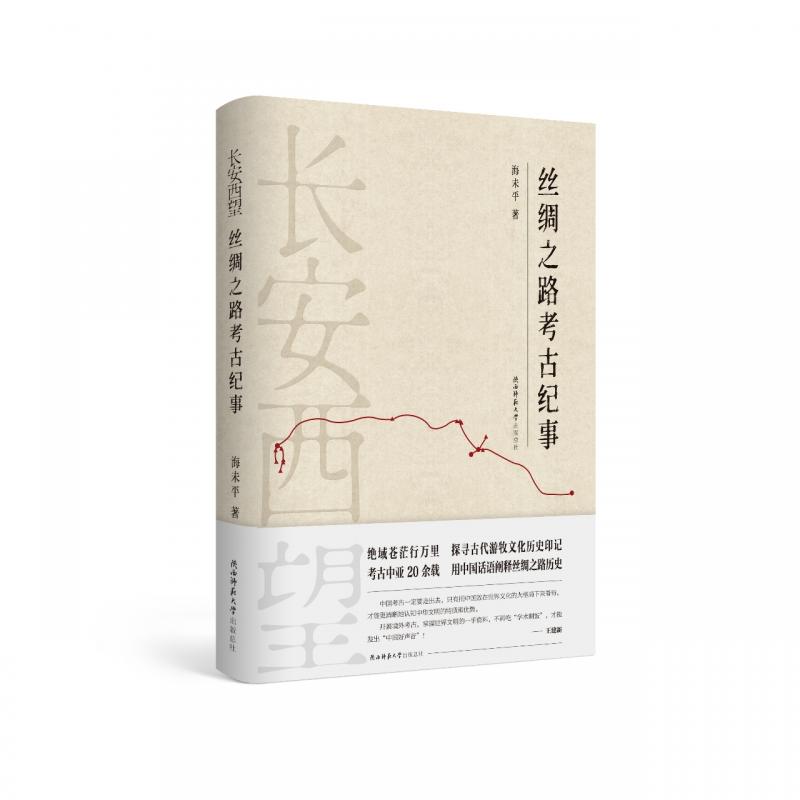2018年5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再次前往拜松的拉巴特村。
这次,考古队阵容庞大。中方人员有王建新、梁云、赵东月,博士生唐云鹏、李伟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斌、张如意,故宫博物院的吴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吴晨、赵兆,天水市博物馆的裴建陇,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秋实、李家杰,留学生苏荷、比龙;乌方人员有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塔力夫、萨纳特、拉赫莫夫、阿尔泽耶夫,铁尔梅兹大学的阿纳耶夫,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的哈米德加诺娃、索比洛夫。
王建新始终对拜松盆地炎热的夏天有所担忧,这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见过的洛阳生产的带轨伸缩大棚,这种大棚适合考古工地:早上可以把大棚收起来,只占很小的空间,等到中午再把大棚伸张开,遮挡阳光的暴晒。他决定为拉巴特考古工地购买安装这种大棚,这样大家就可以在阴凉下工作了。然而这件事情却大费周章,因为出口手续和运输出关等问题,一直到5月底,大棚才在工地上安装到位。
大棚遮住了阳光照射,却隔绝不了拜松盆地灼热的气温,大家依然挥汗如雨,但却无人叫苦。
这次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1号墓地的北部和西部,依然是大量的清理工作。考古工地上来了一位女孩子马娜,她是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二年级学生,利用暑假参加实习。活泼可爱的马娜像一只蜜蜂,在工地上飞来飞去,甜美的笑声让整个工地充满了欢乐。马娜非常聪慧,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了状态。刚开始,考古队的老师还要手把手地教她发掘,两天之后,她就能独当一面,负责清理一座墓葬了。她跪在墓坑边,专注而认真地用木签和刷子把板灰仔仔细细地清理出来,看见遗骸也不会尖叫害怕,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整理、清点文物时,马娜也毫不含糊,瞪大眼睛一个一个交接。梁云夸赞她,说这孩子是块搞考古的料。暑假很快结束了,马娜要返回学校了。考古队按规矩准备给她开工钱,但她坚决不要,说实习就是为了学习,跟中国老师学了很多学问,这比金子还要珍贵。
7月初的一天,考古队在一个墓葬中发现了五串胸饰,其中有玛瑙珠上百颗,还有斯芬克斯(人面狮身)形费昂斯吊坠。斯芬克斯形的饰品最早发源于古埃及,后来传播至中亚,再由中亚传播至欧亚草原,最远甚至传至我国北方地区,而费昂斯是最早的亮色彩釉陶制品。斯芬克斯形费昂斯吊坠出现在中亚,能够充分反映古代世界文明传播的路线、方式和文明交往的密切程度,因而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玛瑙串珠是古代极其珍贵的饰品,也是当代文物收藏家们热衷收集的宝物,在文物市场上价值连城。
这些饰品还没清理完,天已经黑了,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梁云无奈,只好用遮雨布将墓葬盖起来,将所有工作放到第二天完成。但他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安全是个问题,让他迟迟放心不下。
当时,考古队专门雇了一个强壮而憨厚的村民看护工地。这个村民对考古队很友好,白天会给大家端来茶水,聊上几句,考古队也经常从他们家采购一些酸奶,照顾他们的生计。离开工地的时候,梁云再三向这位村民交代,请他晚上多加小心,关照一下工地的安全,防止失窃。
回到驻地,梁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甚至觉得冰箱的嗡嗡声都比平时更吵。到了半夜,梁云总觉得会出事,便叫醒几个人,开车前往工地查看。工地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呼喊那位看护工地的村民,却无人应声。梁云一下子就慌了神,着急地说道:“怎么回事啊,看工地的人都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去查看那座墓葬,发现遮雨布完好如初,墓葬没有被刨动过,这才大出一口气,放下了心。
后来,梁云听穆塔力夫解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盗墓的恶俗,在他们的文化传统里,盗墓是犯忌讳的事情。这给梁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肃然起敬。
2018年7月,拉巴特墓地发掘工作正式结束,共发掘墓葬42座,算上2017年发掘的52座,总共发掘墓葬94座。
墓葬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厚。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石器、骨器、贝饰、费昂斯制品,以及铁剑、铁镞等武器,大小共计上千件。与周边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梁云他们判断,拉巴特遗址墓葬整体存在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这段时间正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崩溃至贵霜帝国建立的初期,也正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活动的时间段。
拉巴特遗址最关键的发现是墓葬的形制:所发掘的94座墓葬中,竖穴偏室墓59座,竖穴墓29座,因被破坏形制不明的6座。
根据出土文物推定,这些竖穴偏室墓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前期。梁云分析,“这个时期,在帕米尔以西、西天山以南、铁门关以东、阿姆河以北这一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已知遗址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巴特、阿伊尔塔姆墓地,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克陶、考库姆、图尔喀墓地及丹加拉的克希罗夫墓地。
“就出土文物来看,拉巴特墓地以束颈带耳壶或罐、高足杯等轮制陶器,无纽或具柄镜、缠丝耳环、喇叭形端口的手镯、凸起椭圆形戒面的戒指、 弧顶喇叭形铜铃等生活及装饰品,横栏格式铁短剑、三翼式带铤铁镞等武器,以及各种质地和形状的串饰为代表。
“就墓葬形式和葬俗来看,拉巴特墓地墓葬地表无封堆或有低平的石封堆,形制上流行偏洞室墓,洞室大多开在墓道的西侧,竖穴墓道往往填石或泥砖。如阿鲁克陶墓地,在发掘的111座该时期的墓中,偏洞室墓73座;在图尔喀墓地发掘的219座墓中,偏洞室墓183座。葬式绝大多数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这种文化遗存有自身的特征,与其他地区同时期文化区别明显,可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
王建新分析:“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与已知分布于伊犁河、楚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的塞人文化遗存没有关系,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
“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王建新最后推断,“我们认为该类游牧遗存的时空范围和文化面貌特征等与大月氏西迁的历史背景更加相合,应该就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遗存。”
王建新和梁云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拉巴特墓地的竖穴墓年代应该已经进入公元2世纪,为拉巴特墓地晚期遗存。对照竖穴偏室墓和竖穴墓的分布位置,他们发现,拉巴特遗址东部主要为竖穴偏室墓,西部主要为竖穴墓,埋葬的次序是从东往西,说明拉巴特遗址墓葬的形制和葬俗存在由竖穴偏室墓向竖穴墓演变的过程,晚期竖穴墓与平原区域的贵霜帝国早期地面龛式墓同时存在。
按照现有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能够推测,大月氏被击败之后,带领治下的各个部落迁徙至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这里,他们仍然沿袭山地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保持强大的武力,采用部落制和领有制统辖游牧人群和绿洲农业人群。他们很快接受了新栖息地的日常器物,但其社会组织体系的演化却需要更长时间,因而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这能够从拉巴特墓地的整体形制上管窥一二——从那种具有明显规划痕迹、存在某种秩序的墓地,以及墓主人随葬品的基本相似性所体现的身份等级相似性,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公共墓园。而墓葬中的武器,显示出武力对这个部落或者氏族的重要性。大月氏的不同部落抵达巴克特里亚地区之后,分散各地,依然延续了各自的包括葬俗在内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但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习俗却未必一致。
王建新和他的团队终于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城外的拉巴特遗址追到了大月氏的身影。这是一次跨越2000年的追寻:张骞用了13年时间,一路受尽磨难,充满艰辛;王建新则整整花去了18年时光,其间的磨难岂是一句艰辛能言尽,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才完全知道。现在,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回答当年的樋口龙康之问了,不仅如此,他和他的团队还完整地还原了公元1世纪前后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原貌,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做到这一步。
但是,他们的脚步并未停歇。在西方文献里,巴克特里亚的历史有一段“黑暗时代”: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灭亡直到贵霜帝国建立,时间长达100余年,没有文字记载,没有人知道发生过什么。而这正是大月氏统治巴克特里亚的时期。下一步,王建新将带领团队用考古研究复原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的历史,把“黑暗时代”的历史“空缺”填充起来。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好在,拉巴特遗址的发掘已经揭开了大月氏在中亚的面纱。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