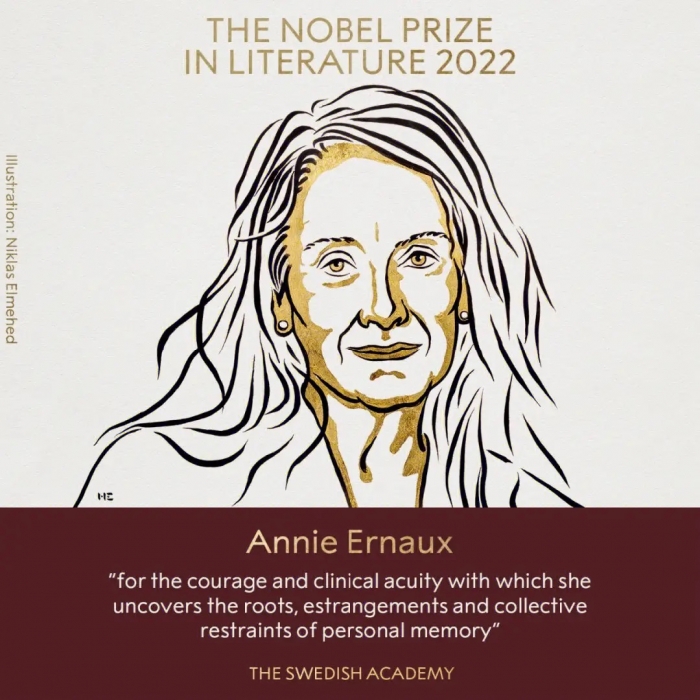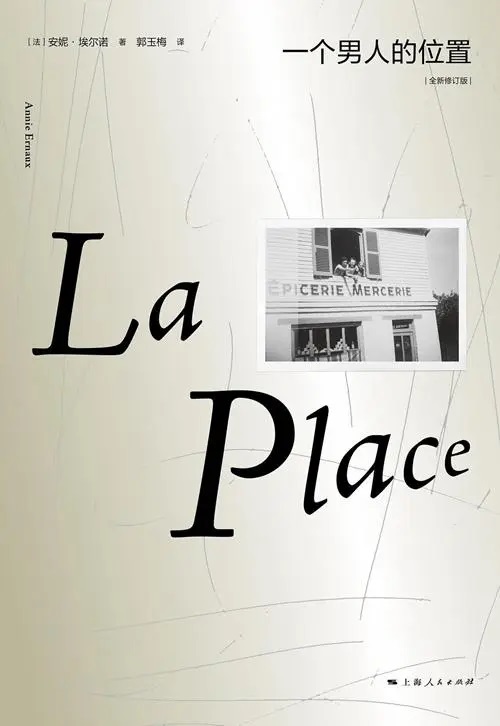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或许称之为小说并不精准)看似简单——它摒弃了大众认知中所谓的文学性的浮华表面,不再玩弄精巧繁复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一望即知是刻意的人为操控),不再燃放绚美华丽的比喻(除托尔斯泰外几乎少有作家能抗拒这种魅惑),没有高深的哲学性长篇大论或者争辩(这种段落被安插在小说中的效果通常都是很糟糕的,演变为令人生厌的说教,戳破小说的真实感)。在当代作家争先恐后地忙碌于炫技之时,安妮·埃尔诺反倒显得另类,她最好的作品像是与“生活”浑然一体——几乎就是生活本身。
极度自我的情感描述
安妮·埃尔诺的写作虽然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可简单被划分为两种类型。
类型之一是她对自己某种情感的解剖学般的描绘,重心在于心理与情感的分析,叙事几乎为零。她通过主动或者被动遭遇“符号”去引爆情感的炸弹,符号——包括某样物品与某件日常性的小事——仅仅只是情绪的舞台,情感不断被揉碎与淬炼。在某些时候,这种写法有着沦为一种简单话语版《恋人絮语》的危险倾向——或者说得更残酷一些,类似于阿兰·德波顿。但同样在某些时候,我们能对叙述者的受难记感同身受,像是作者握着读者的手同步跳着激烈情绪的探戈。
这种类型中我个人认为最佳的作品是《简单的激情》。在这部作品中,安妮·埃尔诺使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副文本”的技巧,即在小说中穿插作者自己的注释。在“正文”中,安妮·埃尔诺的写法犹如不断冲刷着海岸的波浪,这种自我情感的脉动包含着一种极度激情的血液翻涌,那是不顾留下伤痕的自我宣泄,看起来好像随时随地都会走向失控,所产生的感受是一种剧烈的即时性。但她的注释,冷静得像是另一个人,与正文拉开了距离,给人的感受是一个时过境迁的人对这段畸变的感情的镇定回顾。两种风格形成了对照,也形成了互补。
《简单的激情》令读者被震撼或者被打动的地方在于我们似乎随着她的文字在进行等幅震颤,其原因可能包括她抛弃了雕琢的词汇,例如形容词或者意象化的名词;也包括他人在小说中并非描写的重点对象,她所爱的人在小说中几乎也是一个符号,被悬置起来,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缺席比他的在场更加重要。作者无法让我们贴近他的内心,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地了解另一个人,就像在《简单的激情》尾声中所写的那样,“我只是用文字将关于他的存在,将只是通过他的存在带给我的东西还原出口”。叙述者置身于道德的禁区例如婚外恋,但她用一种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所有人都应该习以为常的事实的语调,用一个平淡叙述的语句交代出来。赋予浓墨重彩的永远是她自己的个人独舞,泛起涟漪的根源永远是自我的湖心。
当然,这种极度自我的写法带来的限制就是无法将作品写得太长,那会成为一种对读者的折磨,而非对这种痛苦的“享受”。说是享受,是因为安妮·埃尔诺带给了读者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用她的原话),情感不断地变化波动,但同时本质上又没有什么变化,像是被钟绳牵制的钟摆,只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运动。我们看着叙述者坠落于某种主流角度上非正常的情感迷网中,我们和她一起泥足深陷,一起经历这种风雨飘摇的不定状态。叙述者是情感的发起者与创造者,但同样她也是情感的奴隶与俘虏;她主动而被动(但一样的徒劳),叙述者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她的矛盾状态,而读者其实也共享着这份矛盾——我们一方面病态地沉溺于这种体验,某种程度上渴望它绵延下去;一方面我们又期盼着叙述者最终能解脱,期盼着这份畸形感情的消亡。而消亡,早有预示,作者自己所加的注释已然潜伏着结局的暗流。
深刻的日常性
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另一种类型虽然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但焦点则放在了另一个亲近的人身上,故事真正瞄准的是他/她者。故事的架构要比前一种稍稍丰满一些,但也仅仅只是水流般静静延伸漫流的细线,故事的进程几乎三言两语就能被概括。此类型的代表作当属《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本小说描述的是自己眼中与记忆中的母亲。这种独特的视角让她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就如布莱希特所言“他在他人中思考,他人通过他思考”。安妮·埃尔诺的文字栖息着一种奇妙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并不源于对细节细致入微的营造,叙事推进的步伐缓缓前进,同时又像是在拼贴着叙述者的记忆碎片。
以《一个女人的故事》中的那些讽刺语句为窥镜,我们发现,她的讽刺并不是一种掐着嗓子的尖酸刻薄,好像是随口一说。这些讽刺通常是一闪而过,绝不做过多的停留,仿佛一句轻声的抱怨——“我没有想到仪式如此简单,时间如此短暂,仿佛他带我们去见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无可挑剔罢了。”甚至于仿佛每个人经历的日常就是如此,“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这句话被夹杂在了一段客观描述行动的叙述中一笔带过。
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感受,那种惊人的深刻的日常性。说是日常,是因为在安妮·埃尔诺笔下好像全天下的母亲的经历与转变都和她母亲惊人的相似,其缘由其实在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越长大离母亲越远。说它深刻,则是因为那些发现、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其实早已被日常生活的尘埃所淹没,是安妮·埃尔诺将这些残砖败瓦挖掘出来,铺展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才能被震惊。小说中时常会有对照片的描写,在其他的小说比如《羞耻》中也常常出现,甚至于早期安妮·埃尔诺有一本小说就叫《相片之用》。当我们回首往昔时,记忆所遗留的只是一缕模糊不清的残影,有时我们仅仅只能幸运地,同时也是不幸地从照片的信息中拾起陈年往事的香灰。
同样,母亲和前一种类型小说的叙述者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只不过安妮·埃尔诺在这里使用的是相对客观的视角。比如她痛恨馥颂,因为它抢夺走了自己杂货店的生意。但当左派分子劫掠了巴黎的食品杂货店时,她又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她觉得馥颂只是经营比她规模大一些的杂货店。人物在矛盾中更加真实,甚至于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也同样诡异地矛盾着。女儿一直反抗母亲,但与此同时两者又有着延续性,她们同样有着孤独的本质,是“弃儿”,不被周边人所理解。即使这反抗也是一脉相承的,同样是对阶级牢笼的反抗与挣脱,同样是对自己母亲的反抗。
《一个女人的故事》如此的“现实主义”,因为当我们描述一个逝去的人时,巨细靡遗的临摹只能抵达一种虚假的真实,走马观花式的描写才是我们回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时思绪的真相。小说的结尾部分,安妮·埃尔诺剑指自己的文本本身:“我重新读了这本书的前几页。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已经忘记了某些细节。”但这种遗忘是写作的必然,所以无法再被改动——就像母亲死亡的必然一样无法改动。
纪录片般的死亡主题
死亡同样也是以悼亡父亲的“私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的重要主题。两本书同样以故事对象的葬礼为起点,同样行使着一种波澜不兴的语调,又同样在其中暗含了对葬礼一以贯之的不耐烦与暗讽。她所希望描述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所以她的书写作用之一就是从死亡的深海中打捞出被淹没的人。这是文学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但同时也是文学永恒的不可能完成的悖论。
《一个男人的位置》在描述父亲的时候有一种拼凑感与断裂感,语言被客观化、生活化,如同纪录片。小说的场景永远不脱离日常的经纬线,偶尔她会挑战我们对叙事变化的期盼,同时把情感圈定在一种非常节制的状态(这与第一种类型的情感风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父亲的棺材下降到墓穴时,一直不曾流泪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这一幕极度真实,但同时又有拐入情感溢出的危险。安妮·埃尔诺在后面睿智地添加了一句话“就像我出嫁那天做弥撒一样”,用与过去的对比将即将溢出的情感偷偷拉了回来。同样,小说开头和结尾的情节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在制造了疏离感的同时又隐隐给我们留下解读空间。
说到底,安妮·埃尔诺的目标可能是要实现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极端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她要让她的描述对象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质,恢复一个真实的人的状态;另一方面,她又想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和世间千千万万的人是同质的,他与我们一样有着相同的困惑、期盼以及情感。所以她才会使用这种迂回的手段,通过女儿的视角去追忆父亲。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天平的平衡,防止小说构筑的氛围突然坍塌——这就像拯救逝去之人一样是不可能抵达的目标。小说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就是“他越来越热爱生活了”。这句话出现在临近尾声的时刻(想象着你拿着这本书,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此书只剩下寥寥数页),我们才恍然发觉在这看似按部就班的进程中人物一直是变化的渐进的。父亲放弃了他曾经与之抗争的东西,反倒意外地与世界和自己和解,但同时他也越来越接近了死亡。
安妮·埃尔诺同样也抗拒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很快就没什么可写的了,我想放缓最后几页的进度,让这些书稿一直停留在我面前。”但书写与死亡不可能停止,最后,她是那么详尽又那么克制地描绘了父亲死亡前的情景,又以母亲那句轻轻的又在意料之中的话语“结束了”淡然而深邃的落幕。面对死亡,书写必然走向失败;但同时,书写的失败又是文学的成功。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