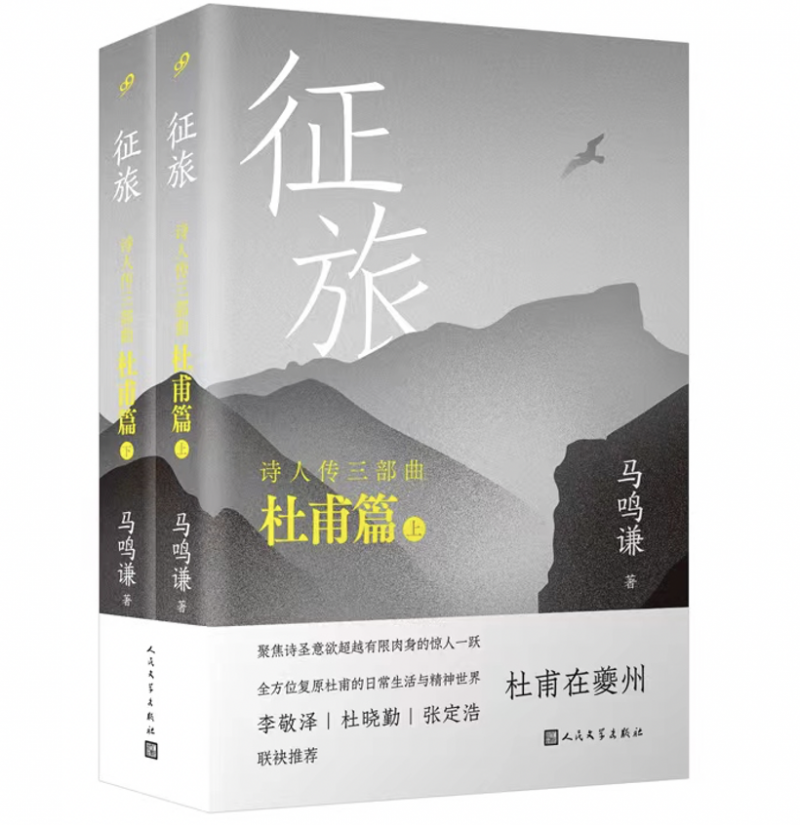终于要离云安了。
中午,王判官在官驿外亭设席饯行。因为消渴症发作的缘故,到云安后的半年里,杜甫已经断酒,故而对饮时只是约略沾唇、聊表心意而已。并没有旁人作陪,杜甫与王判官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着。晴日的气氛让他很想鼓舞起谈论的热情,可是,他却找不到太多话题来讲说,兜来兜去就是重复的几句表示谢忱的话。这位王判官年纪二十六、七岁,入仕时间不久,去年才调来云安。不过,他的从伯父却是夔州的当任刺史王崟。正是依托了这层关系,杜甫这次才下定了决心携家搬去夔州。
席间,王判官告知,夔州那边已有安排,杜员外一到州城,就可投递名刺到州府内。另外,云安县令严丹前日已去夔州例行述职,料想也已在刺史面提前做好了铺陈。
饯行过后,王判官要回县衙料理公务,还说明早倘若没有其他事情耽搁,定会来江岸送别。杜甫长揖拜谢,两人就在驿亭分别了。
午后登船时,江上无风,桅樯顶端指示风向的木鸦静止不动,那赤白两色圈点的鸟目直直地谛视着东方。两岸耸峻的山崖上未见厚积的云翳,只几片絮状的碎云停在半空。并没有下雨的迹象。
沙岸狭长,勾勒出弓曲蜿蜒的弧线,接近城门处向内凹进,形成了一个天然泊港。杜家的大舸就这样沐浴在斜照的日光中,静候在云安城下。此时的泊港里,除这艘预备下峡的船只,只有一艘荆州的上行商船正在卸下货物,十数个挑夫脚踩着两条长而柔韧的跳板正来回奔忙,不时传来船主催促的呼喝声。商船后面,另有三、四艘刚从益州 到来的白舫,船上的旅客结付了船钱,正指挥随行仆役搬运行李上岸。入晚前,他们必会找到投宿处,有正式官身的可以在官驿停歇,白衣平民则在邸店过宿。在杜家大舸和商船中间的开阔水面上,还浮着七八支土民艓子。这是形状如同长梭的小艇,尖尖的船头,尖尖的船尾,前后各有一人。船尾的那个坐着,不时翻动两片桨,谈说嬉笑;船头之人站立着,单手抓着渔网,却不言语,身后的木横杆上都栖立了一羽黑鱼鹰。不一会儿,随着尖锐的哨声响起,这些小艇仿佛约齐了似的,各各向江心飞驶而去。趁着日光尚且明亮,渔人们要捕捉顺流游下的成群白鱼。
沙岸再往西,原有一处激流回滩。去年初秋抵达云安前,杜甫已见识过滩水涨涌、波涛汹卷的可怖情状。不过,眼下还是三月,江面低落下很多,水流已不似那时湍急迅猛,从江心到对岸的半幅江面透出了浓酽的墨绿,望去竟然平展如镜。
杜甫由僚奴阿段引导搀扶着,拾级而下,踏上了自己的旅舟。
这艘船可不是寻常小艇,前年在蜀中时由梓州刺史章彝赠送,以前曾做过官船。虽然大小远不及旁邻那艘号称“万斛之舟”的商船,体量却比纯粹载客的白舫要宽绰许多。有前后三重舱室,前舱供休憩,中舱置行李,后舱供眠卧。三个舱室的船板下还有底舱,可以装载重物。
已提前招募雇佣了船工,舟前撑篙的篙工峡中人称为“长年”,掌舵的舵师称为“三老”。类似商船这样的大船须雇佣“长年”六人,“三老”两人,为八人配备。类似杜家这样的中船须雇佣“长年”二人,“三老”一人,为三人配备。在“三老”站立扶舵的望台下还有仆役的矮舱,那里可以安置厨灶。
三天前,仆人信行雇好船工后,已和阿段、女仆阿稽将整船清扫打理过。杜甫与王判官在驿亭告别时,临时雇佣的五名挑夫就开始往舟中搬运行李了。这次出峡旅途等于是将成都草堂的“旧家”不断整体搬移,身边长物可不少哩,挑夫们来回奔走了三次。
先是搬运米粮、舂米器具和厨灶碗碟。去年从成都带出的精米留存已不多,因为有员外郎的头衔,在云安还能领到禄米,禄米是糙米,因此舂米的石臼和木杵必不可少。另外,这次搬运可不要破损了大邑瓷碗。大邑碗白胜霜雪,扣之如玉,是轻而又坚的上好瓷器。那是初到成都时从涪城尉韦班那里索要来的。前年韦班返京后,听说又转任了河南尉,可是,劫后的洛阳满目疮痍,想来万事艰难吧。哦,远方的东都,不知几时才能回返,杜甫不由想念仁风里的二姑母故宅和自己的土娄庄和陆浑庄了。
第二趟搬运了家具、卧具、冬天用的暖炉还有衣物。家里人口多,衣箱就有十来个。乌皮几和书案也也带上了吧,还有两根桃竹杖(也是章彝赠送的)。杜甫每每想到桃竹杖,念及这位被严武当场击杀的刺史,心内总是唏嘘不已。章彝待自己可不薄啊。
第三趟搬运的全是书卷和文房笔砚。此前洛阳土娄庄留有两三千卷,旅食长安十年时贮藏的书卷数量有四、五千卷,此后乱离大半已失落,由秦州入蜀时只携带了小部分最珍爱的随身书,不及五百卷。不过,这几年在成都重又收聚,加上友人馈赠,目下也已有近二千卷。还有自己历年积累的诗文稿。惜乎保存在土娄庄的早年诗稿已散失,存留下来的也只有带去长安的十数首,以及凭记忆恢复的十数首,不及十分之一)。这些书卷文稿满满登登装了十几个箧箱,为防止行船打湿,箱上都蒙了油布遮盖。
从杜甫家寄住的水阁到南门泊港路途不远,夫人杨氏、长子宗文、二子宗文、二女杜堇都是徒步走来的。孩子们上了船,掩饰不住脸上的喜色,因为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坡陡地狭的山城,继续向前探索了。他们生性好奇,心里已在想象前方的州城和新的住所了。宗文在和船头两个“长年”攀谈,具体说些什么,杜甫却听不明白(这宗文什么时候竟学会了当地僚人的土话?)
到他登船时,所有行李物件已归置停当。杨氏和阿稽也已将卧舱里的被褥安顿完毕,今晚,全家人就要在郭外滩岸边的船上过夜了。预定明天一早就起航出发。
这是永泰二年 的晚春,三月十四日的傍晚。
晚食过后,明月跳出崖间,辉光晕染了夜空,照映着山城和船侧的江水,也照入了前舱。探身向外看去,那月亮已近乎满月了。
一家人早早就睡下,要为明日旅程养足精神。
到半夜时,船外传来了呼啸的风声,随后下起了雨。雨势渐渐增大,噼噼啪啪打在舱顶,杜甫被扰醒了来。这是峡中最后一场春雨吧,眼看初夏即将到来。夜风钻入了前舱门帘,将夜灯微小的火苗吹得摇曳不止。杜甫起身,让睡在前舱的阿段关合了舱门。
回到后舱,头重新枕上了瓷枕。合上眼睛,仍有残存的睡意。朦胧地听着雨声,朦胧地胡思乱想,到丑时三刻,却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了,杜甫披衣起身,来到了前舱。阿段身下铺了一条毡毯,靠着舱壁又酣睡着了。这个白日里精力旺盛的的少年,是多么容易沉入黑甜乡,令人羡慕的年纪!
过中舱时,他从油布盖裹的书箱里挑取了一卷,回坐到书案前,将油灯灯芯拨亮,披读起来。
恰好是《文选》二十六卷,于是翻至卷中,找到了陆士衡的《赴洛道中作》二首。读至其一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不由发一叹;读至尾联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再发一叹;待读至其二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一联和尾联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就不由长吁连短叹了。这一联李善有注: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赋曰,游心无垠,远思长想。不过,“振衣”注得不太佳妙,屈子《渔父》中早就说过了啊,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陆机将近五百年前的感发咏叹,正与自己类同无二。此刻,他的心神接通了前代古人,强烈感觉到诗文中所寄寓的那个秘密:古人、今人与后人,心地其实并没有分别,人世的经验原是层累叠加着的。他多年浸淫在《文选》的篇章中,很多段落都已记熟能诵,不料今次重读,竟读出了新的况味。
当年,陆士衡在孙吴亡国后被迫出仕西晋,他是从故乡华亭赴洛阳的途中。自己也设想出峡,至荆州转而北上襄阳,欲将回到洛阳,再赴长安。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按期归返。前年广德二年 入成都严武幕,出任了节度参谋,同时也得授工部员外郎的检校散官,可是,去年开春已辞幕,此后倘若不按期赴京通籍 吏部,期间朝廷也没有新的实职任命,那么,这检校郎官终究也只是挂名的虚衔而已。去年入峡后,因病滞留云安,半年来用药精心调养,身体状况已恢复,而眼看着两年期限很快就要来到。
实在有太多的顾虑,太多的不定之数了。去年接连发生了两件切身相关的大事:一是自己的友人、前宰相房琯因失势而被贬蜀中,放还回京途中在阆州不幸去世,紧接着,另一故人严武去岁亦在盛年故去,他在朝中已没有强有力的援手了。而因为滞留忠州、云安期间耗费较多,出峡北归的旅资已严重不足。
这前程未定的孤旅将如何展开呢?前方的夔州又会如何?想及此处,杜甫感觉郁闷之极。由夔州又想到了云安那位话语闲静的王判官。没有这位青年的热心助力,自己仍会困在云安不得出。于情于理,都是应该写点什么表示感谢的。赠诗予人,眼下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了。受人恩惠而表示礼敬感激,这也是儒家子应有的态度。
他定下心神,继续翻看这一卷。灯芯发出轻微的爆裂声,焰舌闪烁,连带了投在舱壁的影子也在跳跃。不知觉间,时间似已过去很久。待读到卷尾谢灵运那首《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至 莫辨百世后,安知千载前 一句,复又抿嘴而笑,想起天宝三载 与李太白同去王屋山访问华盖君的求仙往事。一晃已二十多年了哦,唉,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酒中仙”也已身故不在人世了。
搁下书卷,杜甫的心脑异常清醒,眼前却产生了幻觉:一时间,古人的语句,今人的语句,陆机的语句,谢灵运的语句,太白的语句,他自己的语句,所有的语句犹如海上潮汐般一齐涌来,倏忽淹没了他,倏忽又消隐去。他在灯火光里捕捉,在吟哦声中过滤。他的吟哦,其实只见嘴唇的微微翕动,几近无声而更似耳语。那边厢,阿段翻了个身,仍自打着轻鼾,外面的雨势已小,江水的流动声清晰可闻。
再回过头,重读了陆机那两首赴洛诗,杜甫就开始构想赠给王判官的诗作,吟得了起首一联,又想到此际仍在云安,大可在到达目的地后再作回顾。如此这般,又过了两刻多,早起的信行从后面矮舱来到了前舱,见家主已起身,赶忙唤醒了阿段。阿段揉着眼睛,跟在信行身后走出了舱室,他们要整理厨间与烧火,准备一家的早食了。
杜甫放下书卷,起身步出舱门,立在了船头。
雨几乎已经停了,三、四颗雨星拂上了头面。头顶,密集的雨云正奔涌散去,云层罅隙间露出了尤暗的冥空。峡江上升起了轻雾,东方已泛出淡白的曙色。
山城东向的崖间有寺院,此时,连续敲响的晨钟声穿透湿润的空气与微雨,传到了江岸边。团团雾气贴近了江面氤氲着,渐渐集聚起来,变得浓厚稠密。此时,一羽鸥鸟自雾影中飞出,越过桅檣,升上了高空。与它的躯身相比,那对完全展开的翅羽,有着惊人的宽度。
仰看鸥鸟在空中翱翔、盘旋,杜甫恍然忆起了成都的白鸥,忆起了草堂,忆起了当年的入蜀。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