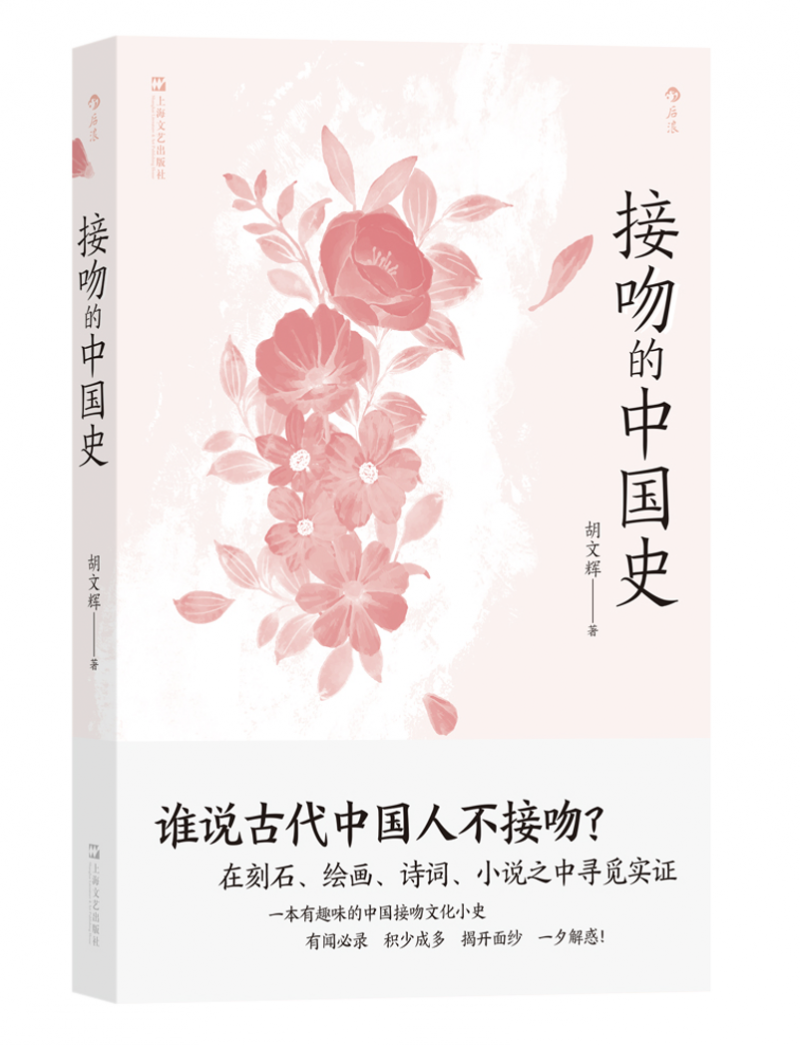众所周知,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军政上的西力东侵,也面临文化上的西潮东渐,真可谓“数千年未见之变局”。而中国人之接受西洋式接吻,当然也是这一历史浪潮造成的——只是这一历史浪潮中的一束浪花,虽甚炫人眼目,但也谈不上有多重要。
这一风气的转移,不可能是个别人登高一呼的结果,而必定是无数人的观察、无数人的尝试、无数人的模仿,才日渐造成的。
张德彝1866年(同治五年)游英时,偶然留下一个记录:
后上火轮车回寓,同车者有女子四人。或云西国有轻薄少年,如与女子共车过山洞时,当幽暗之区,彼以嘴啜自己手背作亲吻之声。路径通明,互相疑惑,而不知其亲吻者为谁。(《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2008年第2版,第517页;按:此承友人王丁提供)
这里并不是直接地描述接吻,只是记下了西洋“轻薄少年”假装与女子接吻的一种恶作剧,但显然张氏已了解英人接吻的一般习俗了。
又张氏1871年(同治十年)游法,也有一个记录:
见楼下经过一车,内坐一男一女。正驰骋间,女扶男腿,男捧女腮,大笑亲吻,殊向(欠?)雅相,亦风俗使然也。(《西学东渐记·游美洲日记·随使法国记·苏格兰游学指南》,岳麓书社2008年第2版,第433页;按:此承友人王丁提供)
这就是直接目击后的述闻了。
早期游历西方的人不必说,即使留心西方事物的人,也很容易注意到西洋人的这种习俗。如清末曾任驻槟榔屿副领事的印尼侨商张煜南,依据西洋图书的记载撰写杂事诗,其中有一首咏英伦云:
眼光一瞥□行人,回视朱门独立身。挑拨春心两相照,更加亲爱接香唇。(自注:女子在门首,过路男女嬉笑无忌,皆以口啜自己首[手?]背,如其意则接吻。)(《续海国咏事诗·英吉利》,《海国公余杂著》卷三;此据2005年广东梅州影印本)
这是说英国女子习惯接受男子的吻手礼,遇到自己喜爱的,更愿意与他接吻。
又如中日混血的苏曼殊曾译拜伦诗《答美人赠束发带诗》有云:
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相就不几时,何如此意长。(此据马以君笺注《苏曼殊诗集》,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226页;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下册第645页)
又苏曼殊的友人盛唐山民(葛循叔)亦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有云:
朱唇生异香,猥近侬情切。(此据《苏曼殊诗集》,第277页)
而苏曼殊在描写自己与日本情人百助接吻,就借鉴了拜伦的诗句,见其诗《水户观梅有寄》: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自注:此译摆伦“The dew I gather from thy lip”句。)(此据《苏曼殊诗集》,第80页;《苏曼殊文集》,上册第29页)
这里说的拜伦诗句,即前面所译的“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可见西洋咏接吻的诗,也用到东洋的接吻实践里来了。
即使完全未出国门者,也不难通过间接的介绍了解此俗。如1936年有署名左右的作品《时事杂咏·接吻节》,其诗并序云:
罗马尼亚民间,每年有一接吻节。是日凡新婚妇女,各摆葡萄酒,随其姑出游,相率聚于通衢。遇有行人经过,即奉酒一杯,听行人一吻而去。倘有却之不受者,则新妇家庭,认为大辱,必与此人理论,以是往往发生争执。又美国某乡村,每年于复活节后十四日,举行接吻节。是日村人集合一处,先行一种仪式,既毕,推选二青年男子,执花饰竹竿,游行全乡,向每户收取一辨士。其有迟疑者,或不予者,则二青年可向该户女自由接吻。因感其趣,乃为打油三首如次。
罗马尼亚事荒唐,吻遍娇娘不算狂。何惜牺牲一辨士,唇边赢得口脂香。
倘教道学骤闻之,一定含嗔以鼻嗤。那有许多林妹妹,哥哥嘴上拭胭脂。
颇闻妒妇作娇痴,索舌何须故吝之。莫是聊斋老居士,醉心欧化已多时。(孙爱霞整理《〈北洋画报〉诗词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下册第620—621页)
这里说,在罗马尼亚接吻节,新娘有与陌生男客亲吻的惯例;在美国某地接吻节,各户女子有以接吻代替交费的惯例。所述风俗不知是否准确,但与前述韦斯特马克所介绍的苏格兰、英格兰风俗颇为类似(《人类婚姻史》,第二卷第950—951页),应有来历。此类风俗的介绍,对于国人自然有开阔眼界、触动心理的作用。以这三首诗而论,其虽因域外旧民俗而作,但语境却针对此时此地,反映出西化时代大众对接吻问题的关注。从第一首“吻遍娇娘不算狂”“唇边赢得口脂香”这种句子来看,多少透露出一些艳羡的心理;而第三首“莫是聊斋老居士,醉心欧化已多时”,则表现出新旧过渡之际一种微妙的文化心理。这一作品发表时代虽已较晚,却也足以说明中西接触时代的普遍情形。
至于真正像西洋人那样的接吻,不难想象,留学生群体更有条件成为“饮头啖汤”者。张竞生在1910年代留法,其经验大约颇有代表性——其西式接吻经历,系发生在他与西洋女子之间:
我的第二次接吻,是在法国海边,对那位为我后来的情人施行的。这次不是在她颊上与在金丝发上亲吻,而是在她的口中,在她的唇中用极热烈的亲吻。那是“灵的接吻”,是接吻中达到艺术上的境界了。
以后的亲吻,不止是在唇间,在口中,而是在舌与舌的缠绕中!当我与爱人在伦敦时我须要用我舌与她舌互相纠缠中,长久不停地互相亲吻到好事毕后始休,到此灵肉一致得到满足。亲吻,成果始是达到最高峰。(《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下册;又见《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
不过约略同时,即北洋时代,中国本土或已开始有了公开接吻的风气。台湾掌故家伍稼青写过一则轶事:
方地山久居天津,一日与诸名流小饮于蜀通菜馆,众议招妓,时方中午,诸妓尚高卧,例罕应召。独某名士自诩招某妓必能到,且一见面即可“吃鱼”(谓可接吻)。飞笺之后,某妓果即至,某名士迎抱吻之。当时风尚,诸妓侍酒,仍颇矜持。突被拥吻,以为大失面子,竟怒掴之。
地山乃高诵孟子鱼我章句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合座狂笑。(《方地山高诵孟子鱼我章》,《拾趣续录》,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这是《世说新语》或《艺林散叶》式的名人轶事,细节未必准确,姑信其有。“某名士”要公开拥吻名妓,自然是西化的新派作风;不料名妓虽风尘中人,却仍守传统旧俗,羞于当众接吻,乃有怒掴名士之举。这很可见过渡时代的新旧冲突——不妨说,这是接吻问题上的白话与古文之争,或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争。
陶晶孙写到一个小笑话:
且说在我国,某小学教师读了英语书后,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我要体验一下接吻。”可是一试验却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即他突然意识到,四只鼻孔里出来的二氧化碳太有毒。(《烹斋杂笔》,《给日本的遗书》,曹亚辉、王华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这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一个教训,可见中国人学习西式接吻过程中的尴尬。这也仍是过渡时代的特征。
张宗和在自传体小说《烽火》里,写到未婚夫妻“初试云雨情”时,有这样的描述:
……首先她不会接吻,为了病,她不让他吻她,但家麟一再要求,见他诚心,她也就答应了,而且在家麟的教导下她也会主动把她的舌头伸到他口中,让他吮吸着,渐渐的她也享受到这种甜蜜的乐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女方这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大约也属于接吻西化过程中的常态吧。
偶尔见到三十年代一篇庐山游记有句比喻:
我生平总算没有和游泳池里的水亲过嘴的。这一回玩黄家坡,看看天然的游泳池,实在爱好不过……居然在水面顽过一回。(抱一《牯岭,避暑乎!趋炎乎!》,此据《〈论语〉文丛·东京花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亲过嘴”这个用语是传统的,但以接吻比拟亲密接触这种修辞作风,却应该是西化的。
我还见到一篇以接吻为主题的短小说:《一个可怖的接吻》(《永安月刊》第六十二期,民国三十三年七月;此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影印版第六册)。其情节大略说:一对男女婚后,因丈夫无能,女子出轨,而又悔其所为;为了证明自己对丈夫的爱,就在与出轨对象接吻时咬断他的舌头,将舌头带回去给丈夫看,而丈夫却难以接受她的残忍。这个情节,有点像前述褚人获《坚瓠集·广集》那个“因奸被啮其舌”的故事。不同的是,在这篇小说里,女主角不是在做爱时咬断对方舌头,只是在单纯接吻时咬断对方舌头,而且该女觉得此举能证明自己对丈夫的爱。这个故事似暗含了一个前提:接吻不等于性爱,故她利用接吻伤害对方并不算失身——这应该属于西洋式的接吻观了。
最后,且让我们看看张爱玲笔下的接吻。
在前些年始公布的遗作《小团圆》里,张爱玲借角色盛九莉与邵之雍,写了当年的自己与胡兰成,其中有这样一段:
有天晚上他临走,她站起来送他出去,他揿灭了烟蒂,双手按在她手臂上笑道:“眼镜拿掉它好不好?”
她笑着摘下眼镜。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
九莉想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是一只方方的舌尖立刻伸到她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他马上觉得她的反感,也就微笑着放了手。(《张爱玲全集·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46页)
“一个干燥的软木塞”这样的比喻,让人哑然失笑。这既显出她对前夫的冷眼,也显出她对自己的冷眼——也未必不是显出她对西式接吻的冷眼。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