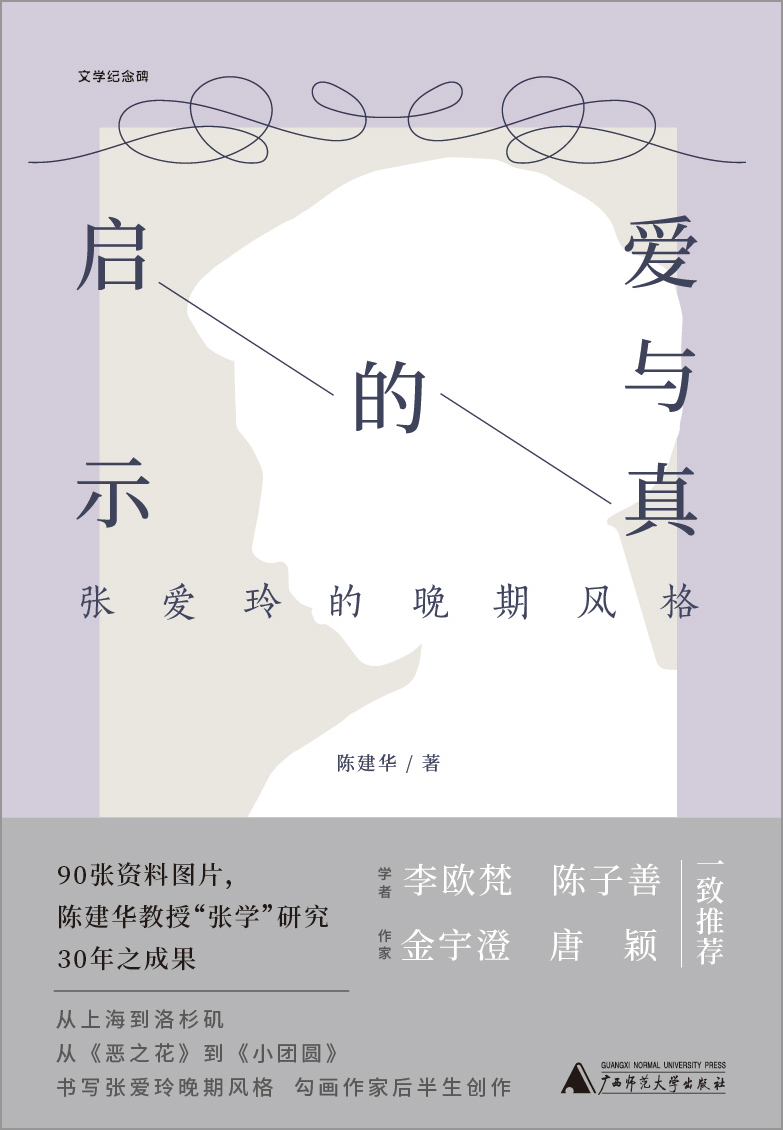张爱玲是传奇的天才女作家,是红学家,是“最后的贵族”。她出身名门,年少成名,后来移居美国,在写作了《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后,又在五十五时写下极具先锋性与现代性的《小团圆》,写“我自己的故事”,处理和清算那些“咬啮性的回忆”,可以视作张爱玲的自传性作品。但为表现复杂的人生,在《小团圆》中她用罗生门式的角度来讲故事,以变幻无常的视点编缀记忆的碎片,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有时显得扑朔迷离,给阅读带来困难。
复旦大学教授、文学研究学者陈建华所著的《爱与真的启示: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从上海到洛杉矶,从唐传奇到《恶之花》,在我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系谱中,呈现从《传奇》到《小团圆》的华丽苍凉。书中主要探讨了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创作体现的“晚期风格”。着重剖析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之后的二十余年里那种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书写。她的写作尊崇真实,徘徊于写实与超现实之间,既从我国古老记忆中汲取含蓄的诗学传统,也从西方现代主义中师法叙事手法,最终形成对现代精神的中式理解,以及其华丽为表、苍凉为里的书写范式。
在《小团圆》写作过程中,张爱玲不懈探寻内心的“真实”。小说以一个新旧交杂时代的乱世佳人为主体,主要围绕她与母亲、恋人的关系,以敏锐观察与自我审视描绘了她在没落贵族之家的感情成长史。作者以反叛的姿态揭示了家族中不堪的污秽、腐朽与堕落以及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甚至对母亲与自我的剖露均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而在她与风流才子的爱情遭遇中袒露其热狂与幻灭,在对复杂人性与自身软弱的省察中最终走向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之途。
《爱与真的启示: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陈建华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2-10
在文学中清算自己
关于她自己、她的家庭与家族,张爱玲确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这在她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已有明晦不一的表现。她出国之后曾向宋淇夫妇披露……之后写“我自己的故事”。确实如此,她写了《雷峰塔》与《易经》,与张爱玲从幼年到香港沦陷后回到上海的这一段历史相合。接下来写《少帅》,讲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罗曼史。经冯晞乾的考证,认为是张爱玲借以“影射”他与胡兰成的故事,因而把这三部小说看作“自传三部曲”,并指出:“七〇年代她写《小团圆》,坦荡荡讲她与胡兰成的故事,已经豁出去了。”这看法不乏灼见。张爱玲在《少帅》中大胆描写性爱,一变其淑女作风,大有“豁出去”之慨,而《少帅》是“历史小说”,将一些性爱描写几乎原貌搬到《小团圆》,既然张爱玲自认《小团圆》为自传,这不啻验明正身,更非同小可,何况《小团圆》并非仅仅针对胡兰成而作。
《小团圆》以“自传三部曲”为基础,若稍作比较,《雷峰塔》与《易经》大致平铺直叙,如艺术性资料长编,被改写到《小团圆》前半部分,至少被缩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怎么写《小团圆》?对张爱玲来说,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她都遇到极大的挑战。她自言“酝酿得实在太久了”。从时间上看,《少帅》在六十年代中写得断断续续,由于种种问题未能杀青。她在1975年10月16日致宋淇的信中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这说明《小团圆》的“酝酿”可谓旷日持久。又同年7月18日信中说:“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没有碍语。”此前已有成稿,却觉得“完全不能用”而另起炉灶。所谓“没有碍语”是说原稿还有所顾忌,现在完全放开了,可见“酝酿”的曲折过程。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碍语”?又何以自我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1971年6月即将移居洛杉矶之际与水晶的访谈中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引自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陈子善认为:“这段话或可看作更全面地理解《小团圆》的一把钥匙。”
“还债”意谓清算,通过写作还自己欠下的债,实即清算自己,文学上也银货两清。写作期间不断给宋淇写信,各封信虽是寥寥数语,却道及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如谈到写《小团圆》起因于胡兰成,“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又说:“《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按:充满震惊),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有像后来那样。”说明她摆脱了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怨情仇,更多写到她和母亲及姑姑的关系,不啻她的感情成长史和家族史。所谓“爱情故事”不限于与胡兰成的恋情,而包括亲情、友情的普泛之“爱”,充满复杂而令人惊悚的情节。又如:“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露的好。”事实上小说里对自己与他人的“揭露”的“不客气”程度完全超乎读者想象,彻底颠覆了她的既有形象。又谈到创作手法:“看过《流言》,一望而知里面有《私语》《烬余录》(港战)的内容,尽管是《罗生门》那样的角度不同。”
《私语》和《烬余录》是张爱玲最早的自传性作品,《流言》里另有一篇《自己的文章》,说她所尊奉的写作方法是“差参的对照”,借以表现复杂的人生。在《小团圆》中她用“罗生门那样的角度”来讲故事,以变幻无常的视点编缀记忆的碎片,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有时显得扑朔
迷离,给阅读带来困难。
总之,在《小团圆》写作过程中,她不懈探寻内心的“真实”,不断突破自己,终于打通情关,通体透明,毕其功于一役。小说以一个新旧交杂时代的乱世佳人为主体,主要围绕她与母亲、恋人的关系,以敏锐观察与自我审视描绘了她在没落贵族之家的感情成长史。作者以反叛的姿态揭示了家族中不堪的污秽、腐朽与堕落以及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甚至对母亲与自我的剖露均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而在她与风流才子的爱情遭遇中袒露其热狂与幻灭,在对复杂人性与自身软弱的省察中最终走向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之途。这部索隐体自传小说介于真实与虚构、具象与抽象之间,在“差参的对照”中糅合心理分析与自由联想,穿插藏闪与蒙太奇并置等表现手法,相对于作者早期错金镂彩、镜花水月的抒情风格,创造出一种开阔而深邃、清彻而硬朗的晚期风格。这是一种记忆书写的超前实践,一个富于中国“含蓄”美学的现代主义先锋文本。
《小团圆》“写得非常快”,可说是一气呵成。她已和《皇冠》与美国《世界日报》说好一俟完稿即同时连载,但在宋淇夫妇的劝告下未能兑现,被“雪藏”了三十三年之后方才面世。显然她在写作中不曾考虑小说的社会效应——诸如被胡兰成之流利用或自毁形象而遭到攻击等,当然会影响到皇冠与她的经济利益。然而为什么答应修改却始终未竟?为什么说要“销毁”却恋恋不舍且表示要和《对照记》一起面世?这些至今成谜,但有一点可确定:她当初如此专注于创作而未曾考虑到复杂的接受环境。或者说对她而言写《小团圆》含有回到自身与文学的双重意涵,它在“认识自己”的意义上臻至“白茫茫一片”的彻悟境界,替文学一次性清偿了债务。当然这个“文学”与经典传统是一体的,永远听到来自她内心的呼应。
有情有欲、灵肉合一的女人
回到自身,首先,也是最终——从身体出发。《小团圆》中的盛九莉是个有情有欲、灵肉合一的女人,小说人物同样富于七情六欲,在作者的记忆碎片中个个发出欲望的尖叫。这一点赋予这部传记小说永久的生命。“认识自己”的形而上探索必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正是在“真实”的拷问下张爱玲击碎重重心锁,还原一个货真价实的真身。其中情欲与性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对中国女作家而言已属稀有,更何况《小团圆》中“验明正身”的自我指涉,无疑具有文学史意义。比方说在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李清照的《点绛唇》一词描画少女情态:“见客入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遭到士大夫的抨击,如王灼的《碧鸡漫志》说:“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对于床笫之欢恣肆描写的以《金瓶梅词话》为最,时值晚明思想解放时代,在人的“自然之性”的新观念催生下,“人欲”从传统感情体系中分离出来而在文学前台作目眩心荡的表演。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为“民族寓言”所左右,从“鸳鸯蝴蝶派”到“五四”新文学皆遵循文明规训的典律,视《金瓶梅》式描写为禁脔。张爱玲在港大期间读过劳伦斯的《上流美妇人》,并摘取“他在美妇人的子宫里的时候一定很窘”这一句,不论她是否知道劳伦斯的作品对于社会习俗与保守观念的逆袭性冲击,在她笔下的性爱描写绝非庸俗,而是人性表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运用隐喻、象征意象等方面与劳伦斯有相通之处。
冯晞乾指出,张爱玲开始写《少帅》时,“女权运动开始席卷美国”,并认为受到其影响。其实不光是女权运动,以“要做爱,不要作战”(Make Love , Not War)为口号的反越战运动也风起云涌。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就写到有关“越战与反战”以及“现在学生性的革命”的情节。六十年代末张爱玲在伯克利加大,那里更是反主流学生运动的中心。尤其是从一九七八年发表的《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一文可见她在美国通过各种纸媒和电视节目对“新女权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注与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加剧了她的个人主义与性别意识。这方面不容忽视弗洛伊德的重要作用。对她的早期作品,夏志清早就指出“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也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确实如《心经》描写女孩的恋父情结,《沉香屑——第二炉香》表现中国家庭缺乏“性教育”而导致悲剧。再如本书第一篇所分析的“奇幻”小说等。这方面学者作了不少研究。张爱玲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驾轻就熟,但在那些故事里基本上是暗用的,《小团圆》里则一再明言“弗洛依德”,意味着她的情欲也随之浮出水面。一个前后对比的例子是:《小团圆》第九章写盛九莉去乡下找邵之雍,在村里听唱戏一段是根据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华丽缘》改写的,原文写戏台上“但看两人调情到热烈之际,那不怀好意的床帐便涌上前来”,在《小团圆》中变成“生旦只顾一唱一和,这床帐是个弗洛依德的象征,老在他们背后右方徘徊不去”。 这“弗洛依德”是性欲的代词。《小团圆》第七章写九莉怀疑之雍在汉中爱上了小康小姐,很郁闷。她心中想:“他是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于是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手搁在一颗棕榈树上,突出一环一环淡灰色树干特别长。沿着欹斜的树身一路望过去,海天一色,在耀眼的阳光里白茫茫的,挣不开眼睛。这梦一望而知是弗洛依德式的,与性有关。她没想到也是一种愿望,棕榈没有树枝。
“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这“枝干”指邵之雍移情别恋,另生“枝干”。梦中的“棕榈树”指涉男子的生育器官,而棕榈树没有“树枝”,合乎她的“砍掉他一个枝干”的“愿望”。弗洛伊德在其名著《梦的解析》中把梦境看作性欲的投影,张爱玲据此解读九莉的梦。《小团圆》中这类欲望语言比比皆是,第三章写九莉父亲从天津搬回上海,她母亲和姑姑也从欧洲回来了。有一段涉及家中的语言禁忌,跟性有关:
很不容易记得她父母都是过渡时代的人。她母亲这样新派,她不懂为什么不许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九莉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乐林”?她不肯说“快乐”,因为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此外还有“坏”字,有时候也忌,这倒不光是二婶,三姑也忌讳,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也是多年后才猜到大概与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新闻报》是一张大报,副刊“快活林”具鸳鸯蝴蝶派色彩,九莉的母亲与姑姑都喜欢看。“快活”会让人联想到性行为,因此她母亲把副刊叫“高兴”。这个例子反映出心理上的扭曲,这是日常发生的,所以“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不光“快活”,如“碰”“干”“坏”等词都是禁忌。尽管进入民国已有二十年,这个贵族之家在日常语言方面仍讲究文雅与体面,当然也包括旧时代的纲常礼教与规矩。令人警醒的是,她母亲与姑姑出过国,已经是“新派”女性,但回到家里仍旧照老一套生活。张爱玲说“她父母都是过渡时代的人”,含有一种历史意识与现代批评的视角,揭示了这一陈腐而令人窒息的家庭空间和她们的忍受或顺从的精神形态。
此时的九莉大约八九岁,开始思索、怀疑,且具反叛倾向。父亲教她背唐诗,而“她总是乘他在烟铺上竅着了的时候蹑手蹑脚进去,把书桌上那一大叠悄悄抽一本出来,看完了再去换”,“父亲买的小说有点黄色,虽然没明说,不大愿意她看”。上面说她“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家中缺乏性教育,九莉通过犯禁而达到自我启蒙。她自言在四岁时便有一种“怀疑一切的目光”,像个“小间谍”“在旁边冷眼观察大人的动静。我小时候可以算很早熟,虽然样子老实,大人的事我全知道。后来我把那些话说出来,拿姑姑和母亲都吓坏了”。 的确,日常而琐碎的细节描写触及感情成长中最为隐秘的角落,所体现的心灵禁锢、创伤与欢愉皆至为深刻,给记忆留下永久的痕迹,给读者别样的历史启迪。如九莉因在母亲处住了一晚,回家后因后母的责问而引起冲突,遂遭到父亲毒打与长达半年差点死去的禁闭。在幽禁的房里九莉发现弟弟给他的从堂兄的信中写道:“家姐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她一夜未归,在弟弟眼中好似做了下流的事,认为有玷家风。弟弟的糊涂想法说明其深受旧礼教的毒害,给她带来不小的伤害。后母责问她是因为事先没告诉父母,罪名是“不敬”。他父亲歇斯底里式狂怒则因为她先前向他提出过要跟母亲一块儿住,知道她一心要逃离这个家,而与后母直接对抗更是大逆不道。
半年幽禁之后九莉逃了出来,与母亲、姑姑一起住。《小团圆》写到有一天九莉在浴室里洗澡,母亲与姑姑在旁边议论她的身体,姑姑“不由得噗嗤一笑道:‘细高细高的——!’”母亲说:“也有一种,没成年的一种。”又说:“美术俱乐部也有这种模特儿。”九莉“是第一次听见她母亲卫护的口吻,竭力不露出喜色来”。母亲与姑姑的对白,眼神多于语言,九莉明白在两人眼中她已发育成人,母亲用“模特儿”作比方,她暗中高兴。这种日常偶然的细节被写进《小团圆》,对于九莉的成长史来说标志着一个象征性时刻。
让情欲开口,直面性,是张爱玲晚期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对于理解九莉与她母亲、邵之雍的关系也至关紧要。这一晚期风格的形成是跟她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有趣的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同“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之流相比,认为“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张爱玲确实看不上曼斯菲尔德,说她“已过时”,又说:“曼斯菲尔德小说,闺阁气相当重,她很‘清丽’——清得简直像水。”这是在五十年代之后说的,口气中含有不屑。“闺阁气”应当指描写闺阁小姐与体现淑女仪态的风格,其实张爱玲的许多早期小说也可归入“闺阁”之类。在这样的批评中已经隐含着她的风格的前后转变。她在前期小说中暗用弗洛伊德,对性事三缄其口,直至她在创作《易经》时仍然如此,而《小团圆》则突破了禁区。如写到杨露(《小团圆》中蕊秋)为她的侄女们介绍外国男朋友时说:“我听见她们说要嫁给高大的人,我自己倒是有点吃惊。”又挤眉弄眼地说:“冯先生不够大。嗳,女孩子家的说什么大不大的!”琵琶(《小团圆》中九莉)“听得摸不着头脑。要个高大的男人有什么秽亵的?”在《小团圆》里这一段被重写,琵琶的一句改为“听她的口气,‘高大’也秽亵,九莉当时不懂为什么——因为联想到性器官的大小”。另一处是母亲来到香港探望女儿,带她去浅水湾游泳时,从水中冒出母亲的英国男友,《易经》中琵琶“自觉看见了什么禁忌的画面,自动移开了视线”。 在《小团圆》中:“一撮黑头发黏贴在眉心,有些像白马额前拖着一撮黑鬃毛,有秽亵感,也许因为使人联想到阴毛。”在《易经》中用“秽亵”与“禁忌”,而《小团圆》中更为直白具体犹如R级影片,显然不宜于“闺阁”的“清丽”风格。
“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
无法回避的是《小团圆》的真实性问题。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夏志清等人的私聊可见,它无疑是一本自传,但采用小说写法,套用曾朴的《孽海花》,给每个人物使用化名。学者们对《小团圆》中的众多人名作了考索,指认盛九莉即张爱玲、邵之雍即胡兰成、卞蕊秋即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盛乃德即父亲张志沂、盛楚娣即姑姑张茂渊等,几乎无一不爽——颇如张爱玲自己从《孽海花》中读出她祖父母的浪漫传奇而深信不疑一样。夏志清建议她写祖父母与母亲的事,成为写《小团圆》的重要缘起。她说:“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这么说《小团圆》具有高度真实性,可当作自传看,但另一方面毕竟是小说,在张爱玲与盛九莉之间隔着层层厚薄不一的面纱,因此对书中所述的真实程度仍须抱一种审慎态度。
使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对书中人物作“本事”搜索可发现历史文本与小说描写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第四章写到“有个二〇年间走红的文人汤孤鹜又出来办杂志”的一段。汤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一九四三年张爱玲在他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先后刊登《沉香屑——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而声名鹊起。据周瘦鹃当时《写在紫罗兰前头》的叙事,张爱玲带着一封“岳渊老人”的介绍信去他家拜访,要跟他谈她的小说,他赶忙下楼,见到一位长身玉立的小姐站起向他鞠躬,然后见到她带来的小说稿子。两人谈了一个多钟头。周介绍了张如何在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及在香港念书快要毕业等,如一份简历。且写道:“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学法国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这应当是听张爱玲说的。一周之后她再度拜访,周说她的小说“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按:即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张听了“心悦神服”。周又记叙了在小说发表后应邀到张居住的公寓喝茶,见到了她的姑姑,也见到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文章与插图,“不由得深深佩服她的天才”。但在《小团圆》中仅说“九莉去投稿”,“汤孤鹜来信说稿子被采用了”,只字未提与汤的两次交谈,却津津乐道她姑姑对他的好奇和她母亲当年写信给他等事情,又说请汤孤鹜来家做客是姑姑的主意,“他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不激赏她的文字”。这么说令人诧异,也有点不公平,显然周瘦鹃对她推颂备至,说她的风格像毛姆,说她是“天才”,还是有点眼光的,而她也在其著述中再三提到毛姆,那么怎么看待《小团圆》的真实性呢?
我想最好把这部小说看作记忆之书,欲望之书。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我们不妨以其道还治之。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一书中对列奥纳多关于一只秃鹫落到他摇篮里的“童年记忆”作考察,指出这对他的性意识与艺术创作起关键作用,而这一“秃鹫幻想”“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今后的趋势服务”。 “今后的趋势”指后来生活中的心理趋势,包括意志与欲望等,记忆在重复中受到这种“趋势”
的制约,原初的映像被重构、被扭曲。其实弗洛伊德的看法——他的“杀父”“恋母”情结的说法另当别论——有助于理解一般的记忆现象。
若以此来看不断重写自己过去的张爱玲,似尤富启示。她自述:“我从来不故意追忆过去的事,有些事老是一次一次回来,所以记得。”《小团圆》中所“记得”的当属记忆中“老是一次一次回来”的事,然而在不断重复中难免走样,像《雷峰塔》与《易经》被大大压缩到《小团圆》中,哪些被筛选改写?又怎样改写?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的确,张爱玲在追忆中讨生活、还文债,也在不断“寻根”与重塑自我,由上述与《易经》对照的例子可见改写凸显了性欲,由此标志着晚期风格的特征,这其实跟她对“成熟”自我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可资参读的是《张爱玲私语录》中两段话:“我倒情愿中年,尤其是early middle age[中年初期](中国人算来是三十前后,外国人算起来迟得多,一直到五十几岁)人渐渐成熟,内心有一种Peace[宁静],是以前所不知道的。”张爱玲历尽沧桑,中年以后仍然流离颠沛,要获得内心的宁静,须有看透世事的睿智和坚强的意志。又说:“人年纪大了,就懂得跟许多不快的回忆(咬啮性的回忆)过活,而不致令平静的心境受太大干扰。”看来这“平静”来之不易,她内向而孤僻,自知不能摆脱梦魇般回忆,不得不学会与之和平共处而获得“平静”。她在五十五岁写《小团圆》,所处理的正是“咬啮性的回忆”,却使“平静”的水面上欲情四射、风波无限,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令人啧啧称奇。
回到有关周瘦鹃的回忆。本来《小团圆》以爱情为主题,详叙九莉与她母亲的爱恨纠缠的关系,而从姑姑口中知道她母亲“那时候想逃婚,写信给汤孤鹜”的秘密,遂引起她的追问。汤来她家作客,九莉还指给他看墙上母亲的照片。至于她的“投稿”只是个话题引子,不必尽道其详。尽管得到过周的提携,但在她眼中他是个旧派文人,1944年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声称自己不属新派也不属旧派,次年在《姑姑语录》中因姑姑喜欢讲“狠好”,张爱玲把她“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 这就表明她与周之间的代沟,当然包含文学品味上的差异。《小团圆》中说“有个二〇年间走红的文人汤孤鹜”,也有这层意思。明乎此,说汤“又不激赏她的文字”之句正是由于记忆的重复而产生了误差,而把话反过来说,无伤大雅地表达了她自己对周瘦鹃的疏离感。
《小团圆》书写记忆中的人和事,大多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具体细节如果与事实有出入,是由于记忆的误差或艺术虚构,而有些地方含心理依据,或是无意识欲望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一再提到弗洛伊德的“失口”概念,《对照记》中讲她一九五五年至美国在檀香山入境时,检查员把她的身高写错,于是她“不禁憎笑——有这样粗心大意的!五六寸半会写成六五寸半。其实是个Freudianslip(弗洛依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这个职员是个“瘦小的日裔青年”,大约被她的身高惊到了,这个“无意中”的“笔误”是否含有性的成分?跟“日裔”有关?跟“汉奸”胡兰成有关?她的带有惊叹号的“憎笑”一词分量不轻。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宋淇的信中说《小团圆》“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有像后来那样”。这在《小团圆》最后的第十二章里也出现过,九莉听到之雍说“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使她憎笑得要跳起来”。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聚,九莉终于明白之雍“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女人,始终做着“二美三美团圆”的美梦,而这“憎笑”意味着九莉最终放弃他的决心。
《对照记》是张爱玲的临终手势,书中对“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依德”倍加崇敬,对Freudianslip的一番解释显得郑重其事,难道是递给读者一个解读她的暗示?
文 | 陈建华
(节选自《爱与真的启示: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