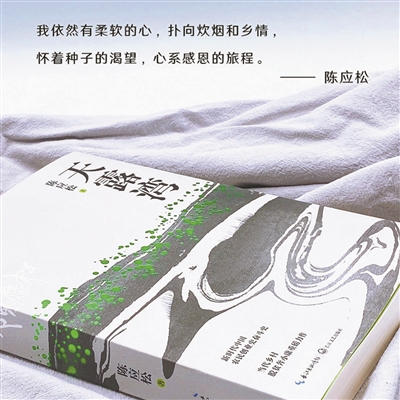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应松形容自己“拎着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在故乡的葡萄园里游弋”,在这种心绪之下,陈应松最新长篇小说《天露湾》今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天露湾》是陈应松的一部家乡之书,他说:“书写故乡是惶恐的,我从来没有为哺育我的故乡写这么长的文字,我小心谨慎,又大胆恣意。一个时代,一片土地,当她诞生神话和传说的时候,壮美的历史就开始了。我的笔,与他们命运相系,心心共鸣……”
《天露湾》首次书写故乡,是所有写作的一个异数
陈应松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100余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中国好书奖等重要奖项。《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等知名作品均出于他的笔下。而在《天露湾》中书写故乡,则是他的第一次。
在陈应松看来,农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术师。每年六七月间,他都会收到寄自故乡的葡萄,阳光玫瑰、浪漫红颜、甜蜜蓝宝石、藤稔、美人指……而他的故乡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原本是没有种葡萄的历史的,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几个农民尝试种葡萄,打破了长江以南不适合种葡萄的断言,改写了教科书。如今,葡萄已经成为陈应松家乡一个巨大的农业产业,公安县被称为“江南葡萄第一县”。“有一天,我坐在公安葡萄种植第一人老陈的家门口,品尝着这位‘甜蜜的挖掘者’种的葡萄,在他宽大的楼房前,看着浩荡的田野上闪光的大棚,以及在露天生长的碧绿葡萄,绿潮喧嚣,没有尽头。葡萄成熟的芳香甜味弥漫在这片我曾经劳动的土地上,农民在这个时代是多么伟大,他们创造了幸福,也创造了一个关于种植的神话。这片田野上诞生的浪漫和奇迹,是谁发现并发掘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获得了甜蜜的密码?江南不能种葡萄,但故乡的农民种出了,种成了,种好了,而且名满全国,这个关于土地的神话,有追溯的必要和书写的意义吗?我想试试。”
《天露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代背景,书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创业史,全景再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巨大变革历程。
陈应松2019年开始在公安县采访进行田野调查,“这之前,我在荆州挂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采访过他们,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真正动笔是2020年,在疫情期间我开始写这个小说,写了两年。这本小说的灵感来自家乡,也来自生活。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记录我们湖北江汉平原这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葡萄产业从无到有发展的历程。至于在田野调查和素材的准备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和感想,我其实都写进小说中了。一个作家,田野调查是他必备的能力,准备什么样的素材,完全要靠你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田野当中、到生活当中行走的人。我曾经说过,人是一株行走的植物。要说我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这些农民让我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在陈应松看来,《天露湾》是他所有写作的一个另类、一个异数:“第一,我是写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文坛立足的;第二,我过去的小说比较沉重,或多或少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第三,我过去的小说以神秘神奇和魔幻为读者所熟悉。但《天露湾》这部小说,是我对家乡的农民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所写,没有那些神秘魔幻,是以纯粹的、不走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四是,我过去写的多是高寒山区的贫困生活,现在我写的是富庶的平原水乡生活,小说的色彩和调子都与过去完全不同;五是,我过去从没有写过这种时间跨度三四十年的小说,这需要一定的技巧掌控;六是,这是一个真正正面书写农民形象和农村改革的小说;七是,在写作上完全口语化、生活化、地域化,力戒知识分子腔和小说翻译腔;八是,着力刻画人物,这部小说中有几十个人物,我争取都让他们各有性格,栩栩如生。”
对故乡的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倾诉的对象和通道
《天露湾》写到了两代人的奋斗,也写了众多的人物群像。陈应松表示,小说中的这些众多人物群像,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我不喜欢虚构。当然通过书写,把所有的原型和他们的特质放进一个主人公或者两个主人公身上,这是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表现能力和塑造能力。”
对于自己喜欢书中的哪位主人公,陈应松说:“如果说一位的话,就是金甜甜,说第二位的话,就是洪大江。金甜甜是一个任性的、单纯的、可爱的、善良的、美丽的女孩,但是她命运多舛。她的命运可能代表了那一代农村的独生子女的命运。因为父亲摔断了腿需要换关节,她放弃了高考,一个人到外面去打工挣钱为父亲治病,她碰上了好的老板,结果却在长江中遭受了船难,差一点失去了生命。她离不开救他的恩人,也就是公司老总乔汉桥,然后结婚。但是这位没有生育能力的老板良心发现,不想耽误她,希望她离开自己,可金甜甜已经离不开他了。最后就这样硬生生地被这位丈夫和老板强行撵走,离开了武汉,无家可归,重回了自己的家乡。她与自己儿时的好友、青梅竹马的同学最后走到了一起,再进行创业,种植葡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最后,她把曾经的婆婆接到她的葡萄园来养老,也就完成了对这个女孩、这个主人公的塑造,我自己认为是成功的,也在写作中为她流了不少泪。另外她后来的丈夫、同学洪大江的命运,也是令人动容的。”
陈应松自认是乡土作家,“我写了几十年乡村和自然,我的小说肯定是乡土小说。只不过,我过去主要是写神农架,写高山和森林。现在我回过头来书写我出生的水乡和平原,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哺,重新唤起我过去的记忆,重新回到故乡,书写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乡亲。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和应该承担的写作责任。我热爱农民和土地。通过这个小说的写作,我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和通道,所以写作真的是充满快乐的一件事。”
葡萄和家乡只是一个背景,想写两代农民的命运
陈应松记忆中的乡村曾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脸朝黄土背朝天和无休无止的劳作,挑粪、挖沟、锄草、插秧……没有一样不是繁重的苦力。但在《天露湾》里,落后的农民形象不复存在,读者可以看到的是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新农民形象。他以八个字来总结创作《天露湾》的心情:讴歌土地,赞美农民。也因此,在《天露湾》中,葡萄和家乡只是一个背景,陈应松更想写一群农民,写两代农民,写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他们奋勇拼搏、脱贫致富、可歌可泣的命运。
陈应松说自己2009年挂职期间发现,几乎一夜之间农村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再也不需要锄头、镰刀和耕牛了,不需要除草,也不需要插秧割谷,一切交给了机械。聪明的、精明的、有知识的农民崭露锋芒,现代的、先进的、时尚的新农村遍地开花。“过去说农民是落后的,但在我的家乡,葡萄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农业产业,恰恰说明现今的农民在这个时代不仅不落后,而且比我们想象得更加聪明和先进。时代就是这样,以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速度在进步着。”
在陈应松看来,农民的精神变化是巨大的,“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种所谓落后的阿Q式的农民形象,至少在我们江汉平原是不会存在的。中国的农民在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敢于探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有强烈的求知欲。在江汉平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已经彻底地告别了农耕生活,学习新的知识、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农民种地,要具备全方位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新的经济作物的栽培种植,这些作物品种本身就是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不去利用它们,学习它们,掌握它们,农民将无法生存,种不出一粒粮食。”
陈应松以葡萄为例,“葡萄这类水果,包含了世界农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水肥一体化,电脑和手机监控,它让大棚科技成了工业化管理,农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更不是牧歌时代的农村。我采访了这么多人,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故事,我都把他们放入到我的人物中去了。比方说有的葡农把葡萄当做一种田野艺术来经营,葡萄的枝条非常漂亮,像艺术品一样。树型、穗型、果型几乎一模一样,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令人惊叹。他们高呼农业就是大地的艺术,种地能种到这样的境地,可见湖北江汉平原的农民们是多么令人敬佩。有的葡农紧紧盯着国外最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还有的农民把葡萄产业做得非常之大、非常丰富,这是要有气魄和想象力的。有的将葡萄卖出120块钱一斤,有的将葡萄一颗颗剪下来卖,也卖出高价。还有一个回乡种葡萄的年轻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返乡,他种的生态葡萄与众不同,有相当的土地情怀,这样的事情都令人非常惊讶和感动。”
通过写《天露湾》,陈应松想告诉大家,“农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最伟大的人。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主动还是被裹挟,他们都跑在时代的前面,而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所谓城里的作家,却成了落伍者,是真的被时代抛弃的人。另外,我想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过去是洒下多少汗水,怎么勤耕苦做,而现在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怎么精心打扮它,怎么用科技之光照亮它。过去用赤脚丈量它,现在在大棚里摆弄它,农民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让土地喂着我们的方式,全都变了。希望大家能在我这部小说中,看到每一个具有传奇性的农民的故事。”
作家永远是在生活中在真实的感动中
陈应松曾说:“所谓故乡,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来越远的地方”,在写完《天露湾》后,他对故乡有了新的认知及感悟,“就是用文字重新发现故乡,重新发现土地,重新发现农民。再通过故乡的书写,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文学,重新发现作家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作家是为故乡而生的。毫无疑问,我在以后的写作中,肯定会继续出现水乡和平原的故事与风景,生活之树常绿,故乡永远年轻。更传奇的故事、更伟大的变革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它是作家们写作的源头活水,我们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们的文字也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陈应松表示,自己不太喜欢设定写作计划,总是突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今后我还会有关于家乡的作品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关于平原或水乡这样的符号的作品一定会出现。我现在主要是在神农架山里面居住和写作,因为空气特别好,特别清新、安静。《天露湾》是我的第一家乡的题材。神农架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作品我会交替写作,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好,另外一部关于神农架的长篇小说,在我完成了《森林沉默》之后,也已经开始动笔了。”
对于主题出版与文学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陈应松认为,对作家来说还是不必要考虑为好,“这是出版单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能考虑主题出版这样一个概念。写作就是写作,写生活就是写生活,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对于作家来说,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创作规律去写作,不要被所谓的主题出版所局限、所束缚。写作不能先入为主、主题先行,不能思想大于形象,不能喊口号,不能扎堆、起哄。不能为了完成某种主题出版,去迎合、虚构、图解、编造、夸大某种主题。出版方有他们的要求与任务,有时需要突出某种写作、某种题材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但是作家永远是在生活中、在真实的感动中。如果你撞上了某种主题出版,只能证明你撞上了,而不是命题作文、应景之作。作家内心的写作动力是生命中的感动。”
而不管创作什么题材,陈应松认为都不能离开生活,“当你真正深入到生活里面去,生活、人民,我们马上就能触摸到它的温度、它的气息和它的内涵。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深入生活和人民,就站在文学写作的道德制高点上,从而去漠视、否定写作中的艺术复杂性和丰富性,对艺术的探索不再有敬畏。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战胜一切压倒一切,从而把生活、人民、现实主义、主旋律,都概念化、符号化、扁平化和最大化。如果这样,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单调的、单一的、同质的、图解式的甚至是迎合式的表达,所以我的体会是写这样的作品必须非常小心翼翼、怀有敬畏,不能忘记文学的根本意义和审美品质。我希望在未来的写作中,更加努力地去克服过去形成的偏颇认识,更加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写作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远不如站在艺术的制高点长久。”
供图/珍妮猫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