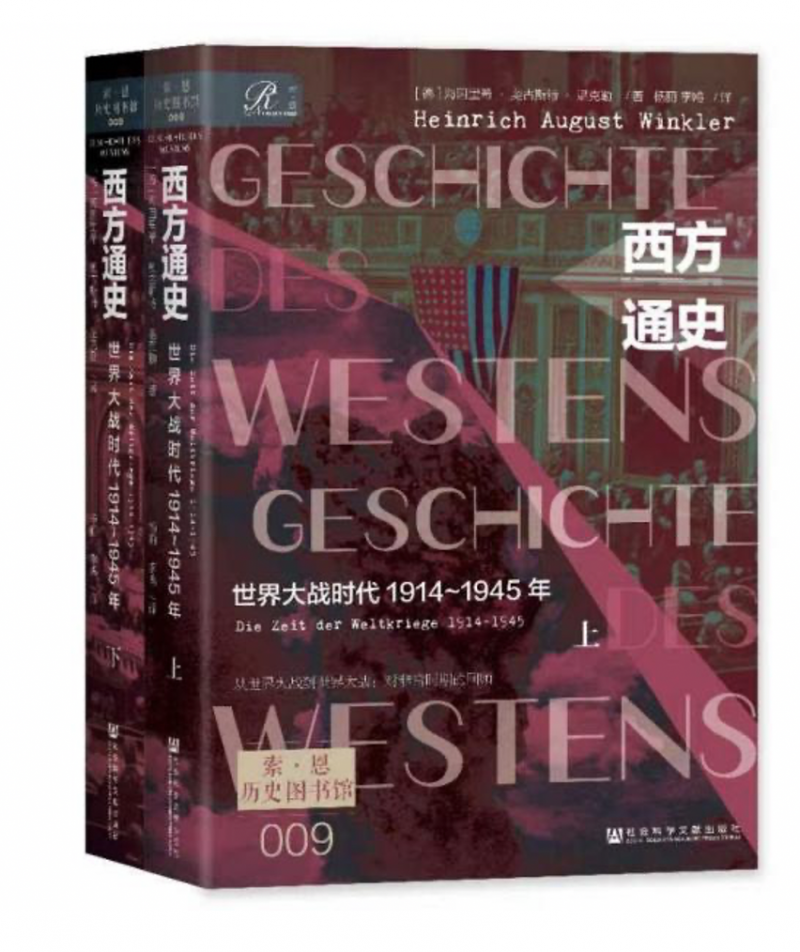此书是本套《西方通史》的第二卷。2009 年秋季出版的第一卷涵盖的历史跨度很大,始于早期犹太一神教影响的西方历史,谈及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围绕的重点是我称之为西方价值观规范工程的发展,即 18 世纪后期两次大西洋革命的理想,也就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古老的西欧就接受还是摒弃这些思想的争论,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甚至号称“发明家的合众国”曾几何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其内涵背道而驰;然而在今天,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如果西方想在非西方世界面前坚定地代表其价值观,那么它也必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身。
第二卷讲述 1914 年到 1945 年的历史,这 3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战争、危机和灾难此起彼伏。在此之前只有 1618 年到 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同在 17 世纪上半叶,德国在20 世纪上半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1914 年到 1945 年,德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甚至西方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可谓德国的篇章。同时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章节:最终以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以 20 世纪国家犯罪史上最彻底的大规模屠杀,以德意志帝国的灭亡而告终。
某些作者,例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大屠杀是一种现代性的、向理性化努力的、追求“唯一量化”的结果,是努力消除“矛盾心理”的结果,是某种技术性“社会工程”的极端案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工程在思想界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此外,很多作者长期以来将大屠杀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武力的经验,那些越轨的、迄今为止只在殖民战争中使用武力的经验。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乔治·F. 凯南(George F.Kennan)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20 世纪的“始发灾难”。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推导出其可行性的设想,在战争中养成机械化杀戮的习惯,这都是普遍的跨国现象。我们可以将 1918 年后的种种事件放入这个视角来分析,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犯下了大屠杀犹太人的反人类罪。本书就是从这个问题的背景出发,探讨 1914 年到 1945年德国历史的进程,去尝试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如此顽固地否定西方价值观的规范,特别是否定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以至于令世界和自身都跌入灾难的深渊。
如果按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想象,1918年后应该是西欧民主在全欧洲凯旋的时代。然而早在1925年,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尤利乌斯·博恩(Moritz JuliusBonn)就提出“欧洲民主的危机”。他分析的核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心理的变化:工人阶级势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产阶级的恐惧、军事化思维,同时严重低估了可以依靠严格的规范和公认的机构来解决民事纷争的种种办法。
在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那些民主立宪国家中,20年后只有两个国家还可以被称为民主国家,这就是捷克和芬兰。而其他国家中,执政的或多或少都是专制政权。它们在西方的遗产中挑选出更符合执政者利益的成分,而不是民主的思想,奉行“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原则。由于这些新生国家并不是纯粹的民族国家,有些甚至明显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它们在接受西方这种观点的同时,具体而言就是接受来自法国思想宝库的思想的同时,也埋下了产生重大分歧的种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体系的一个新特点是新型独裁,即所谓的极权专制。我们经常讨论的“极权”这个概念指的是某些国家,其对权力的垄断和镇压的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独裁者,超过那些公开的或者是秘密军事独裁的“正常标准”。极权政权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要求绝对服从,其政治目标是创造出新人。尽管在很多方面有天壤之别,但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极为相近。在和更激进、更极端和更“极权”的法西斯政权,即德国纳粹政权打交道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才重新评估了它们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关系,甚至迈出与其结成同盟的一步。在纳粹德国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所谓的“两极”世界,为 1945 年后的历史留下深深的印迹。德国为第二次争霸欧洲的尝试付出的代价是无条件投降,损失了战前四分之一的领土,盟军占领了全部国土。欧洲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力因战争被大大削弱,再也无法阻挡其海外势力不断缩小的进程。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国家分化割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这种现象推向极端:1947 年后“冷战阵营”相互对峙,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则成了各自阵营的领导力量。
——节选自《西方通史(第2卷):世界大战的时代(1914~1945)》序言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