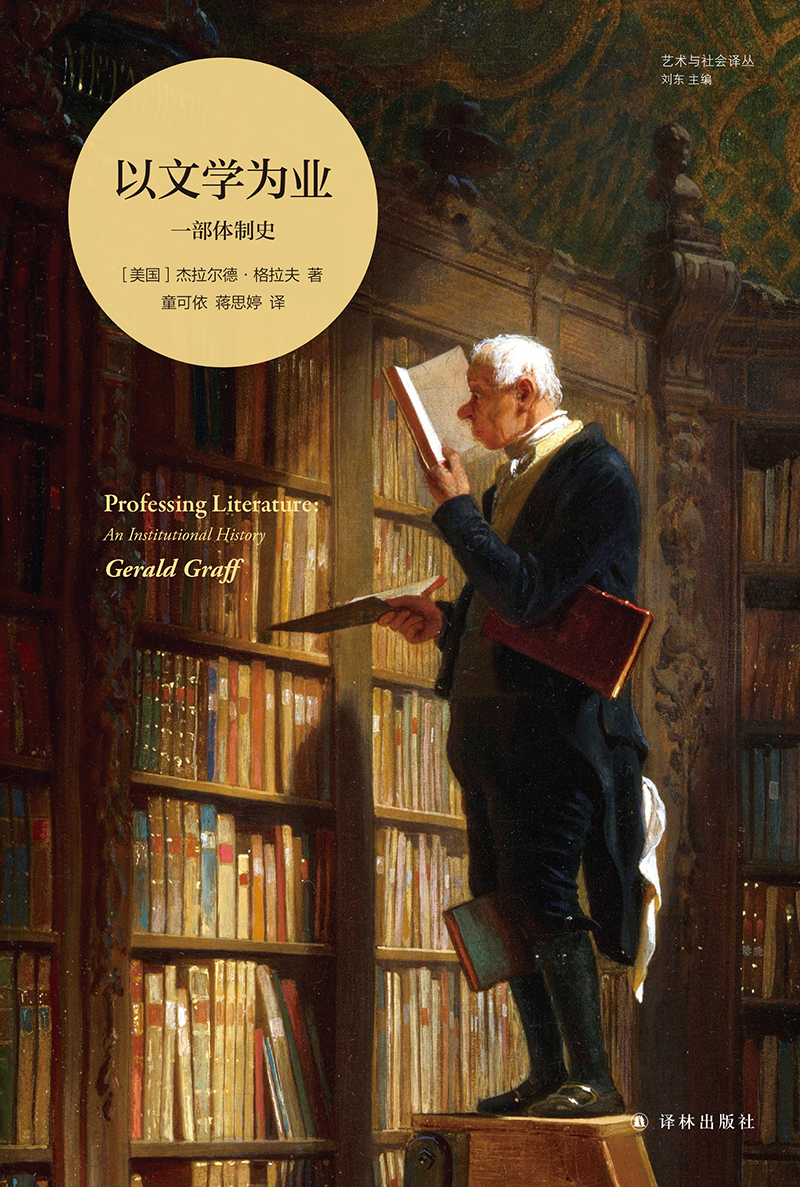据说,只要学院聚集了足够数量的专家,即使他们每个人都只懂某个学科的一小部分,这个学科的内容也可以算是被全面覆盖了,他们所属的学院科系也可以视作师资完备了。传说在古爱尔兰有一座塔,塔很高,需要两个人才看得到顶。一个人从塔底开始,一直看到目力所及之处,另一个人则从第一个人停止的地方开始,把剩下的部分看完。
——约翰·厄斯金
组织文学并非易事。
——欧文·豪
《以文学为业》是对美国学院文学研究历史的考察。这段历史大致始于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该报告确保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古典语言相较于俗语在美国大学中的优势地位——终于20世纪60年代新批评的衰落,以及随后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争论。严格来说,直到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大学语言文学系最终形成以前,“学院文学研究”在美国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是不存在的。然而将文学作为教育媒介的做法古已有之;在美国,从殖民时期起,文学文本就已经在大学的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文法、修辞学及演讲术等课堂里得到研读。这些早期实践有其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理论预设,而这种预设也将对后来文学系的形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学不仅是上流社会绅士教养过程中的一环,也是可以或者应该被教授的知识——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之前还未曾有过组织这种事业的先例。“组织文学”在任何情境下都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当它意味着要在一种或多或少民主的条件下,将此前一个特定阶层的社会交际的一部分内容重组为课程。我的研究表明,直到今天这项事业也很难说完成得十分全面,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我们对于其中的困难还不如早期的教育者来得警觉,因为学院文学研究一旦确立并变得自足,一旦忘却了一种可供比较的前学院文学文化,它也便失去了前人所拥有的历史视角。
想要在一本书的容量内处理如此宏大的主题,就必须略去一些内容,并将余下部分也相应精简。虽然我在行文中使用了“学院文学研究”和“文学系”这样的统称,我的绝大部分例证都来自主流大学中偏向研究型的英语系,至于英语系的范式与其他现代语言文学系或比较文学系之间的不同,我只是偶尔提及。也许我应该为本书加上一个“英语研究史”的副标题,然而我最终决定使用“文学”这个更为宽泛的标签,因为各个文学系的本质特征在我看来足够相似。
尽管如此,我的研究仍然无法代表小型学院的经验。同时我也怀疑,对于那些文学课——不同于写作课——已成为奢侈的教学机构来说,某些我视之为困局的状况已足以使它们艳羡不已。我在行文中只是顺带提及写作课的教学,然而正如威廉·莱利·帕克、华莱士·道格拉斯以及理查德·欧曼等学者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中表明的,如果没有写作课的教学,文学课的教学永远不可能获得如今的中心地位,我在这里讨论的种种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此外,我也只是偶尔提及英国大学,尽管它们对本土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书最后一章的目的并非详尽考察最近有关文学理论的争议—这已超出本书所能处理的范围—而是指出这些争议与学院文学研究滥觞时期的那些争议具有相似之处。此外,我还希望表明,文学理论可以给文学研究注入一些有益的自觉,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过去和现在的争论。当我使用“理论”一词时,其中一层含义是,所有文学教授都是“理论家”,也都在理论争论中有利害关系。与此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文学系(及其课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尽管这种理论总体来说并不连贯也不清晰,而正是这种不连贯加强了人们关于文学系没有理论的印象。
从传统的考量出发为将理论引入课程辩护也是可能的,比如可以说,学生需要理论概念来理解并聪明地谈论文学。应该看到,直到最近,出于对研究和阐释中原子化的经验主义倾向的反对—他们相信,关于文学的各种事实和解读的累积能自然地拼合出一幅连贯的图景—教育领域的传统主义者事实上是积极接受“理论”一词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新近的理论构成了对传统文学人文主义的前提和价值的猛烈攻击,而只是想说明,这些攻击者提出的有关文学的性质和文化功能的问题曾经也是传统人文主义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即使他们不再满足于后者给出的答案。传统的真正敌人是忽略一切有关目的、价值和定义的理论问题的正统文学研究,它将这些视为不言自明的。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或表面共识)的破裂激发了当下的理论井喷,而且我认为这不会只是昙花一现的潮流。
当我最初着手研究时,我有一个模糊的预设,即学院文学研究的开创者最初一定有一个关于这项事业的共同目标,只是这个目标后来不知为何失落了。在我的想象中,它与马修·阿诺德心中的“人文主义”和“文化传统”等理念相关。然而,经过研究我发现,虽然文学系的官方目标的确传承自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人文主义和文化传统,但对于这一目标应该如何实现,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分歧。认同马修·阿诺德的文学及文化观念的早期教育家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从语言文献和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尽管正是后者使文学研究在新式的研究型大学的科系设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阿诺德式人文主义与催生了学院文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从来都不稳固。传统人文主义者坚称,将文学割裂为一些专门化的、孤立的“领域”,以及对研究中的量化“生产”的吹捧,是对阿诺德的总体文化理想以及文学作为生活之批评的观念的损害。实用的、技术性的机械运作对于道德和文化理想的胜利,是阿诺德谴责的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中的一种,而研究崇拜似乎不过是这种胜利的又一例子——而且这一倾向在美国似乎尤为彰显。
得深思的是,如今我们称之为传统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在那些更早期的、沿袭文艺复兴经典人文主义的传统主义者看来,是一种颠覆性的革新。同样值得深思的是,那些传统人文主义者用来指控研究型学术的罪名,与后来的传统主义者指控新批评,以及今天的传统主义者指控文学理论的罪名如出一辙:重专业术语而轻人文主义价值,阻碍学生与文学本身的直接交流,使文学成为专家精英趣味的消遣。无论新近理论的罪过为何,那些将人文学科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学理论的人,无非验证了他们自己恪守的信条,即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回归伟大的传统,而不去考察这一传统为何逐渐受到质疑—也只会使之前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循环再次上演。
当然,研究型学者并不认同传统人文主义者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同样自视为马修·阿诺德的合法继承人,认为指摘自己的人不过是外行,纯粹是出于恋旧心理(很多时候也确实如此)。然而即便如此,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型学者当中,仍有相当多的人认同对于他们的某种批评,即他们的传统人文主义理想与他们的职业实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在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早期的会议上,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互相敦促要对这种差距有所行动,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止步于一些收效甚微、如今已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声明:必须把教学重新提至与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面对研究生院的专业化,必须重申本科“通识文化”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必须重新将文学本身置于学术和方法论之上。这种对问题的诊断导致他们陷入了宿命论,将自己的问题归结于美国民主内在的庸俗、现代社会内在的粗鄙,或是学生质量无可救药的低劣。
对于研究和发表取代了教学的指控,与另一种并行的指控类似,即技术或官僚体制取代了更为人性的或公共性的关系。无论其出发点如何,这样的指控注定是无益的,因为它认定学者的职业利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除了自行消亡。这种指控所基于的诊断,是将学院制度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于专业化本身,而不去区分专业化概念与新兴大学环境中特定形式的专业化之间的差异——必须强调,这些形式并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无论这些早期批评者的观念对当下的指导意义如何有限,它至少有助于打破我们的一个错误印象,即学院文学研究是从某个时期起才开始偏离真正的、阿诺德式的人文主义的。
支撑这种人文主义神话的是一种惯性思维,即把制度视为重要人物和运动的价值、方法、意识形态的直接投射。这种思维非常便捷,初看起来也符合常识,然而它忽略了,即使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批判性价值、方法和意识形态在被制度化为学术领域、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专业化”与“学院化”并不是中性的组织原则,而是将各种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主义”进行转化的能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义”的本意往往被彻底颠覆或偏离,以至于外人完全无法辨认。设想与结果并不必然一致,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在体制内的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却可能很难为体制外的人觉察。
我将本书命名为体制史,意在强调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特定的学术批评实践,还包括这些实践在现代大学中被以某些方式—这些方式并非唯一可能的方式—制度化后所经历的变化。换言之,我关注的不仅是以个别学术成果、潮流的形态“进入”的东西,也包括作为一种操作性的整体“出来”的东西,以及这个整体如何被体制以外的人理解、误解,或是完全没有觉察。大多数关于批评的历史都彻底忽略了这些问题,把焦点放在主要人物和运动上,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结论无法为制度分析提供可靠的基础。因为即使是主要人物和运动也无法保证其价值能在一种制度的整体中留下深远的影响。阿诺德式的人文主义对其学生和追随者的个人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他们却从未成功地把这些价值转化为整体制度的可见特征。到了20世纪初,“人文主义”——以欧文·白璧德及其团体为代表(如果我们暂时把这个词的复杂历史放在一边)——已成为学院的一个阵营,成为诸多已确立的“领域”中或多或少被疏远的一个。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标志性的阿诺德式人文主义者,从白璧德到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最后都成了行业的激烈批评者。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