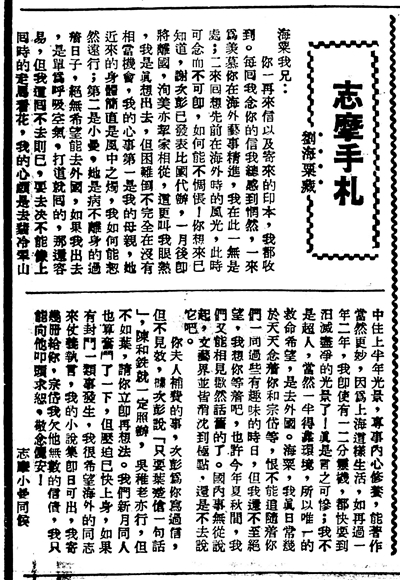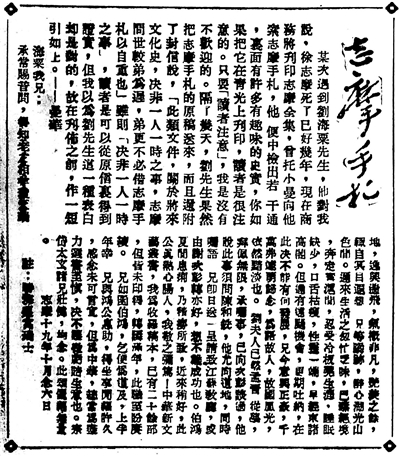刘海粟看待“志摩手札”: 决非一人一时之事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殒命。中国新诗界最杰出的代表就这样英年早逝。消息传出,社会各界无不感到震惊与哀痛。从1931年11月22日至1933年11月20日,两年时间里,关于这场死难事件的各种调查与追诉一直在进行,对徐氏英年殒命的哀悼与纪念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在悼念活动中,作为徐志摩的多年挚友,其暂寓北平期间的“房东”胡适,始终辗转奔忙其间。在徐氏逝世两周年之际,胡适等倡议出版《徐志摩全集》,以为永久纪念。
当时,全集文稿编制基本就绪,遗孀陆小曼原拟交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经胡适从中斡旋协调,改由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因为全集待搜求的信件一时难以罗致齐备,编印工作也因之耽搁。在此期间,亦有徐氏信件零星见诸报刊发表,多为其生前友人缅怀追念之举。
譬如,刘海粟就曾于1943年在上海《文友》杂志上,发表过数通徐氏信件——这些被冠以“志摩手札”之总题的徐氏通信,时隔七十余年之后,方才被收入《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201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可谓至今最为齐备的徐氏全集,上述这些新近发掘出来的徐氏致刘海粟信件,自然悉数收入,务求完满。
其实,刘海粟曾早在1936年末,即将部分徐氏通信冠以“志摩手札”的总题,交由上海《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发表,比后来交由《文友》杂志发表,早了七年。“志摩手札”在该报首度发表时,副刊主编的一则“短引”,就很能反映出刘海粟亟欲尽快发表这批徐氏信件的“初心”所在:
某次遇到刘海粟先生,他对我说,徐志摩死了已好几年,现在商务将刊印《志摩全集》,曾托小曼向他索志摩手札,他便中检出若干通,里面有许多有趣味的史实,你如果把它在“青光”上刊印,读者是很注意的。只要“读者注意”,我是没有不欢迎的。隔了几天,刘先生果然把志摩手札的原稿送来,而且还附了封信说,“此类文件,关于将来文化史,决非一人一时之事,志摩问世较弟为迟,弟更不必借志摩手札以自重也”。虽则“决非一人一时之事”,读者是可以从原信里得到证实,但我以为刘先生这一种表白却是对的,故在刊布之前,作一短引如上。
——曼华
“曼华”即朱曼华,其人自1935年初主编“青光”副刊,直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事新报》迁至内地续办。当时,朱曼华对刘海粟拟将志摩手札先行发表的心愿,表示理解与支持。自1936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25日,《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上,陆续十二次刊发了“志摩手札”,全部为徐志摩致刘海粟手札,共计达十七通之多。
徐志摩致刘海粟信札,最后一次刊载于《时事新报》,1937年1月25日(局部)
辞职“北上”前的心声:“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
“青光”副刊首次发表的“志摩手札”,为徐志摩于1930年10月26日致刘海粟的手札。1943年7月15日,此信又在上海《文友》半月刊上刊发了出来,信文字词上略有差讹。在此,谨以“青光”副刊所刊布的“原信”为底本,转录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承常赐音问,得知老友徜徉琼天瑞地,逸兴遄飞,气概非凡,艳羡之余,辄自冥目遐想:兄等踪迹,醉心湖光山色间。迩来生活之匆忙乏味,已臻绝境,奔走宁沪间,忍受冷板凳生涯,睡眠缺少,口舌枯瘦,性灵一端,早经束之高阁。但待有远飏机会,更期吐纳,在此绝不能有何发展。兄今意兴正豪,千万弗遽萌归念,为语故人,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刘夫人已然孟晋从学,拜佩无限,承嘱事,已向次彭谈过,他说此事须问陈和铣,他允向道地,同时嘱语,兄即日送一呈请致江苏教厅,或由谢次彭转亦好,想不难成功也。伯鸿夏间患痢,乃积痨所致,近来稍好。此公真热心肠人,我敬之弥笃!中华新文艺丛书,我为收罗稿本,已有二十余部,但皆未印得,转瞬满年,此职至盼赓续。兄如函伯鸿,乞便为道及,上半年幸兄与鸿公惠助,得坐享闲福许久,感念未可言宣,但为中华,总当为尽力选书至慎,决不要做亏赔生意也。宗岱、太玄诸兄壮健,均念。此颂俪福无量。
志摩十九年十月念六日
《时事新报》刊发此信时,于文末有小注称“时海粟寓瑞士”,可知刘海粟当时旅寓瑞士,正忙于海外举办画展。彼时徐志摩有意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北上”,赴北大任教。所谓“奔走宁沪间,忍受冷板凳生涯”“故国风光,依然黯淡”,正是这一时期苦闷心境的写照。收到瑞士寄来的这一信件,徐志摩在回信中所流露与表达出来的情绪,恰恰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其“奔走宁沪间”,郁郁不得志,意欲“北上”重谋发展时的真实心境与心态。
徐志摩致刘海粟信札,首次刊发于《时事新报》,1936年12月28日(局部)
此时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怅
1937年1月25日,第十七通也是最后一通“志摩手札”在“青光”副刊上发表了出来。此信后于1947年7月间发表在了《文友》半月刊之上,同样也被收入了《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提及徐氏个人亟愿出国“专事内心修养”,可因为母亲病重“如风中之烛”,夫人陆小曼“也是病不离身的过着日子”,所以一时无法“追随着你们(指当时正旅寓法国巴黎的刘海粟与梁宗岱)一同过些有趣味的时日”,表现出对二人海外游学与旅居生活的追慕与向往之意。这样的心态与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后来徐志摩毅然辞去南京教职,果断“北上”谋求更大发展的动因所在。
特别是文中一句“我不是超人”之慨叹,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此时徐氏虽仍孜孜以求寻求个人发展,却因“家累”种种而不得不疲于奔命的情态——在这样的主客观因素叠加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两年后因仓促行事,搭乘载邮货机不幸坠机罹难的命运,似乎早已冥冥注定了。转录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你一再来信以及寄来的印本,我都收到。每回我念你的信,我总感到惘然,一来为羡慕你在海外艺事精进,我在此一无是处;二来回想先前在海外时的风光,此时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怅!你想来已知道,谢次彭已发表比国代办,一月后即将离国,洵美亦挈家相从,这更叫我眼热,我是真想出去,但困难倒不完全在没有相当机会。我的心事第一是我的母亲,她近来的身体简直是风中之烛,我如何能恝然远行;第二是小曼,她是病不离身的过着日子,绝无希望能去外国,如果我出去,是单为呼吸空气,打道就回的,那还容易,但我这回不去则已,要去绝不能像上回时的走马看花,我的心愿是去翡冷翠山中住上半年光景,专事内心修养,能著作当然更妙。因为上海这样生活,如再过一年二年,我即使有一二分灵机,都快要到汩灭尽净的光景了——真是言之可惨;我不是超人,当然一半得靠环境,所以惟一的救命希望,是去外国。海粟,我真日常几于天天念着你和宗岱等,恨不能追随着你们一同过些有趣味的时日,但我还不至绝望,我想你等着吧,也许今年夏秋间,我们又能相见欢然话旧的了。国内事无从说起,文艺界并皆消沈到极点,还是不去说它吧。
你夫人补费的事,次彭为你写过信,但不见效,据次彭说“只要叶楚伧一句话”,陈和铣就一定照办,吴稚老亦行,但不如叶,请你立即再想法。我们新月同人也算奋斗了一下,但压迫已快上身,如果有封门一类事发生,我很希望海外的同志来仗义执言,我的小说集即日可出,我寄几册给你。宗岱我欠他无数的信债,我只能向他叩头求恕。敬念俪安!
志摩小曼同候
上述六百余字的“志摩手札”,没有时间落款,“青光”副刊上也并没有任何说明。为此,不妨就从信中所言“谢次彭已发表比国代办,一月后即将离国”之事,来推测此信的书写时间。
据考,谢次彭即谢寿康,江西赣县人,曾于1923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次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1929年归国,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2月,出任驻比利时使馆代办。显然,徐信应当写于1930年2月前后。
遥思那一番“我不是超人,当然一半得靠环境”的慨叹,在八个月之后“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的感慨之中,终于令其做出了辞职“北上”的人生抉择。可以说,“青光”副刊上的这十七通“志摩手札”,是以某种类似于“倒叙”手法,将诗人从“奔忙宁沪间”转而毅然“北上”的心路历程,悄然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