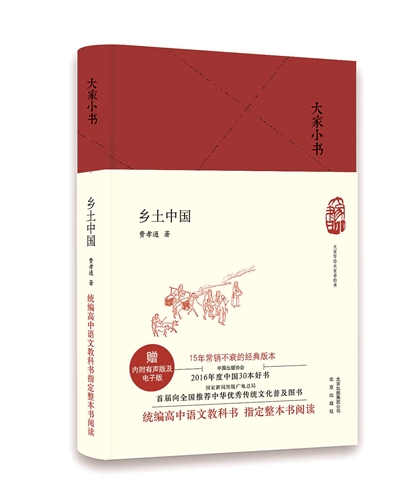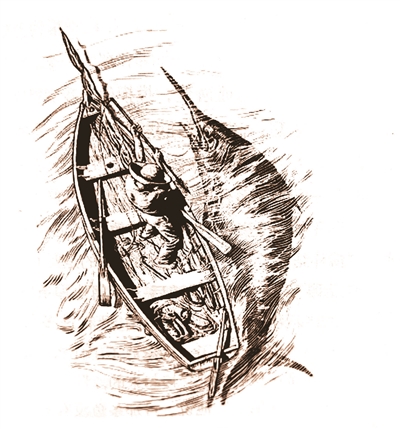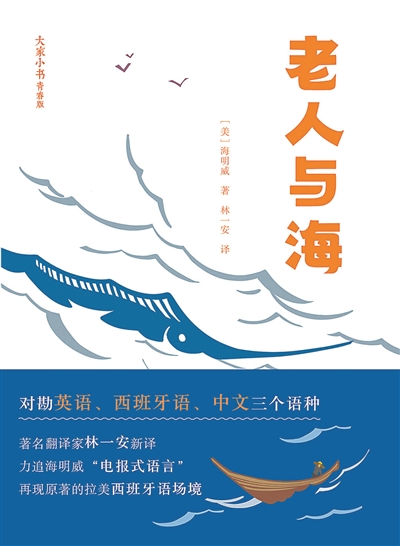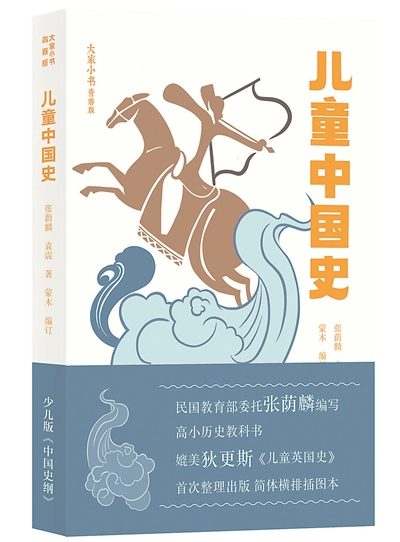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的办公室和我想象中没有区别,书籍盈满,错错落落,叠了又叠。让我讶异的是,他能在其中准确随意地找到他需要的书,然后拎出来如数家珍。
“大家小书”这套丛书占据了他书柜的好几层,种类繁多。这是北京出版社的拳头产品,曾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它的编辑宗旨是,提倡大家写小书,让各学科的常识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
丛书每本篇幅都在10万字左右,为的是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知识。著名学者袁行霈在丛书序言中说:所谓“大家”,包含两层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大家小书”开本都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高立志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策划人,在丛书出版二百种之际,高立志又相机推出了“大家小书青春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2020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教育推荐阅读书目,‘大家小书’被大量选入,我就想借此契机把适合学生阅读的拎出来,为中国教育贡献点力量,这就是做‘大家小书青春版’的策划初衷。”
和高立志谈话,能深切感受到他的风趣睿智。做书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志趣爱好。他的做书理念融合在他的幽默中,可以支持他滔滔不绝地讲话,而话语里尽是“真金白银”。
读书,入门不正很害人
高立志做“大家小书”的野心,是希望打通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的学术文脉。他相信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一定是趋同的,而差异部分就像镜子。“想要进步就需要照镜子看看自己,这也是哲学产生的根源。而理解这个镜子之前,必须承认和尊重差异,文化遗产不分国界,继承了才是你的,不继承永远不是你的。”这是高立志的理念。
目前丛书做了二百余种,高立志遵循理念自觉地涵纳融通,希望提供给大众一个系统,因为只有了解系统才能知道“传统文化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大家小书”是专业大家写给普通大众读的书,即学术普及,不少书目的作者是民国时期的大学者。民国大家普遍接受过中西教育,他们更知道如何给普通读者讲话,这一点在高立志看来尤为重要。他说:“民国这些人的成长环境中没有很细分的学科概念,他们多在传统文化中哺育成长,国学修养后人难以企及。他们又普遍接受过西方教育,把西方思想作为镜子来反观我们的文化,这有极大好处。所以他们一般都善写,写得漂亮大气,那东西当然适合普及。”
当代“大家小书”的作者,很多也为高立志所钦佩。这些作者的共同特点是精益求精。“像刘北成老师,我们给他一个稿子,他的改稿能把每个空间都写得满满的,字还很正,照排的工作人员都能认识。”
“大家小书”有个倾向,阅读对象越低端越跨界,书的销量越好,如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这样文史哲诸学科都避不开的必读书目。但像《训诂简论》《敦煌学概论》,作者是大家,关心的人相对较少,可对于“大家小书”来说,高立志认为它们也是必需的。
做有传承、能传承的“大家小书”,除了强调“大家”概念,高立志还强调要界定清楚“民科”和真专家,“对于传统文化和优秀的西方文化,都应该采取严谨的态度对待。”而这个严谨的态度,在高立志心目中,就是版本选择和阅读门槛。“我不讳言,很多‘大家小书’虽然立足普及,但都存在阅读门槛。我觉得读书不愿意克服困难,谈不上传统文化弘扬。”对于读一本《左传故事选》就可以谈《左传》,读一本《论语选译》就可以对孔子思想发表高论的现象,在高立志看来非常荒诞,所以他认为急需普及版本学知识。
高立志常逛公园和旧书店。有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盗版书摊,一位老太太正问摊主有没有《论语》。摊主拿一本很大很厚的《论语全集》递过去。老太太看半天说:“原来《论语》长这个样子?”摊主回答:“只有一本《论语》,没有别的《论语》。”于是老太太买下了,嘴里说是给孙子买的。
这样误人子弟的事,高立志评价为“入门不正很害人”。“古书这一块,特别是诗歌,真的是版本重灾区。”这是高立志长期以来的感受,所以他到北京出版社后,立刻把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放进了“大家小书”。选书,懂一点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看看作者、整理者、译者、出版社,甚至责任编辑,非常必要。如果还是不好辨别,可以看作者简介,“假如作者是做管理学的,他从管理角度切入解读《老子》,而这个读者也是搞管理的,买它就很对路;而如果你想了解的是基本文献或者思想史,那显然买它就不合适。”
做书,反感“速成品”
做书之前,高立志是个媒体人。在江苏《无锡日报》的新闻版面耕耘时,他却总想做些能留存更久的东西。“感觉书比报纸要长久一些,我就在2003年转入了出版行业。”出版和媒体在他看来是相通的,出版编辑的技术手段和理念与新闻编辑一般无二。
高立志曾经非常关注畅销书,发现超级畅销书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社会思潮,就像新闻由头一样。而出版界是一个奇特的场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有好点子未必能赚钱。“一本书最终落在谁的手里,在谁的手里出,形态完全不一样,书有书的命运。但还有句话:栽树的不如采蘑菇的。图书最终是否送到需要的人手里,也就是说销量如何,真不敢说,最富创意的产品往往不如跟风产品挣钱。”
见过太多“死”在畅销书路上的书商,高立志明白真正应该追求的是长销。在出版行业中,带流量的作者具有绝对优势,出版社也需要一定的品牌和流量。据高立志所知,很多大名头的书出版社是亏损着出。而很多时候,一本优质书的产生,编辑力量不弱于作者,这是一种综合性工作。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的一句话高立志很认同:作者写他们能写的,编辑编我们能编的。按理论说,作者是智力生产者,出版人只是传播者,但突出作品的某一方面,以使其适合市场,体现的则是编者智慧。对于出版编辑的真正成就感,高立志总结有三:引领业界某一倾向;发现重要作者;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书。
高立志内心很反感做速成品,觉得“三分钟读懂世界史”之类的书荒唐至极,他吐槽:“三分钟读懂世界史,还要那么多历史学家干吗?”有一段时间坊间纷争图文书,接着绘本大热,高立志当初就觉得不是正途。他认为图像和文字带给人的想象力当然是不一样的,而某种意义上的具象化限制想象,可一个人无论想在哪方面有所发展,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译本,看重译者的风格与自律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具有国际眼光。高立志和同行们的共识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需要有西方文化参照,所以,他主持开办了“大家小书”译馆系列。
对于译本,高立志强调的是译者,讲究的还是版本。他很看重那些一辈子只译一本书的老译者,“吃透了,研究透了,他的译本就是一个研究产品。”高立志始终认为翻译工作首先是态度问题,“我们审译稿时,凡是读不通的地方基本都有问题,就是译者在一些地方没有吃透而硬译过来造成的。”
高立志敬重在翻译工作上具有苛刻态度的人,“这些人天生适合做翻译,比如林一安老师。”高立志和林一安合作出版“大家小书青春版”的《老人与海》,是他的一部得意之作。
为了做《老人与海》,高立志比对英文版和几个优秀汉译本。他过去一直认为《老人与海》比较简单,但对比起来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细读文本会发现有好多语焉不详的东西。这本书是海明威在古巴写的,原型也是古巴老渔夫。为了精确反映情境,海明威的写作将大量当地西班牙语糅进了英语,所以如果单纯根据英语来翻译就会出不少问题。”林一安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他首先是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又出身于海关职员家庭,从小英语就不错,还一直研究拉美文学。
《老人与海》这部海明威的名著一般被定性为美国精神的表现,但高立志从林一安处了解到,《老人与海》反映的是一种拉美革命精神。高立志回忆:“他和我说这个时,我脑海里立刻反映出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的那张合照。海明威无疑是倾向于左翼的,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所以林一安说《老人与海》是拉美革命的史诗,我觉得基本成立。”
林一安的一些译法,开始高立志看不太惯。如将第一段的“老人和孩子”译作“老人和小伙子”,在他的概念中,《老人与海》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来岁孩子的形象。为此他查阅很多资料,最后得出了和林一安同样的结论:和老人在一起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而非弱小孩童。
另有很多译本将第三人称的动物译作“它”,高立志认为这有违海明威的风格。“因为原文中海明威对动物的表述是‘he’,我想海明威要表现的是人与大自然的亲密相伴,他不希望人在大自然中过分分彼此,所以他对老人、鸟、鱼的称呼都是人格化的,如果翻译成‘它’就丧失了这一层意蕴。”
林一安在翻译上有着精确自律:句子尽量不超过20个字。“这也与海明威电报式的语言相应,是林一安译本的鲜明风格,而我们的大部分译本没有风格追求,甚至有的是汉语对汉语改写的结果。”高立志说,“《老人与海》早期比较重要的汉译本包括张爱玲、余光中、海观、赵少伟诸先生的,后来阅读最为广泛的是吴劳先生的译本,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了海明威版权。海明威公版后译本就满天飞了。”
林一安版《老人与海》,高立志的得意之处在于,它反映出了自己的编辑思想。“《老人与海》文本很短,三四万字,这是很多编辑不愿意碰的。因为利润空间薄,文字少也难撑起一本书。”高立志说,“市场上的《老人与海》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或者是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而我做的这版却干干净净,就是《老人与海》中文文本和插图。”
插图作者是插画界大名鼎鼎的雷蒙德·谢泼德和查尔斯·图尼克利夫,他俩为伦敦“重印书”学会1953年版《老人与海》做了漂亮而精致的插图。“极好!”高立志评价。林一安版《老人与海》中译本插图均出自该版书,但现在只是部分选入。“如果条件允许,将来我想把原著的图全部弄过来。”高立志说。
《儿童中国史》诞生中的意外
“大家小书青春版”中还有一本《儿童中国史》,署名张荫麟、袁震,也是高立志的得意之作。这本小书的成书过程着实有些意外。
张荫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梁启超、陈寅恪格外看重的学生。他到国外学哲学,后来修社会学,被人称为不务正业。他却说自己将来的志愿还是历史,学哲学是要获得超观世界的方法;学社会学是要学会理解社会演进的方法。这样一位具有明确大格局的人,是高立志看重其作品的原因。
最初,高立志买到一套《张荫麟全集》,其中有《儿童中国史》,只有薄薄几页。“我过去读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序言中介绍,这是民国教育部委托其编的一部中学教科书。没有想到他还编有小学教科书。”在序言中,张荫麟提到如何普及中国历史的问题,认为我们的历史从小学学到大学都是由三皇五帝到现在,实在是浪费精力,所以应该编适合各阶段学生学习的教材。“他的想法是高中生应该懂得历史演进的大脉络,小孩子则了解一些英雄人物就可以了。”
高立志细读张荫麟的《儿童中国史》,觉得“他用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的类《史记》写法,有贴近感,语言也好,很大气”。
做书的人永远盘算着选题,高立志直觉《儿童中国史》可以成书。他注意到张荫麟编写的部分缺少北宋几个人物,这通过自己整理的《两宋史纲》可以辑录出来。但袁震和杨联陞撰写的部分呢?正发愁时,习之先生给他带来喜讯,他在编《吴晗年谱》时整理到吴晗夫人袁震的几篇文章,认为该编入《吴晗佚文集》。高立志认为,“如果将袁震的这几篇宋文补充进来是很好的。但其作者究竟是谁?张荫麟在序言中说得清楚,南宋和明代部分由袁震执笔,明清部分由杨联陞执笔。”
但习之先生认为文章虽然署名袁震,却可能出自吴晗之手。高立志仔细分析后排除了这种可能。他想,当时袁震未婚,张荫麟作为她的师兄,不会不了解其身体情况,如果袁震的身体不支持她去写书,张荫麟不可能强迫她去做。另外写法也是袁震的,而不像吴晗,例如其中的于谦,对比这一篇和吴晗写的于谦,一句相同的话都没有,甚至一些重要观点也不一样。因此,他果断地将袁震文收进《儿童中国史》,同时署名张荫麟、袁震著。
令高立志遗憾的是,杨联陞先生的清代到抗日这部分文章始终没有找到。他遍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都了无踪影,“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杨先生的文章在哪。我想可能已经遗失了,毕竟当时是战乱时期。”
踏踏实实做书比八面玲珑做人重要
作为一位做书人,高立志不喜欢荐书,觉得那是一种堕落,“读书应该是主动的,为什么要别人推荐呢?”
“大家小书”做满一百种时,有人提出书目有深有浅,能不能做阅读分层?这件事真的让高立志困惑了一年。“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比如《诗词格律概要》,算浅还是算深?我想学习写旧诗的人肯定要读,学生也许也要读。但像我,天生平仄不全,就像看天书一样,那就不想读。”困惑中的高立志被陈平原教授的话解救了,“陈教授就反对阅读分层,因为阅读是一个人考虑问题时主动找书来读,分层不是剥夺人的思考权吗?”
高立志还请学生慎读改编本。他举例,“儿子三年级时学校要求读《三国演义》,我想三年级字都认不全怎么读,就给他买了一本带拼音的少儿版,后来发现人家根本不看。我很奇怪,《三国演义》多好看啊,为什么不看?拿来一翻,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原著开头的气魄全丢掉了,把最精华的部分丢掉了,只抽了几个故事。其实孩子的领悟能力是很强的,他觉得难理解他就不看。阅读习惯的养成,客观上需要大量阅读,但一定要是比较自主的选择。”
高立志特别喜欢作家史铁生,认为是难得一个在浮躁社会里深思的作家,“给他怎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而天天没完没了琢磨精神和大奖,却说有伟大创作的不可想象,我觉得除了骗人还是骗人。”
汪曾祺他也喜欢,认为是难得的始终持守纯净的作家。他自觉受汪先生影响很大,并回想起1992年刚进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汪曾祺来做讲座的情景。“汪先生眼睛不看人的,大眼睛朝上盯着天花板,半天谁都不理,然后带着家乡口音开始讲:有人问我怎么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第一是逃课。停下来想一想,又说,第二还是逃课。我为什么在西南联大不能留校?就是因为朱自清先生认为我总是逃课……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书就不读。我最喜欢的是我老师沈从文,喜欢契科夫、阿索林,都反复读。托尔斯泰我不喜欢,我就不读。”
特别烦闷的时候,高立志愿意读上几页经典书,感到平静一些。他反对各种励志书,也不喜欢大部分网文,那只会使他心境更浮躁。“好的语言不易得,有天生的成分,沈从文、萧红语言都好,他们的语言不是规训出来的。语言是有灵性的东西,满脑子私心杂念,写出来的也是私心杂念。”这是高立志的总结。
学者王宁先生曾对“大家小书”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其自身语言就成为一种规范。高立志一直在遵守:“我们已经出了好几本有关汉字的书。”他也一直强调做学术普及要读原典,虽然他不是语言哲学的盲目崇拜者,但相信语言是所有文化的最终结点。“中国最伟大的发明肯定不是纸张、指南针,而是汉字。汉字维系了汉语言文化圈,这才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东西。”
出版业碰到一系列困境,如何去适应?高立志认为在时代大环境下考验的是领导者智慧,而不是编辑。他经常给手下的编辑们打气:文化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需要传播,所以编辑的创意永远需要。“今后真正考验编辑的是审美素质。因为传播形式的转变,使书的奢侈化不可逆转,而判断一个内容值不值得出纸质书,将是对编辑判断力的第一个考验。”
高立志也知道很多事情做起来难。做书多年,他常常想:谦受益,满招损,学会倾听比学会语言更重要,踏踏实实做书比八面玲珑做人更重要。
供图/方一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