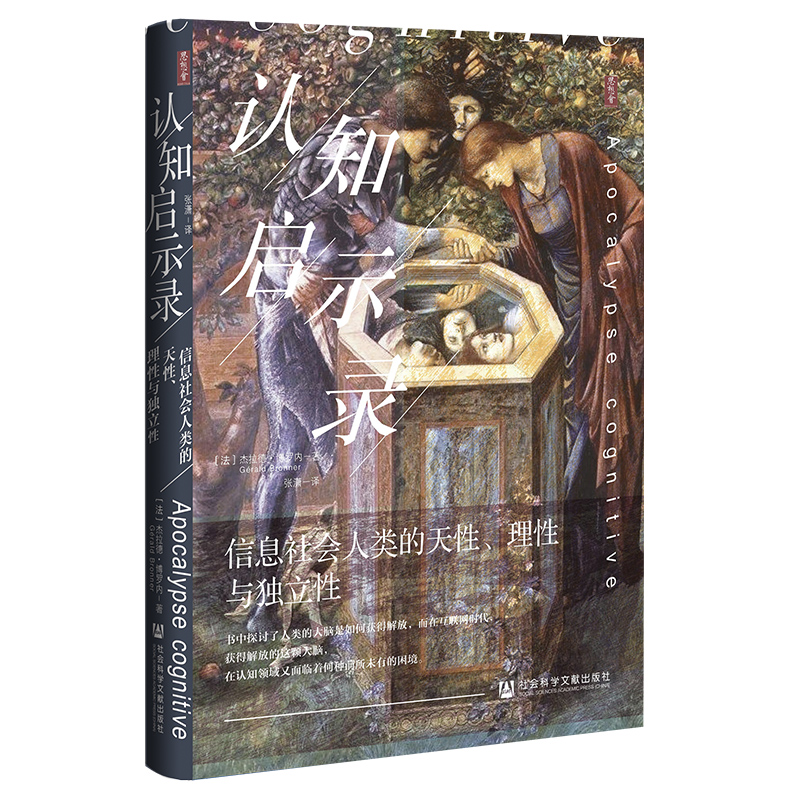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当时我还年轻,不能完全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人们欢呼,跳舞。同年,齐奥塞斯库夫妇(Ceausescu)也双双被处决。一句话,新的时代正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个见证它的机会。但同时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因为有人断言此类事件将不会再发生。其中包括年轻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30多岁时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本书后来在全球引起了巨大轰动。该书是福山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延伸,有人认为它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论述之一。书中指出,新的时代意味着“自由民主制理想的真正到来”。福山十分清楚暴力和动乱不会消失,但在他看来,至少“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代表制度能够与自由民主相竞争”,而“自由民主是今后政治思想唯一可能的前景”。
这是否只是顽劣稚子的突发奇想?在为我们预言的普遍和平中,有些事情让我高兴不起来。所以我们要这样缓慢而无聊的生活吗?你即使不了解历史的恐怖,也能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推理,但这却是我开启20世纪末的方式。我还注意到,道德愤慨正在成为常态,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的遮羞布。我们并非不如前人勇敢,却不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英雄。历史是否会走到尽头?我的智力训练一定不完善,以至于会相信这种寓言。历史永远不会结束。
30年后,历史似乎突然撞进了我们的现实。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几乎不可能去好好想明白。作为自由民主模式替代方案的政治制度层出不穷:中国式政治制度、土耳其或俄罗斯的民主制度等都提出了社会变革,其中一些分支希望衰减,而另一些则宣称反物种主义。
在这个激动人心却又令人不安的时期,从其特有的种种事实中,我注意到,21世纪前20年带来了对认知市场,也可称为思想市场的大规模放松管制。一方面不难看出,可用的信息量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人人都可以将自己对世界的表述汇入信息海洋之中。这种情况削弱了在这个市场中行使监管职能的传统看门人(记者、学者、专家等任何被视为具有社会合法性可参与公共辩论的人)的作用。这一重大的社会学事实产生了种种后果,但最明显的是,我们见证了各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智力模型在相互竞争,宣称要勾勒出这个世界的轮廓。今天,一个在社交网络上拥有账号的人或许可以就疫苗问题直接反驳国家医学科学院某位教授的观点。前者甚至可以吹嘘自己比后者有更多的观众。
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信仰和系统思维的竞争,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前者经常阻止后者的表达。在某些社会中,想要为新兴科学和系统思维辩护的违禁者的代价可能是死亡。信仰可以压制异议,例如以火刑相威胁。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尽量避免同反对意见当堂对质。因此,在经院哲学的时代,当人们意图弄清上帝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时,当时的思想家发现自己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左右为难。到了充斥着学术危机的13世纪,人们发现了历史学家阿兰·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称之为“中世纪精神分裂症”的双重真理,即希望同一个人以哲学家的身份相信一件事,而作为基督徒则相信另一件事。这是人类历史为避免对抗而发明的其中一项权宜之计。但这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知识的进步往往再次直接挑战宗教文本的字面意义或任何其他基于超自然、魔法和伪科学的命题。
仅举一例,《圣经》中的观点(创世纪1∶20-30和2∶7),即动物和人类均由上帝创造——每个物种都是单独、有区别地被创造出来——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威信。当它仍然声称我们的地球是在六天内被创造出来的(创世纪1∶1-31)并且已有6000年的历史时,面对化石的发现、它们的年代测定以及总体上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在19世纪,情况并没有好转。这一切给盛行数百年的圣经世界观带来了诸多麻烦。可以说,在关于世界的某些设想上,科学的智力模型与宗教的智力模型是截然相反的。
面对这种矛盾,信徒有几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信仰,承认其信仰所依据的书只是由一则则寓言所组成;要么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错误的。而第二种解决方案比第一种选择更为常见。无论事实如何,很少有信徒仅仅因为一个反驳就放弃自己的信仰。相反,他会竭力诋毁异见持有者,无休止地剖析导致这些困扰他的结论的方法,清除这些结论背后的推理错误。简而言之,他不会任人摆布,必将斗争到底,维护这种在不知不觉中束缚他的描述体系。
如今,这一策略在土耳其仍然盛行,例如2017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将达尔文的理论从生物课本中删除,认为它违背了该国的价值观。从现在开始,只有年满18岁的人才被许可了解构成生命之谜的科学方法。就这样,进化论被列为X类,如同在沙特阿拉伯一样。在美国,进化论并没有被学校禁止,但也没有被广泛教授。当然,我们可以高兴的是,盖洛普研究所在2019年强调这个国家从未如此强烈地坚守达尔文的观点,但也不应过于激动,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22%的人认为“人类数百万年是从较低级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上帝与这种现象无关”。1983年仅9%的人持此观点,但生物学中笃信宗教的人仍然存在——包括所有的敏感论断——至今仍占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总人口的70%以上。
当知识的进步威胁到其陈述时,信徒可以采取第三种策略:认为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对立。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这种多方讨好的策略。许多天主教徒建议将《圣经》记载的时间理解为更长的时段或地质年代的隐喻。对他们来说,《圣经》描述了宇宙的缓慢形成和物种的相继出现,这与科学的发现一致。他们于是对《圣经》这一神圣文本不可思议的现代性和科学预见性欣喜若狂。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ean-Paul II)1996年10月22日在宗座科学院的讲话中表明,梵蒂冈所赞成的正是此类解决方案;他特别肯定:“进化论已不仅仅是一项假设”,并邀请“教会和科学之间进行信任的对话”。以往宗教对书面文字进行象征性解释,这是神学信仰最常见的伎俩之一,目的是避免与科学知识对簿公堂。这样的话,宗教就制造了一种模棱两可,让其信仰无从辩驳。
但是,如果知识的发展进步干扰了信仰的表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当今普遍存在的这种认知模式竞争而欢欣鼓舞吗?通过与迷信、都市传说和其他阴谋论等思想腐化产物的自由竞争,客观的理性叙事是否最终会从中胜出?
但只要对现状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此类自由竞争往往导致各类轻信和盲从。21世纪初以来,某些现象已经被放大,它们还没有在网络上发酵就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对疫苗的怀疑、阴谋论以及各种缺乏根据的健康或环境警告层出不穷,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自2018年举行第一次国际大会以来,即使是地球扁平论者——“地球是平的”理论的捍卫者们——现在也有了一定的受众。他们还喜欢强调“团队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原文如此\]。我们拥有这么多关于地球是圆形的图片和直接经验,可是又如何解释这种古怪理论令人费解的死灰复燃呢?通过观看捍卫这一论点的视频——此类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不下上百万,包括著名意见领袖马克·塞根特(Mark Sergeant)发布的——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其中所有的论点都是可以反驳的,但它们还是很容易就能让那些毫无准备的头脑感到困惑。因此,这种极度边缘化的观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认知市场中的自由竞争为什么不能让这类武断言论直接消失呢?
某些令人轻信盲从的观点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是否可持续,或者从长远来看,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种心智模式的认知竞争将有利于那些论证最充分,且最接近符合理性标准的观点?如果不是瞎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它却提供了一个与已故的伟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对话的机会。读者应该记得,布东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一种进步的思想理论。显然,他意识到集体观点可能偏离方向(这是其作品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时,和托克维尔一样,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支持共同利益的观点最终将占据上风。在布东称之为“跨主体性”概念的论证基础上,这一“进化”理论同样适用于有关真假和善恶的观点,因为它们“能够被更多人认可,即使人们无法谈论它们的客观有效性”。
这一概念无疑值得进一步分析和阐述,因为它引导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某些思想的跨主体性确保了它们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具有某种形式的持久性和对其有利的传播性,因此,一旦这种性质的思想被强加于人,公众舆论只会盲从,不再做任何辩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描述性领域和规范性领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理性的“安全装置”(cran de sécurité),他也多次阐述论证这一观点。他喜欢举死刑的例子:死刑一旦被废除,其原则就不再被讨论。因此,这是一种乐观的进化论,是布东构思选择观点的方式。在他作品的最后部分,包括《价值感》(Le Sens des valeurs)和他的小书《道德的衰落?价值观的衰落?》(Déclin de la morale? Déclin des valeurs ?)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此,一个信念的跨主体性是由它向其他思想输出影响的能力来衡量的,至少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能力是在纯粹而理想化的认知市场中思维模式的竞争能力。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认知市场有其历史。某些观点占据寡头甚至垄断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跨主体性,而是因为它们得益于确保其持久性的扩散效应。Boudon (2003)然而,从理性规范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可以打赌思想认知的自由市场会催生论证最充分的认知产品吗?
我们可以援引布东的跨主体性概念来讨论这个假设。事实上,如果它能够理解认知竞争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将个人判断从主观决定因素中解放出来,那么它也涵盖了某些推断性欲望汇聚于一个放松管制的认知市场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虚假或可疑的想法几可乱真。问题是竞争是否总有利于最好的产品,抑或只有利于最令人满意的产品。在许多市场中,两者有时是同义词,但在认知市场上,它们描述的恰恰是有条不紊的思考和轻信之间的空间。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个问题,历史将有力地向那些可能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人宣示其历史性错误。
如果思维认识现在能够不断迭代演变并进入无节制的竞争,不仅是因为信息市场中占优势的新技术条件,而且还因为我们大脑的可用性更大。这些观点除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无论它们提出的是什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道德学说、政治纲领还是虚构小说,只有我们给予它一部分的大脑时间时,它们才能生存下去。碰巧,作为当下历史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样的可用大脑时间从未如此重要。
因此,我们眼前的情景前所未有:人类祖先的大脑遭遇了思维认知的普遍竞争,而这种竞争又伴随着迄今为止未知的大脑时间的释放。
在这场争夺注意力的终极之战中,谁会胜出?这是一个利害攸关的关键问题。因为在这个可用的大脑时间里,等待着我们的可能是梦幻般的安魂曲或癌症治疗方法,还可能会是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罪行或最令人心碎的文化产品。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学习量子物理学,也可以用它来观看猫咪视频。因此,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将是我们可以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政治性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对于被解放出来的大脑时间,我们应该用它来做什么?
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同时表明认知市场的竞争揭示出人类最深层次的愿望。换句话说,正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天性,能够让我们人类更接近一种务实的人类学。在所有可能的智慧文明中,人类会成为得以克服自身进化命运的那一个吗?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这个被解放出来的大脑时间,这是已知世界所有宝藏中最珍贵的瑰宝。
与我们自己的本性对抗的时刻将会到来。与所有的启蒙故事一样,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承认自己在镜中的亲眼所见。纵观历史,总有些人试图通过那些天真人类学的乌托邦计划来逃避这种反思,而他们——不可避免地——总是以糟糕的结局收场。他们想创建新社会新人类,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社会。与此相反,另一种计划迫使我们接受本性丑陋是最终宿命,它们糅合了我们最直接的直觉(有人可能称之为常识)和我们最迫切的欲望,以实现其纲领的政治合法性。它们往往采取民粹主义的形式,并且大量使用煽动手段。
其实还有一种出路,但通往它的道路异常崎岖。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