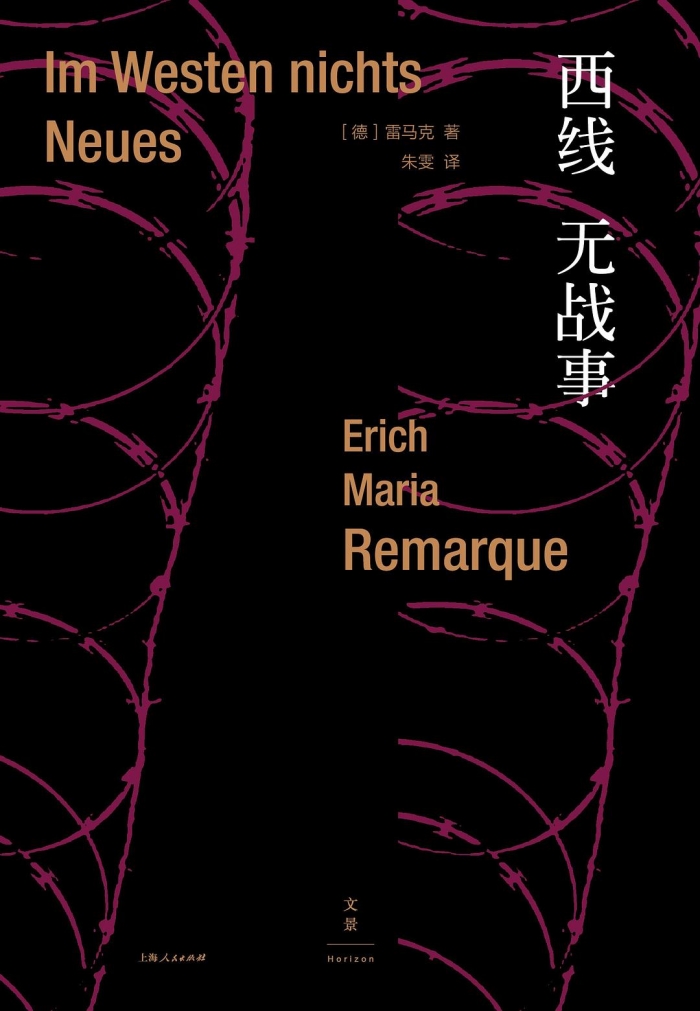第一次世界大战刺痛、侵蚀了那个时代无数德语作家的灵魂,内心深处盈满着哈布斯堡王朝情结的约瑟夫·罗特,怀缅着哀婉着昨日世界余晖的斯蒂芬·茨威格,以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1929年,雷马克的第一部小说《西线无战事》的出版令他声名大噪,随即于1930年被刘易斯·迈尔斯通改编为电影。通常情况下,作为两种不同的表现介质,一流的文学作品会被改编成为二流的电影作品,《西线无战事》成为了罕有的在文学史和电影史都被奉为经典的少数个案。2022年,《西线无战事》再度被爱德华·贝尔格改编后登上银幕,并在2023年的奥斯卡获得多项提名,更是成为了金像奖的热门候选,这部小说凭借电影的东风又再度重回大众的视线中,而时至今日它给读者们带来的那种震撼仍然是经久不衰。
一战爆发后,当时年仅19岁的雷马克意气风发,满怀憧憬,和同代的青年一样,他选择了自愿加入军队效力,那时年轻的他还不知道战争究竟是一个可以怎样将人如同草芥般碾碎的恐怖巨兽。透过小说的棱镜,雷马克让读者看到了他的反思。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他们的老师坎列托克会怀着令人感动的嗓音,以一种反问的方式诘问他的学生们:“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样的坎列托克成千上万,遍布全国,甚至于“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而他们只是在空谈宏大的口号、树立虚伪的旗帜,而这些崇敬与信任的他们的年轻人,就这么被这个扭曲的时代同样也是被塑造着这个时代的每个人,裹挟进了一场未知的血色洪流之中。约瑟夫·贝勒,最先阵亡者之一,那个迟迟不愿入伍的胖小子,最终屈服的原因仅仅是害怕被周围人疏远。从某种意义上,这不啻于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对于那些在小说开头尚未阵亡的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保罗·博伊默尔和他的战友们,世界业已断裂,“我们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孤独,是《西线无战事》这本小说的底色,这种孤独不仅存在于战场之中,更存在于战场之外。保罗·博伊默尔在中途仅有的一次休假回家中,雷马克全方位地向读者倾泻了这种极致的孤独环绕音。他先是透过保罗·博伊默尔的眼睛观察环境,他用了大量体现日常性的词汇短语“跟从前一样”“始终”“与往常一般”,这与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保罗·博伊默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他成为了家乡的异乡人,当他进入家门的时候,看见妈妈和姐姐在煎马铃薯的时候,雷马克用轻巧的不引人注目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滑入了他内心的缝隙,“今天肯定是星期六”——对于生存于暗无天日的战场上的人,日常生活的星期六是从来不会存在的。
面对母亲对前线的关心,他所回应的只能是欺瞒,他霎时明白了,那些生活在正常世界的人是不会懂得,不可能懂得,也永远不必要懂得他们所经历的地狱与噩梦。母亲赋予了他仅有的温柔,母亲希望他穿上便服,而父亲却强制他穿上军装,以便于自己带着儿子去熟人面前炫耀。人们和他攀谈,却并不是真的在意他们,人们所夸夸其谈的,通常都是他们狂妄自大不知何来的对于战争宏观、稀薄且空泛的想象。他们无论说的是什么,总要辗转到“跟自身存在意义有关的话题上”,而这对于士兵们是奢侈的,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意义的存在——活着,用尽全力活着。
战争将人异化,战场中的人将不再是人,这些人被战争驯化得和原始生活的人没什么区别——都只是在勉强地适应。而更可悲的区别在于,原始人通过发挥其精神力量而得到进步,士兵的内在则趋向于退化。在战场上,哲学、艺术、数学这些人类文明的产物对生存毫无助益,而他们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一种野兽般的原始本能。雷马克在小说中经常使用一种特别的风格印记——将人比喻为动物,且通常是直白的明喻。在雷马克的笔下,战争中的人是非人之人,这也引发了雷马克的另一种技法——双重表达,在一句话中,尤其涉及到主人公的心理表现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正是通过这样悖论式的表达,雷马克让我们贴近了一种隐秘的真实。
《西线无战事》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原因之一就是小说的两面性,小说堪称是“冰与火之歌”,一方面是关于战争的带着刺骨寒意的描写,同时又在这冰雪中斜插入一些带着温度的光线,例如关于自然环境的抒情的绘制;保罗·博伊默尔和他的战友说话从不自怨自艾,且有着互帮互助的同志情谊,雷马克甚至为了营造轻松感常为保罗·博伊默尔的讲话结尾增添上一个生动的语气词;在战争中昙花一现的温馨的情节——保罗·博伊默尔和卡钦斯基一起抓鹅炖鹅,偷渡到对岸与法国女人私会。但这种温馨与快乐通常有一个残酷的底片,这在小说一开头就已经折射出来。战士们得到了“平静的满足”,他们获得了双份的食物,雷马克在这里使用的是一种近乎轻快的语调“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这么多东西”,而这个计算错误的代价则是对面的一次袭击,导致了部队丢失了一半的生命。
《西线无战事》的细节丰满而挺立,对于日常与可怕一视同仁,如“我一跤摔进了一个开裂的肚子里,那上面还搁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子”。更多的细节则展示了残忍惊骇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由于不属于日常生活的经验范畴更令读者感到触目惊心,“他又跑了好几步,鲜血才像泉水一般从他的颈根里喷出来”,当然这种细节也包括了以主人公老兵视角出现的于细微之处的经验之谈。
小说设置了多个对照组,其中之一就是老兵与新兵的对照,这些新兵由于缺乏经验与运气,通常刚被当权者们投入战场便毫无价值地被战争机器屠戮,截肢病逝、成为残骸甚至死无全尸,一批批地就这么水波不兴的消亡了。小说的另一个相对隐藏的对照组是当权者和为国奋战的士兵,这些发动了战争的人一直隐藏于小说的雾霭,直至小说的后半段才缓缓出场——皇帝前来巡视。通过保罗·博伊默尔与朋友们的对话,雷马克发掘了一个尖锐而荒谬的事实真相——战争对皇帝也没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他发动战争的原因是“每一位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更荒谬的则是,皇帝检阅后,新东西统统要归还,“好东西不过是为检阅用的”。
这种极致的荒谬在小说临近结尾处达到了高潮,对方阵营中出现了一种足以摧毁一切的怪兽——坦克。坦克代表着毁灭。德国的战士们,单兵作战能力更强悍,单兵作战素养更优秀,但一切无济于事,对方的粮食比德国多,对方的飞机比德国多,对方的科技比德国先进。“我们根本是被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挤垮、逼退的。”士兵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从来就不是战场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一切付出归根结底是无法弥补战线崩溃的。2022版的电影版对坦克这一意象进行了完美的充满压迫力的呈现:浓雾中朦胧的坦克逼近,德军疯狂开枪但损伤不了坦克分毫,然后德军停火,一排排坦克终于浮现真身。然后坦克开火,德军在这样的冷酷兵器面前不堪一击。然后他们看到的是,电影里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坦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就这么毫无感情的碾压而过,人在坦克毫无还手之力,临死前的哀嚎,鲜血四溅喷射而出。
《西线无战事》在出版后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便售出了六十多万册,成为了那一代人心目中不朽的经典,但令人悲观的是,文学的力量似乎并不足以阻挡灾难的降临。纳粹党上台后,眼中自然容不得这个持有强烈反战立场的作家,他的作品被公然焚毁,他的国籍被强制剥夺,不得已只得流亡海外。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同样也是雷马克之后的作品中一直挥之不去的主题与症候——历时更长、规模更大、死亡人数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文/裴雪如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