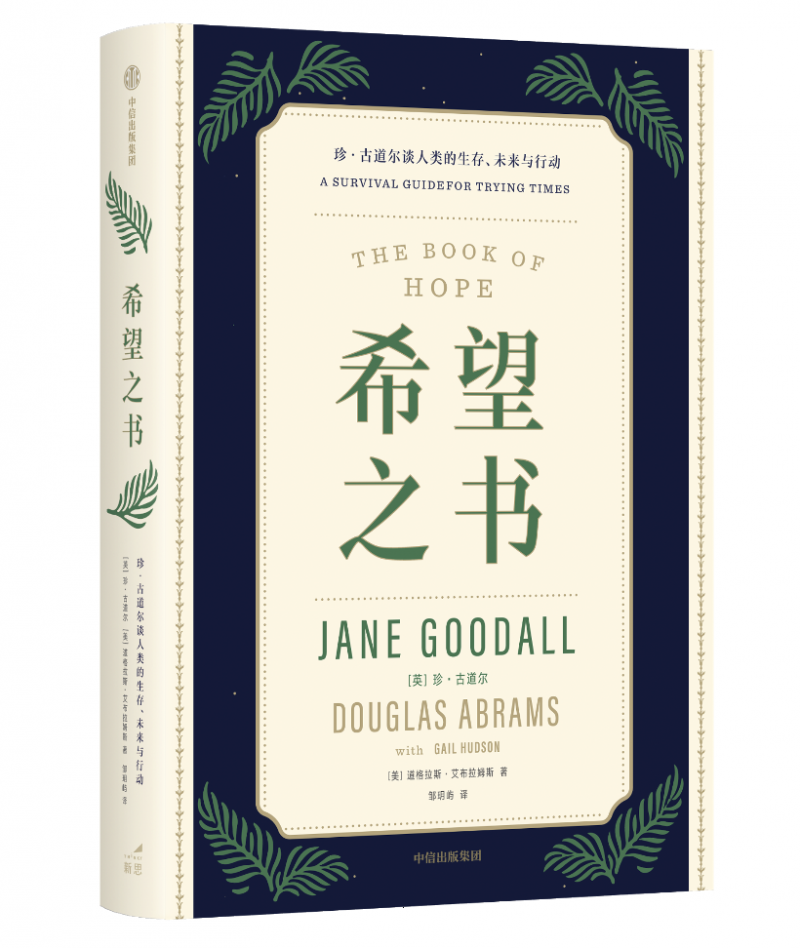希望是真实的吗?
“什么是希望?”我开口问道,“你会怎么去定义它?”“希望,”珍回答道,“它是一个能让我们在逆境中前行的东西。它代表我们的愿望— 想要什么事情发生的愿望,但也要求我们做好为之努力的准备。”珍微笑着说道:“比如说希望我们合作的这本书能成为好书。如果我们不下真功夫,它就不会成为一本好书。”
我笑着说:“对,这绝对也是我的一个希望。你说‘希望’是我们想要什么发生,但也需要我们做好努力的准备。所以行动是希望的必然要求吗?”
“我不认为所有的希望都需要被付诸行动。有些情况下你是无法采取行动的。比方说你人在监狱,而且是蒙冤入狱的,你可以希望能出去,但是你无法实施行动。我曾和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士交流过,他们因为设置动物监控摄像头被判了很长的刑期。他们自己并没办法做什么,但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争取,让他们早日被释放。”
这么说来,虽然行动和外力的作用对保持希望非常重要,但即使这些都不具备,希望在小小的监牢里也能顽强生长。一只白胸脯的黑猫从屋内慢悠悠地晃到了露台,跳到珍的腿上,随后舒舒服服地揣起爪子团成一团。
“我很好奇,动物会产生希望吗?”
珍笑了。“嗯,就拿这只名叫虫虫的猫来说,”她轻轻抚摸着猫咪说道,“它总是被关在屋子里,我怀疑它‘希望’能被放出来。当它想吃东西了,它会发出有些哀怨的叫声,一边蹭我的腿一边拱起脊背并轻轻摇动尾巴,这通常都会奏效。我很确定它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表达它希望被喂食。想想你的狗在窗前等你回家的样子,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希望的表达。黑猩猩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会发一通脾气,沮丧其实是一种失落的希望。”
所以说,希望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但我想我们可能得把话题拉回来,聊聊人类思维里希望的独特之处。我此刻想弄明白的是希望和另一个经常与之混淆的概念有什么不同。“世界上的许多宗教传统都用同样的口气谈论希望和信仰,”我说,“希望和信仰是相同的吗?”
“它们太不同了,不是吗?”珍说道,语气更像是陈述而不是发问,“信仰是你相信宇宙之上有着一种智能强大的存在,人们可能称之为上帝、安拉或者其他。你相信上帝是造物主,相信生死轮回或其他教义,这叫信仰。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是真的,但其实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去哪,并‘希望’方向是对的。希望比信仰更谦卑,毕竟没有人能预知未来。”
“你是说希望会迫使我们努力,好让我们想要发生的事真正发生?”
“是这样,在一些情况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拿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怕环境危机来说吧,我们必然希望一切都还不太晚— 但我们也知道,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什么都不会改 变。”
“所以,只要行动,就会拥有更多的希望?” “嗯,其实是双向的。除非你怀有希望,相信采取行动是有益的,否则你不会采取行动。你需要希望来驱动你,然后伴随着行动,你会生出更多的希望。二者相生相长。”
“那希望究竟是什么— 一种情感?”
“不,不是一种情感。”
“那是什么呢?”
“是一种关乎生存的东西。”
“一种生存技巧?”
“不是技巧。是一种更与生俱来的、更深层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天赋。快,想个其他的词儿。”
“‘工具’?‘源泉’?‘能力’?”
“‘能力’比较贴切。‘能力’加‘工具’。类似这样。但不是‘电动 * 工具’!”
我被珍的笑话逗乐了:“不是钻子什么的?”
“不,不是电钻。”珍也笑了。
“一种生存机制……?”
“这个说法要好一些,但没那么机械……”珍停顿了一下,试着找到合适的词。
“本能冲动?天性?”我继续说道。
“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特质’,”她终于得出结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特质’,没有它,人类就会消亡。”
如果希望是一种生存特质……我思索着,为什么有些人拥有的比其他人更多?它是否能在特别有压力的时期发展出来?以及,珍是否也有过失去它的时候?
希望可以被科学解释吗?
在我和珍决定开始合作一本关于希望的新书之后,我查了一些与希望相关的研究资料,这还是个比较新的领域。我惊讶地了解到,希望和愿望、幻想非常不一样。希望能够通往未来的成功,一厢情愿的愿望则不行。虽然它们都是关于未来,也都是充满想象的,但只有希望的火花可以点燃行动,带领我们实现所希求的目标。这一点,珍在随后的谈话中也反复向我强调。
当我们设想未来,我们可能有三种表现:我们要么异想天开,抱着宏大的梦想,自我娱乐成分居多;要么踟蹰不前,想着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在我的家乡,人们最喜欢这么干;或者,我们怀揣希望,在设想未来的同时认识和接纳不可避免的挑战。有意思的是,越是心怀希望的人越是能预见前方的障碍曲折,并且努力去排除万难。我因此了解到,希望不是一种盲目乐观的回避问题的方式,而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我仍然觉得乐观的人可能生来就如此,于是问珍是否也同意这一点。
“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有更多的希望和乐观精神,不是吗?”
“嗯,也许,”珍说,“但希望和乐观不是一回事。”
“区别是什么呢?”
“我完全没概念。”她笑道。
我安静地等待着,我知道珍热爱科学探究和辩论。我能看出来她正在思索两者的不同。
“嗯,我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乐观或者不乐观,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哲学。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你总会觉得‘嗐,都会好的’。与之相反的悲观主义者则会说‘唉,没有用的’。希望与乐观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执拗的决心,是我要想尽办法让它成真。希望是可以培养的。在人的一生里,这一点是会变化的。当然,对天性乐观的人来说保持希望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总是看到杯子里满的那一半!”
“我们的基因,”我问道,“能决定我们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吗?”
“就我所读到的,”珍说道,“有证据表明乐观人格可能部分源自基因遗传,但这一点完全可以被环境因素改写——那些生来不带有乐观基因倾向的人,也有可能发展出更加乐观和自立的人生观。这充分说明了孩子成长环境和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一个支持孩子的家庭环境能产生重大作用。这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这主要归功于我母亲,她对我的影响很深。如果我成长在一个不那么支持我的家庭,我会不会就不那么乐观了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无从得知。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一对同卵双胞胎的故事,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的环境里被抚养长大,仍然展现出了相同的个性。但就像我说的,环境能对基因表达产生影响是不假的。”
“你听说过一个关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的笑话吗?”我问,“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而悲观主义者害怕乐观主义者说对了。”
珍笑了:“我们确实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发展,不是吗?但我们也不能想着什么也不做,事情就能自己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珍这个务实的观点让我想起了我和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一段对话。他在把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里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忍受了诸多的悲惨遭遇和艰难困苦。
我对珍回忆道:“图图大主教有一次告诉我,乐观主义可能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迅速转变成悲观主义;希望则是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几乎不可动摇,他是这么解释的。有一次一个记者问图图他为什么乐观。他说他不是乐观,并引用《圣经》里的先知撒迦利亚的话说,他只是‘被囚而有指望的人’。他说,希望是即使被黑暗包围也能看到光明的能力。”
“是的,”珍说,“希望不否认任何存在的困难和危险,但也不会为它们所困。虽然周遭黑暗,但我们的行动仍然可以创造光明。”
“这么说,我们不仅能通过转变视角去看见光明,也能努力创造出更多光明。”
珍点点头:“采取行动并意识到我们能带来改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能鼓舞他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积累下来的行动会带来更大的改变。就这样我们扩散了光明,自然也能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多希望。”
“我总是不太信任那些针对希望进行的量化研究,”我说,“希望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一些有趣的研究似乎表明,希望对我们的成功、幸福甚至健康有着深刻影响。一项对上百个希望相关研究的总分析发现,希望可以将学术表现提高12%,将工作成绩提高14%,还可以把幸福度提高14%。你对这些怎么看?”
“我确信希望可以给人生的许多方面带来显著改变。它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能够取得多少成就,”珍答道,“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虽然数据非常有说服力,但故事比数据更能激励人们行动。很多人曾感谢我没有在讲座里引用任何数据!”
“但我们难道不想告诉人们事实吗?”我问道。
“嗯,那么我们把它们放到书的最后,那些需要所有细节的人就能看到了。”
“好吧,我们可以加一个‘延伸阅读’章节,提供给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在对话里提到的研究的读者。”我说道。接下来我问了珍一个关于希望的公共性的问题:“关于人对自己生活的希望和对世界的希望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
“假设你是一位母亲,”珍回答说,“你会希望你的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找到一份好工作,当个体面的人。对自己,你会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足以支撑家庭。这是你对自己和生活的希望。但你的希望也会自然延展到你所在的社区和国家,希望你的社区能够抵制会污染空气、影响孩子健康的新项目上马,希望选举出来一个好的政治领袖,让你的希望有更多实现的可能。”
很明显,珍说的是我们每个人既会有对自己的希望和梦想,也会有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和梦想。针对希望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我们对个人生活抱有希望的四个要素,这也许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世界的希望:我们需要树立现实的目标,和能够实现它们的现实路径。同时,我们还需要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信心,以及帮助我们克服沿途困难的支持。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希望循环”的四要素,我们有的各个要素越多,它们就越能相互促进,在我们的生活中激发更多的希望。
关于希望的科学虽然有趣,但我还是更关心珍的想法,尤其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这个话题还没来得及开始,珍在贡贝的同事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博士就过来了,告诉我们《国家地理》摄制组现在需要珍过去。于是我们停下了当天的对谈,计划第二天早上再继续讨论面对危机时的希望。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就在第二天晚上,希望会突然变成更加迫切急需却难以获得的东西——一场危机即将降临在我身上。
来源:中信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