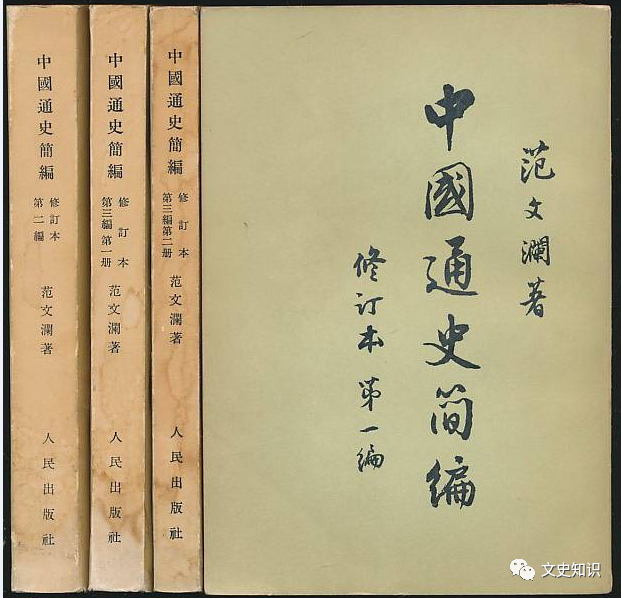光武帝的“柔道”与度田政令的“妥协”
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与东汉帝国的创立者刘秀(图1),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比如少时生活于社会底层,通过参加反对前朝暴政的农民战争而发迹,依靠家乡豪强、经过与各地割据军阀的斗争取得天下等。但在带动新兴王朝从战乱步入正轨的过程中,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治国理政策略,使得两汉前期的高层政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明人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括为:“光武与高祖不同,高祖阳明,光武阴柔。”
图1《历代帝王图》之汉光武帝刘秀,绢本设色,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所谓“阴柔”,指的是一种相对保守、温和、妥协的政治风格,“以柔道”行事,实际上是出身农家、历经坎坷、终定大局的刘秀对自己行事风格的评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记录光武帝生平业绩后,给出的评语是“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亦对这种以柔弱胜刚强的“君王南面之术”予以肯定。
光武帝“以柔道”“理天下”(同上),体现在他继位以后推行的解放奴婢、减免租赋、轻刑省罚、优遇功臣、任用循吏、推动儒学教育等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令举措中,安静执政,鲜少触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传统史家评论光武柔道,还时常举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开展度田活动,但最终向既得利益者妥协。
所谓度田,就是丈量田地,同时统计户口,目的是使中央政府能明确掌握全国各地的垦田、户口数据,在此基础上统一分配地方应当承担的田租、赋税和劳役。对于古代国家而言,控制地方的重要指标就是土地、人口这两项关键性资源,这些资源通常直属国家,但也有可能为地方豪强私占。理论上说,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经过新旧更迭时期的战乱,会有大量的土地、民户从私有者的遮蔽下释放出来;这些无主的荒地和农民能供国家支配,从而增加中央的税收和劳动力。
两汉之际的情况有些不同。西汉后期,尤其是王莽时期禁止土地、奴婢买卖的措施失败以后,国家管理失序,地主豪强跨州连郡兼并土地,而失去土地和财富者卖身为奴,沦为其附庸。而这些豪强恰恰是反对新莽的军事主力,至少是支持者,部分豪强拥兵坐大,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汉光武帝刘秀就出身于南阳的地主之家,他的建国之路,正是与豪强合作、对抗、博弈的结果。建武十三年(37)歼灭最后一个割据军阀——安定郡卢芳之后,光武帝仿效汉高祖,慰劳并分封随其南北征战的功臣,在中兴建武年间,先后分封了三百六十多位有军功者为列侯;而应他们的请求,多以首都洛阳和帝乡南阳附近的富饶县域为列侯封国。
南阳郡(今河南西南及湖北西北部)始设于秦昭王时期,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西汉后期王莽曾受封于此(新都侯),刘秀也生活在这里。光武帝刘秀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人,他的家族约在西汉元帝时期(前49—前33),因长沙卑湿而移居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今湖北枣阳南)。刘秀父刘钦先后为济阳(属陈留郡,今河南兰考东北)、南顿(属汝南郡,今河南项城西)县令,刘秀出生在济阳县舍;三十岁之前则主要在南阳活动;建武二年称帝后,以洛阳为都城。因而,东汉建立伊始,以宛(南阳)、洛(洛阳)为核心的区域,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这里的温和气候与肥沃土壤,也吸引了大量的皇室宗亲、功臣子弟在此购置田地、经营产业,形成一个庄园经济的“特区”。
这些东汉王朝的特权阶层,由于庄园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不能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合法的土地兼并,占田过限,宅舍逾制,隐匿户口、奴婢,私养家兵的情况成为常态(如《后汉书》卷三二记刘秀外祖父、南阳大地主樊宏“开广田土三百馀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由于他们地位显赫,侧近皇权,朝廷任命的刺史、郡守、县令长等,对这些庄园主的违法行为,往往只能包庇、隐匿。为了使岁末上计时汇报给朝廷的本地垦田、户口情况能看得过去,长吏常指使文书吏虚报数字、伪造垦田及户籍簿。
光武帝勤政,据说“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时间一长,自然能觉察到地方递呈上计文书中的问题。史载“(建武十三年后)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后汉书·刘隆列传》)。其实不用调查,光武帝也能知道簿籍数字不实背后的社会原因,隐隐指向南人功臣集团(从光武帝起事者除南阳人外,还有颍川人,袁宏《后汉纪》卷二谓光武初到河北,“公官属尽南方人”);但如果不厉行度田,意味着国家从建立之初,就无法有效控制辖内的土地、户口,必将重蹈西汉及新莽覆辙。事关国家利益,在推行这一政令时,光武帝表现出了相当坚决的态度。建武十五年四月,他指示各郡守、县令长彻查本地旧有和新开垦土地情况,丈量田亩、评定等级,同时开展人口普查,限期到首都洛阳汇报。
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陈留,光武帝出生地)太守在派遣属吏到朝廷汇报本郡度田执行情况时,反复叮嘱属吏,准备好相关资料(应是书写在简册或木牍上的文书)和汇报陈词,可以关注下邻郡的汇报情况;但千万不要主动询问河南尹、南阳郡的情况,当两郡属吏汇报时,也不要随意评论。或是为了备忘,陈留郡文书吏在上报文书册内夹了一枚木牍,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但没想到在御前汇报、呈奏书简时,竟忘了将这枚木牍抽出。光武帝发现后,询问木牍的由来,陈留吏自然不敢供出太守私言,谎称是在洛阳长寿街上捡到的,不详其内容。
光武帝大怒。其实皇帝本人与参加御前汇报的群臣,大概都对这句隐语的意涵心知肚明,但这一下子牵涉京畿地区多少富豪的利益!没有人敢出来明说,倒给了当时躲在帷幄后面、光武帝的皇子刘阳一个表现的机会。刘阳是光武帝最喜欢的阴贵人的儿子,刚刚被封为东海公,在当时也是储君之位的有力竞争者。
十二岁的刘阳忍不住对光武帝说,不要责备小吏,他应当是接受郡太守的命令来汇报垦田情况的。光武帝又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要强调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阳从容对答:“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光武帝闻此言,悦东海公聪慧(据说改立刘阳为皇嗣的想法,也是此时萌生的),陈留吏事件暂得解围。但此事也昭示着度田政令在河南、南阳等地执行无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派出专使(谒者)到各郡去考察二千石长吏执行度田及相关命令的情况;当查得已为大司徒的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并贪赃巨大的事实后,光武帝毅然拒绝了洛阳数千儒生为其求情(欧阳氏世授《尚书》,当时为儒学宗主),将其处决。
在对汝南郡进行追责后,光武帝又根据调查反馈,严惩了在度田中执行不力的河南尹张伋、东平国相王元、南郡太守刘隆(南阳功臣)、东海国相鲍永、琅邪太守李章、河内太守牟长等十多名二千石长吏,其馀得到处罚的官吏遍及司隶校尉部以及兖州、徐州、荆州等地。
朝廷强令度田并处罚包庇官吏,极大触动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建武十六年九月,引发了波及全国的武装叛乱。史书记载,各郡国的豪强大姓发动兵长、盗贼等武装力量,攻击代表朝廷执行度田的长吏,在青、徐、幽、冀四州最为严重。国家初建就遭遇暴乱,光武帝难免恐慌,除听群盗自纠外,不得不利用郡国二千石官来平叛,对他们已被查明的罪行给予赦免。平息叛乱的核心措施还包括:对武装力量的头目进行安抚,在一些地广人稀的郡国授予他们更多的田地。度田的初衷是要减少豪强对土地的非法侵夺,但最终又许之以良田美宅,政令的推行效果,肯定受到影响。
我们从光武帝事后的两次谈话,可以窥知他在度田遭遇挫折后的态度。一次是征询担任过多年陇西太守、他甚为信重的功臣马援的意见:
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上大笑。(《资治通鉴》卷四三)
虽然史家在对话中加入了“从容”“大笑”来粉饰帝王,从问话中,我们能体会到阴柔皇帝对杀戮二千石官的不忍和追悔。
平定度田引起的叛乱一年后,光武帝回到了家乡南阳郡的章陵(今湖北枣阳南),史书说他是去回顾往时宅院、看望刘姓宗室,并记录了皇帝与故乡亲友置酒言笑、其乐融融的一幕:
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
可惜光武帝已非“文叔少时”,而“宗室诸母”,恐怕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田舍贫妇,而是占田逾制的庄园主了。联系到一年前在这里发生的强制性清查田地、宅舍、户口事件,光武帝此行,应是为了安抚在度田活动中受到打击的南阳宗室豪族;而如果他没有向家乡的既得利益者妥协让步,也是不可能得到“谨信”“直柔”的美好评价的。
度田“失败论”与“持续说”
由于史书没有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的后续记载,而光武帝为平息暴乱,也确实向豪强地主等既得利益者做了妥协,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很多历史学者做出光武帝度田最终失败的判断。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图2)中认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人民出版社,1958)。黎邦正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析,“刘秀对抗拒度田者武力镇压没有效果。只好对豪强地主妥协让步,取消度田……于是大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徐高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提出:“刘秀虽然对农民的反抗以重兵镇压,但对豪强地主则采取妥协政策,最后只好取消度田,从此,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一代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一致认为东汉的度田活动在光武帝以后就被取消。
图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书影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评价:“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张传玺的《中国古代史纲》则指出:“刘秀对反对度田者发兵镇压,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虽然没有正面回应此后是否还有度田活动,但都认为度田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活跃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如韩连琪、王毓铨、朱绍侯、林剑鸣等,也都持类似看法(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 年第3 期;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3 期;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l982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随着对东汉史料的深入解读,学者们发现,建武十五年的度田活动,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政令,在此后的时间里,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曹金华在读《五行志》时,就注意到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续汉书·五行志》)
他指出,“诸郡新坐租”,应是指原先隐瞒户口、田亩的豪右,补交了少缴的租税;而发生在建武十七年二月的“新坐租”,很可能是建武十六年度田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在当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度田武装斗争,光武帝的度田政令仍然照常施行(参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4期)。这是度田“持续说”,因为只是依据相关史料的推测,缺乏直接证据,并未得到普遍支持。
直到1989 年,一项考古发现——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度田简,改变了许多人对于光武帝度田的看法。旱滩坡东汉简共十七枚,简文所见有建武十九年纪年,主要书写的是东汉初施用的律令条文;其中第十四枚简残断,整理者释文如下(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兼论“挈令”》,《文物》1993 年第10 期):“乡吏常以五月度田,七月举畜害,匿田三亩以上,坐”
很有可能是当地(武威郡)所抄写的行用田律或田令的内容。简文虽残缺,但可揭示至少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建武十九年前后,度田活动仍在持续,且由于时常开展,指导度田的相关规定才可以定著律令。二是度田活动在基层社会展开时,由乡吏具体负责,固定于每年五月进行;度田完成之后,乡吏要在七月份上报家畜有无病害情况;为避免度田不实,度田过程中隐匿达到三亩及以上者,要受到法律惩处。
有学者据此指出,光武帝度田不是失败了,而是在继续严格执行,并根据《后汉书·循吏传》中山阳太守秦彭农月亲度稻田顷亩、评定品级的记载(事在汉章帝建初元年),推测光武帝之后的明帝、章帝时期,也还在进行类似的工作(袁延胜《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 年第8 期)。
汉明帝、章帝时期继承光武执政风格,抑强扶弱,史家称颂其政绩“四民乐业,户口衣食滋植,断狱号居前世之十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华峤《汉后书》,《太平御览》卷九一《皇王部》注引),有明章之治的美誉。根据施政的连续性,似可推想度田政令在东汉前期的继续。但毕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到武威汉简提供的信息为止,我们只能说,虽然度田活动在推行过程中遭受到阻力,而光武帝度田的具体做法,也因地制宜做过一些调整;但终光武帝一朝,度田政令仍在被执行,指导度田的相关条规,甚至被纳入国家律令体系。
一份长沙临湘县小吏的度田报告
关于光武帝身后度田政令的实施情况,笔者可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件新出资料——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荆州长沙郡临湘县(郡治所在县,今湖南长沙)临时派出的一名在沮乡(临湘县属乡)工作的小吏伦(名伦,姓氏不详),向上级(可能是临湘县长吏)汇报本乡执行度田情况的报告。文书应系伦本人用浓墨书写在一枚木牍的正面,背面是用不同字体写下的文书传递记录(“邮行”)。
前面介绍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度田时,曾提到荆州南郡的情况,但主要看到的是中央和二千石官在度田活动中的博弈;而这枚木牍讲的是六十多年之后,同在荆州的长沙郡的度田,并且是县乡小吏叙述的基层社会执行度田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视角吧。两千年前的度田报告是什么样子,详见左图(图3),下文用现代汉语介绍。
图3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度田木牍(J1③:264-294,正背双面墨书)
元兴元年六月六日(公元105 年7 月5 日),沮乡别治掾伦叩头死罪,禀告长吏,今年我们接到了上级要求度田的指令,于是按照惯例,在农作物已经成熟的六月,进入沮乡界,对乡里的民户进行案比、并丈量每户所属的田地。我召集了乡属吏(乡小史)和乡内的一些特殊户口(高产田户及享有高级爵位的民户)为帮手,我们分为两组开展工作。我先带领种田能手陈祖、长爵番仲,乡小史陈冯、黄虑、蔡力共五人,去丈量郑尤、越与张昆三家的田地,因为人手充足,三家也比较配合,工作进展顺利。随后,因为只剩下两户了,工作量不大,我就让小史蔡力一人前往周本、伍谈两家去丈量田地;可能真是我大意了,傍晚时分,蔡力在伍谈家工作时,与其家人伍纯产生了争执,并由言语发展为肢体冲突,造成蔡力受伤。
蔡力回来向我汇报,我统计了下,他身体上总共有四处地方被打伤。伍纯恶意阻挠乡吏度田,按照制度规定,我带着种田能手陈祖、长爵番仲去伍家逮捕他,没想到他已经畏罪潜逃。我于是嘱咐认识潜逃者模样的蔡力和管辖事发地治安的亭长李道,一起去抓捕伍纯,务必要将其缉拿归案。
都是由于我的疏忽造成了这次特殊情况,惶恐地向您叩头,陈述事实如上。报告当天从别治掾所在的贼廷发出。
这件文书是考古工作者2010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的一个井窖内发现的,五一广场即东汉长沙临湘县治所在,所以应当就是别治掾伦发出给县内长吏的报告原件,保存在县廷(图文皆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6 期)。
通过伦的报告,可以知道由皇帝发起的度田政令在基层的执行情况,是由县廷派出属吏主管,但度量田地、评定等级、貌阅、案比户口这类具体事务,主要还是仰仗乡吏、亭吏,以及力田、高爵等经验丰富、可以调动的百姓中的头面人物。
还应注意到,长沙在两汉三国时代属于不适宜居住的卑湿之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其他区域相比也相对滞后,在当地可能尚未形成有势力的豪右大姓,肯定无法和河南、南阳、颍川、弘农郡比肩;伦和他的同事们度田的对象,只是三五户普通农家,原本以为不会遇到太大困难(不然不会仅派蔡力一人去伍家度田),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意外。度田牵涉赋税交纳与户口统计,即便是普通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难免会与官府产生摩擦。
从伦的文书,我们能体会到东汉度田在基层执行的难度,但也可以明确,度田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推行,并且有相当的延续性。光武帝以后,明、章、和诸帝都在坚持土地清查,并将其作为每年六月的一项例行工作。
“常态”的度田
度田是自上而下的政令,但其具体操作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大概是在每年五六月、田地里庄稼长势明朗的情况下,由县廷派出熟悉农田工作的专职掾史,驻于乡部或乡部外的临时办公场所,集合乡部、亭部属吏及民户中的力田、高爵等,组成工作组,分区分批深入,对一乡内民户的可垦已垦田、宅舍田等进行测量,可能同时案比户口(汉代为编制户籍进行的案比通常在八月);相关调查结果,最终会以乡为单位制作垦田租簿(如长沙走马楼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和户口簿。
这些簿书的正本通常就存留本乡,另外抄写一套副本(简册),上呈给县;县内保留详本簿书的同时,会将各乡的土地、户口数字进行集计(如青岛土山屯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有全县各类户口和田地总数),并上报给所属郡国;郡国一般只保留各县的统计数据,并汇总,形成郡一级的集簿(如江苏东海出土的尹湾汉简《集簿》),以供每年岁末上计中央;陈留吏上呈本郡度田木牍,就相当于上计环节。中央再汇总并检核各郡的上报数据,形成一个全国的垦田、户口数字。
度田工作跨越了东汉帝国的所有行政层级,在光武帝后,不仅得以延续,也成为政府重要的年度行政任务。这项工作的成效,当然是汉代国家对不同时期户口、土地数量的精准把握。《续汉书·郡国志》注的部分,因伏无忌(元嘉中曾受诏撰《汉纪》,则桓帝时仍在世)的记录,完整保留了从光武帝到质帝时期全国的十一组户口记录,以及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五个不同时期的全国垦田记录,比如冲帝朝数据:
冲帝永嘉元年(145),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
户、口数明晰,垦田数精确到步。不正是光武帝度田政令得以延续的最好说明吗?
由传世文献与新出土简牍之对照,我们得以贴近东汉一代度田活动之真相,度田并不是光武帝一朝之政,也并未因光武帝人亡而政息,而由诸帝接力经办,成为东汉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其实中国历史上像东汉度田这样,一开始以“非常”面目出现的政治事件,还有很多,由于见诸史料记载的后续反响的缺失(很多制度化的工作,史书只在制度初设时有所提及,而对于制度日后如何施行,常语焉不详),难免使人有这些非常、转折、改革、变革等,都是短命的、暂时的、断裂的感觉;如果被这种感觉误导,就很可能低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性,阎步克先生就多次强调这种“常态”和延续:
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10 页)。
作者:徐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8期“文史百题”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