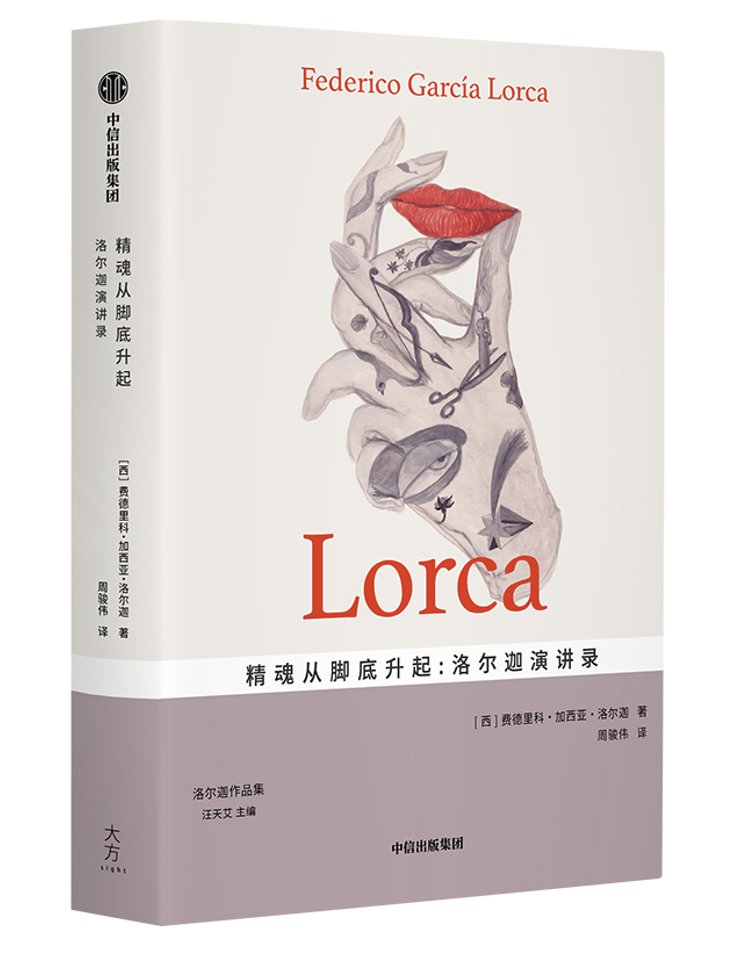女士们、先生们:
从我一九一八年住进马德里学生公寓,到我一九二八年完成文哲系的学业离开它,我曾在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听了近一千场演讲。不仅是我,西班牙的旧贵族们为了一改在法国海滨沾染的轻佻浮躁,也常去那里。
但当时我感到百无聊赖,十分渴望空气和阳光。离开的时候,我竟觉得周身被一层薄灰覆盖,仿佛它是辣椒粉,会刺我口鼻。
不。我不想让那只名叫“无聊”的蝇虫飞进讲堂里,用困意的细丝串起所有脑袋,还在听众眼里扎下一根根小小的针。
简单来说,鉴于我读诗的声音既没有实木的光泽,又没有毒芹的卷曲,还无法像绵羊一样忽然变作讽刺的刀刃,我就尝试给大家简短介绍一下潜藏在忧伤的西班牙背后的精神。
生活在由胡卡尔河、瓜达尔费奥河、锡尔河、皮苏埃加河撑起的公牛皮1里的人(还不用提那些靠近普拉塔河,被它狮鬃般颜色的水奔流涌过的其他河道),总会时不时听到一句话:“这很有精魂。”安达卢西亚大艺术家曼努埃尔·托雷曾对一个唱歌的人说:“你声音不错,也掌握了风格,但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因为你没有精魂。”
在整个安达卢西亚,无论是哈恩的巉岩间,还是加的斯的海螺里,人们总是提到精魂,并能秉着强有力的直觉,在它出现时准确捕捉它。
德布拉调创始人,杰出深歌歌者“莱布里哈人”曾言:“在那些我带着精魂歌唱的日子里,没人能比得过我。”老吉卜赛舞者“马蕾娜”有一日听布莱洛夫斯基弹奏巴赫时也惊呼:“哟!这弹得有精魂啊!”而她觉得格鲁克、勃拉姆斯、米约的音乐都很无聊;更有曼努埃尔·托雷(他血管里流淌的文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丰盛)在欣赏法雅演奏自己的《赫内拉利菲宫夜曲》时给出的这句绝佳的话:“一切拥有暗黑之声的,都有精魂。”没有比这更大的真理了。
这些暗黑之声是谜,是扎在沃土里的虬根。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它,却忽略它,但艺术的本质正由它抵临我们。西班牙人民说它是暗黑之声,这和歌德对精魂的定义重合。歌德谈及帕格尼尼时曾称那是一股“所有人都能感知,却没有哲学家能解释的神秘力量”。
由此可见,精魂是力量,而非劳作;是搏斗,而非沉思。我曾听一位年长的吉他大师说:“精魂不在喉咙里;精魂从内部攀上来,它是从脚底升起的。”也就是说,有没有精魂不是技巧的问题,它取决于是否有真正的、鲜活的风格,取决于天生的血脉,还有极为古老的文化与表演时的即兴创造。
总之,这股“所有人都能感知,却没有哲学家能解释的神秘力量”就是大地的灵魂,它和把尼采的心灼伤的精魂是一样的。尼采曾在里亚托桥上和比才的音乐中遍寻精魂的外在形式,不仅无果,而且还不知道他所追逐的精魂早已从古希腊诸谜团里跳到了加的斯的舞者们身上,或跳到了西尔维里奥唱的断续调中那无头的酒神式嘶嚎里。
所以说,我不希望任何人把精魂与神学上统领质疑的恶灵混为一谈(路德曾怀着些微酒神精神,在纽伦堡朝那个恶灵扔了一瓶墨水);也不要把精魂与基督教的魔鬼——那个愚钝、充满毁灭性、化身娼妓潜进修道院的魔鬼——混同;还有塞万提斯《关于妒忌和阿尔德尼亚丛林的喜剧》中马尔赫西的那只会说话的猴子,同样也不要把精魂与它混淆。
不。我所说的精魂黢暗、抖颤,是苏格拉底极乐精灵的后裔,它由大理石和盐构成,曾在苏格拉底饮下毒芹汁的那天被他愤慨地挠伤;也是笛卡尔忧郁精灵的后世,它渺小如一粒绿色杏仁,对圆形与线条厌倦不已,便顺着河渠逃出,只为聆听壮硕、沉酣的水手引吭高歌。
所有人,所有艺术家,尼采也好,塞尚也罢,在通往完美的高塔中每攀一级,就是在与他的精魂展开一场搏斗。这场斗争不是与他的天使,也不是与他的缪斯进行的——这和人们所说的不同。我认为必须要做这种区分,它对探明作品的根源至关重要。
天使指引、赠予,如圣拉斐尔;守护、避害,如圣米迦勒;通告、警醒,如圣加百列。天使的光耀令人目眩,但他在人的头顶之上翱翔。他高高在上,慷慨地赐人恩惠,人便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作品,或赠予同情,或翩跹起舞。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让保罗归信的天使,从缝隙里爬进圣方济各阳台的天使,抑或跟随着亨利·苏瑟脚步的天使,他们直接宣命。人们没有任何办法驳斥他们的圣光,因为他们直接在注定的疆界里挥动铁的双翼。
缪斯授意,也偶尔予人启示。相较而言,她能做的比较少,因为她太遥远、太疲惫(我曾见过她两次),人们之前不得不给她安上半个大理石心脏。受到缪斯感召的诗人能听见声音,却不知它从何而来。其实那声音就来自缪斯,是缪斯在激励他们,甚至有时宴飨他们——比如阿波利奈尔,那个被可怕的缪斯摧毁的大诗人。神圣如天使的卢梭就曾让缪斯与诗人同画。缪斯能唤醒智力,捎来石柱构建的风景和虚假的月桂气息。但缪斯常常是诗歌的敌人,因为她限制了太多,也因为她把诗人高抬到棱角锋利的宝座上,让诗人忘记,可能很快宝座就会被蚂蚁蚕食,或他的脑子里会掉进一只巨大的砷制龙虾。面对这些时,住在独目镜或小展厅的品红玫瑰里的缪斯便无能为力。
天使和缪斯皆从外而来。天使带来光芒,缪斯赋予形式(赫西俄德就是跟着缪斯学的)。无论他们化身金色面包,还是丘尼卡上的皱褶,诗人们都在自己的小月桂丛中接受他们颁布的准则。然而,要唤醒精魂,却要去到热血淌流得最遥远的几个房间里。要拒绝天使,踹开缪斯,还要不怕十八世纪诗歌里紫罗兰般的微笑和巨大的望远镜——因限制过多而病恹恹的缪斯正栖身其中沉睡。
真正的搏斗是与精魂进行的。
人们知道找寻上帝的道路:或是隐士们粗野的路,或是神秘主义者们精巧的路。要不就像圣女大德兰一般通过一座宝塔,要不就像圣十字若望一般途经三条小径。就算我们要借以赛亚的声音高呼“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但也不得不说,上帝最终还是给那些追寻祂的人递送了最初的火之荆棘。
然而,为了找寻精魂,却没有地图,也无从训练。我们只知道它把血液焚烧到如碎玻璃粉末一样,它把人的精力耗尽,它拒绝一切已经掌握的甜蜜几何学,它打破风格,它依赖无法慰藉的人间疾苦。它能让戈雅,这位原本掌握着最上乘的英国绘画中才有的灰色、银色、粉色的大师,用双膝、拳头和极为可怕的沥青般的黑色作画;它能让教士哈辛特·贝尔达格尔在比利牛斯山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它能让豪尔赫·曼里克奔走至奥卡尼亚的荒野上静候死亡;它能为兰波纤弱的躯体披上杂耍艺人的绿色外套;它也能给黎明时分在大街上的洛特雷阿蒙伯爵安上一双死鱼眼睛。
西班牙南部的大艺术家们,无论是吉卜赛艺术还是弗拉门戈艺术,也无论是唱的、跳的还是弹的,都知道如果没有精魂,一切情感都会沦为空谈。但有些艺术家弄虚作假,明明没有精魂,却要制造一种有它的幻象。这就是那些成天诓骗你们的毫无精魂的作者、画家、文学裁缝。但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不被淡漠无情牵着鼻子,就能发现陷阱,让他们带着那拙劣的伎俩逃走。
安达卢西亚歌者帕斯朵拉·帕翁,“带着发梳的女孩”,是属于黑暗西班牙的天才,也是想象力与戈雅或“金鸡”拉菲尔旗鼓相当的人。有一次,她在加的斯的一间小酒馆演唱。她耍弄着自己的幽灵之声,或凹瘪的铁罐之声,或青苔满布之声。她把声音卷进发丝,或坠至白葡萄酒里,抑或迷失在遥远晦暗的蔷薇丛中。但不行,完全没用。听众们一言不发。
当时在场的有伊格纳西奥·埃斯佩雷塔,他长相可爱,身形犹如古罗马的龟甲阵。人们曾问他:“你为何不工作?”他端庄一笑,仿佛自己是阿尔甘托尼欧斯,然后回答道:“我可是加的斯人,我怎么去工作?”
当时同座的还有“辣妞”艾尔维拉,塞维利亚的贵族妓女。她是索莱达·巴尔加斯的直系后裔,三〇年的时候曾拒绝嫁给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因为对方配不上她的血统。弗罗里达家族的人也在。人们认为他们是屠夫,但他们其实是千禧年主义的教士,现今仍在继续向格律翁祭献公牛。角落里还坐着大牧场主巴勃罗·穆鲁贝,他像戴着一副克里特面具。帕斯朵拉·帕翁唱完后,一片寂静。一个矮矮的男人,像那种突然从酒瓶后面窜出来的侏儒舞团里的一员,带着讽刺的口吻,兀自低声吐了一句:“巴黎万岁!”他仿佛是在说:“在这里,我们不关心你有多会唱,也不关心你的技巧,你的能力。我们在意别的东西。”
于是,“带着发梳的女孩”像发了疯似的拔地而起,浑身抖颤,活似一位中世纪的哭丧妇。她一口气灌下整一大杯烈火般的浓酒,然后坐下来开始唱,不用声音,不用呼吸,不用色彩,整个喉咙像被烧烂了似的,但……她有了精魂。她砸碎了所有关乎歌唱的脚手架,给那个暴怒的、所向披靡的精魂让路——它是载满沙石的风的朋友,会让所有听者撕扯衣服。而几乎在同样的节奏里,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们也在萨泰里阿教的仪式中,群集在圣芭芭拉像前焚毁服饰。
当时,“带着发梳的女孩”不得不撕裂声音,因为她知道在场的听众都是懂行的人。他们要听的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精髓;他们想听的音乐至纯,肢体精悍,能在空中浮荡。为此,她需要削减技巧和安全的因素;也就是说,那一刻她要远离自己的缪斯,变得无依无靠,而后请精魂迫近,屈尊与她赤手空拳地搏斗。她唱得哟!她的声音不再耍弄,反而因苦痛和赤诚变成一股血泉,打开就如一只手有十指,仿佛胡安·德·朱尼雕刻的基督像的双脚,被牢牢钉死,却满是风暴。
精魂的到来总是意味着所有形式的剧烈转变。在旧的层面上,它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好似新造的玫瑰,像奇迹一般,给人带来近乎宗教的热忱。
在所有阿拉伯音乐中,无论是舞蹈、吟唱还是挽歌,精魂的出现都会伴随着充满活力的致意,如“安拉!安拉”“上帝啊!上帝啊”。这和斗牛时人们说的“好哇”如此相似,谁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呢。而在西班牙南部的所有歌吟里,精魂总是伴随着一声声真挚的呼号出现,如“上帝万岁”。这呼号深沉、绵软、充满人性,来自与上帝的交流。因为精魂搅动声音与舞者的身体,人们得以通过五感与上帝对话。这呼号还实现了一场从世界出发的真正的、诗意的逃遁。如此纯粹的逃离,宛如十七世纪的绝世诗人佩德罗·索托·德·罗哈斯通过七个花园所实现的,也如约翰·克利马科斯用一架颤抖的泣诉之梯所完成的。
当然,在这场逃遁成功之后,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已经入门的人会看到风格是如何战胜贫瘠的内容的;而新手则会被一种莫可名状的真实感受包围。数年前,在赫雷斯的一场舞蹈比赛中,一位八十岁的老妪夺得了大奖。她仅凭高抬双臂,昂起头颅,在舞台上跺了一脚,就打败了一众腰肢如水的俊男倩女。但就在那样一场充满缪斯和天使的集会上,在那个形式美、微笑也美的场合,垂死的精魂拖着它被大地磨得生锈的刀翼,它要赢。最后它赢了。
所有艺术都能唤醒精魂,但精魂拥有最大发挥空间的,自然还是在音乐、舞蹈和诗歌朗诵中,因为诠释这几种艺术需要鲜活的躯体,也因为这几种艺术处于永恒的诞生和消亡中,它们在精确的当下构建自己的轮廓。很多时候,音乐家的精魂会传递到表演者身上;而有趣的是,在另一些时候,当音乐家或诗人没有精魂时,表演者也可以用他自身的精魂创造一种新的奇观,让作品表面上——仅此而已——看起来仿佛原先就是如此。例如精魂附体的埃莱奥诺拉·杜斯,她找失败的作品,而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它们成功;或者歌德所阐释的帕格尼尼,他能让真正平庸的旋律听起来深奥无比;又或者我在圣玛利亚港口看到的一位才女,她边唱边跳糟糕的意大利民歌《噢!玛丽》,但她的一点旋律、一些休止和一份用心让那件那不勒斯次品变得宛如一条巨蟒,浑身遍布真金。
确实,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新的,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给一具表达的空壳灌注了新鲜的血液和智识。
所有艺术,甚至所有国家,都有唤醒精魂、天使和缪斯的能力。比如德国特别亲近缪斯,意大利永远坐拥天使,西班牙则在所有时期都被精魂鞭策着前行。因为西班牙拥有历史悠久的音乐和舞蹈,精魂能在拂晓时榨取出柠檬的汁液;也因为西班牙是死亡的国度。西班牙是向死亡敞开的国度。
在所有国家,死亡都代表着一种结束。它一来到,人们便关上窗帘。在西班牙却不是这样。在西班牙,窗帘要敞开。许多人在家徒四壁中生活了一辈子,直到死的那一天,人们才把他抬出去。西班牙的死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死者都要鲜活:他的面庞就如理发师折刀的尖刃一般伤人。对死亡的戏谑,或来自死亡的无言凝视是西班牙人十分熟悉的主题。它横陈于克维多的《骷髅之梦》与巴尔德斯·莱亚尔那烂腐的主教之间;从十七世纪的玛尔贝娅在半路上死于难产,倾吐道:
我的血从心肝流淌出来
正在慢慢将马倾覆;
而你的马扬蹄
蹬出火花如沥青般黝黑。
到最近萨拉曼卡的一位年轻人被公牛所伤致死,哀号道:
朋友们,我要死了;
朋友们,我感觉好糟糕。
身体里已经有三条手帕了,
现在再塞一条就有四条了。
挤满栏杆的硝石花束间,是整个民族在探身观望死亡。若冷酷些,则持耶利米的经文;若柔情些,则倚芬芳的柏木。但在这个国家,一切最重要的终极价值都与死亡相关。
十字褡和车轮,还有尖刀和牧羊人锋利的胡须和蜕皮的月亮和苍蝇和潮湿的橱柜和废墟和镶嵌起来的圣人和石灰和屋檐和阳台伤人的边沿,这一切都在西班牙生长出了死亡之草。它们有其所指,也有自己的声音;它们微小,却对警觉的生灵来说可感可知。也正是它们,用我们自己消逝时那僵直的空气填满了我们的记忆。西班牙的所有艺术都和这长满刺菜蓟与硬石的土地难舍难分,这不是巧合;普莱贝里奥的哀叹或大师约瑟夫·玛丽亚·德·巴尔迪维索作品里的舞蹈不是例外;在欧洲所有叙事歌谣中,这一首西班牙的爱情谣曲脱颖而出也并非偶然:
如果你是我可爱的女孩,
那你怎么不看看我呢,你说?
我以前注视着你的双眼
现在投给了黑暗。
如果你是我可爱的女孩,
那你怎么不亲亲我呢,你说?
我以前热吻着你的双唇
现在扔向了大地。
如果你是我可爱的女孩,
那你怎么不抱抱我呢,你说?
我以前环绕着你的双臂
现在爬满了蛆虫。
那么在我们抒情诗初生的黎明时分,这首歌谣响起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花园里
我将死去,
在玫瑰丛中
我将被杀死。
母亲啊,那时
我去采玫瑰,
在花园里
寻着死亡。
母亲啊,那时
我去剪玫瑰,
在花丛中
找着死亡。
在花园里
我将死去。
在玫瑰丛中
我将被杀死。
苏巴朗画笔下被月亮冻结的头颅,油脂的黄混杂着埃尔·格列柯画中电闪时的黄,希贡萨神父写的故事,戈雅的全部作品,埃斯科里亚尔教堂的半圆形后殿,所有的彩色雕塑,欧苏那公爵宅邸的地下室,里奥塞科城的贝纳文特小堂里的“死亡与吉他琴”……与上述高雅文化等同的,是圣安德烈斯·德·特西多村的朝圣节(在他们的节日游行中,死者要占有一席),十一月夜晚,阿斯图里亚斯女人们手执火灯笼唱的挽歌,马略卡岛与托雷多的大教堂里女先知的歌唱和舞蹈,托尔托萨镇至暗的“缅怀祷词”,以及耶稣受难日的无数仪式。它们连同极为文雅的斗牛节日,共同组成了民众们关于“西班牙式死亡”的胜利。在这一点上,全世界只有墨西哥能与我的国家比肩。
当缪斯看到死亡来临时,她便关上门,或搭起一尊塑像底座,或展示一个骨灰盒,然后用她的蜡手写下一句墓志铭,但旋即又带着一股在两阵微风间徘徊的寂静重新浇灌她的月桂树。在颂诗残缺的拱顶下,她凄哀地拾起那些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笔下以假乱真的花朵,而后叫卢克莱修那只确有把握的公鸡去轰赶意料之外的阴影。
当天使看到死亡来临时,他便绕圈缓缓飞翔,用水仙与泪滴凝成的冰编织挽歌。我们曾看见那篇章在济慈,在比利亚桑地诺、埃雷拉、贝克尔、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手中颤抖。但是,当天使感觉到一只哪怕再小不过的蜘蛛栖停在他柔软粉嫩的脚上时,他那害怕的样子哟!
反之,精魂是不会来的,除非它感知到死亡可能会出现,除非它知道能填满死亡的家,除非它确信,那些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的,当下没有,也永远得不到安慰的枝条能被它撼动。
精魂热衷在深井边缘,伴着想法、声音、手势,和创作者进行坦诚的搏斗。当天使与缪斯携小提琴和节拍逃走时,精魂选择出手伤人。在这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恢复的过程中,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被创造出来的最难得可见的东西就留在了那里。
诗歌的魔力就在于永远被精魂附身,时刻准备用黑暗之水为望向它的人洗礼。因为有了精魂,爱和理解就变得容易,被爱和被理解也肯定能实现。不过,这场为了表达,为了表达得以被交流而进行的搏斗有时在诗歌上却足以致命。
大家回想一下极有弗拉门戈气质与精魂的圣女大德兰。说她有弗拉门戈气质,不是因为她矫捷地经过一头愤怒的公牛三次,并制服了它(尽管她的确这么做了);不是因为她在胡安·德拉·米赛利亚修士面前夸耀自己的容貌;也不是因为她扇过教皇使节一巴掌;而是因为她是极少数被精魂的标枪刺穿过身体的人(那不是天使,因为天使从不攻击)。精魂想要杀死她,因为她夺走了精魂最深的秘密。那是一座纤细的桥,缀连五感与那个鲜活肉体、汹涌波涛的中心——超越时间的爱。
圣女大德兰极为勇猛地战胜了精魂,与她相反的是奥地利的菲利普。菲利普渴求在神学和天文学中找寻缪斯、天使,却被冰冷又炽烈的精魂囚禁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宫殿中。在那里,几何学与梦境接壤,精魂戴起缪斯的假面,永远惩罚那位伟大的国王。
我们刚刚说了,精魂热爱伤口的边缘。在它迫近的地方,形式与一种热望交融在一起——那是一种比形式本身的可见表达更高的渴望。
在西班牙(一如在数个东方部落间,舞蹈是宗教的表达),精魂能找到无尽疆域之处,有加的斯舞者们的肢体,这是马提亚尔曾赞美的;有歌者们的胸腔,这是尤维纳利斯曾夸奖的;还有与斗牛相关的所有仪式。那是真正的宗教胜景,因为和弥撒一样,斗牛时人们也在崇拜和祭献一位神明。
在这个完美的节庆上,仿佛古典世界的所有精魂都聚拢来了。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人们伟大情思的呈现,它发掘了人最好的愤怒、最佳的暴躁、最上乘的号啕。没有人会在斗牛或西班牙舞蹈表演中嬉笑娱乐。精魂借由鲜活形态的表演,承担起令人受苦的职责;它还备好了梯子,让人逃离至周身现实之外。
精魂之于舞者躯体的效用,就如风之于沙。它用魔力,将一位姣美的少女变成月下的瘫痪者;或将脸颊绯红的青少年,变成在葡萄酒商店苦求施舍的跛腿老人。它能凭一头秀发复现深夜港口的气息,并在每时每刻操控舞者的双臂,创造出各种表达。它们是所有时代一切舞蹈的母亲。
但精魂永远无法重复。这一点很有趣,值得强调。精魂无法复刻,就像风暴中海的某种形状没法再度出现一样。
在斗牛中,精魂能展现它最摄人心魄的语调,因为它一面需要与死亡搏斗,死亡可能会毁灭它;另一面需要与几何学,与谨慎的分寸鏖战,这是斗牛最重要的根基。
公牛有它的轨道,斗牛士也有他自己的轨道。两条轨道之间有一个危险点,那就是这场可怕游戏的顶点。
一个人可以把斗牛红布的木杆归功于缪斯,把短扎枪说成天使的造物,然后佯装自己是一个好的斗牛士。但在引逗尚无任何伤痕的公牛,和在杀死它的时候,为了直击艺术本真,还是需要精魂的帮助。
在斗牛场里用莽撞惊吓观众的斗牛士不是在斗牛,而是在做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做的荒唐事:玩命。相反,被精魂啃噬的斗牛士能给人上一堂毕达哥拉斯式的音乐课,让大家忘记他在持续不断地朝牛角投掷自己的心脏。
从斗牛场的拂晓中,“蜥蜴”借罗马精魂,“小何塞”借犹太精魂,贝尔蒙特借巴洛克精魂,“卡甘乔”借吉卜赛精魂,共同向诗人、画家、音乐家们展示了属于西班牙传统的四条大路。
西班牙是唯一一个把死亡当成全国性盛会的国家。在这里,春天来临之际,死亡会吹响长长的号角;在这里,艺术永远被锋利的精魂统摄,并被它赋予截然不同的面貌和创造的价值。
精魂使孔波斯特拉的大师马特奥雕刻的圣人面庞充溢鲜血(这是雕刻史上的第一次)。同一个精魂,让圣十字若望连连呻吟,并焚遍了洛佩笔下十四行宗教诗里赤裸的仙女。
精魂筑造起萨阿贡的高塔,在卡拉泰乌德和特鲁埃尔打磨热砖。也是那同一个精魂,震碎埃尔·格列柯的密云,让克维多诗笔下的法警和戈雅画笔下的喷火怪仓皇逃窜。
下雨时,精魂搬出委拉斯凯兹,他藏在自己君王般灰色画作的背后,被精魂悄然附体;霰雪时,精魂展示赤身裸体的埃雷拉,让他向世人证明严寒杀不死人;起火时,精魂将贝鲁格特扔到丛丛火焰中,命他创造雕塑界的新空间。
当圣十字若望的精魂途经时,贡戈拉的缪斯和加尔西拉索的天使都要松手放开月桂花环。也是彼时,
负伤的小鹿
于山丘探身。
当豪尔赫·曼里克拖着即将伤亡的身体抵达贝尔蒙蒂城堡门前时,贡萨罗·德·贝尔塞奥的缪斯和伊塔大祭司的天使都该闪向一边;当梅那泣血的精魂与马丁内斯·蒙坦尼斯长着亚述公牛头的精魂要过路时,格雷戈里奥·埃尔南德兹的缪斯和何塞·德·莫拉的天使都该为它们开道;就像加泰罗尼亚忧郁的缪斯和加利西亚濡湿的天使也应该怀抱爱与崇敬,望向卡斯蒂利亚的精魂——它离温热的面包和驯顺的耕牛那么遥远,它的天总是被风扫净,山脊也总是干旱荒凉。
克维多的精魂与塞万提斯的精魂,一个携闪耀磷光的绿色银莲花,另一个携鲁伊德拉的石膏花,共同完成西班牙精魂的组画。
每种艺术都拥有一个形态、方式与其他艺术不同的精魂,这显而易见。但所有精魂的根系都汇聚在同一点上。从那里,曼努埃尔·托雷的暗黑之声流泻而出。它是木材、乐声、画布、语词中不受控制且惊恐战栗的终极材料与共同根基。
在暗黑之声的背后,在温柔的亲密中,有火山、蚁群、微风,还有硕大的夜在把腰肢抵向银河。
女士们、先生们,我竖立起三道拱门,并用拙手把缪斯、天使和精魂放在里面。
缪斯静止不动,她可以穿着织有细褶的丘尼卡,长着一双牛眼在庞贝古城目光凝然,或者像她的挚友毕加索给她画的那样,一个鼻子撑满四张脸。天使可以挥动安托内洛·达·梅西那的头发,拨弄利皮的丘尼卡,把玩马索利诺或卢梭的小提琴。
而精魂……精魂在哪里呢?那座空荡荡的拱门间,一阵灵魂之风袭来,它执着地刮过死者的头颅,以找寻全新的风景与未知的韵调。这阵风味宛如婴孩的唾液、新收割的青草、美杜莎的面纱——它宣告着新生物永恒的洗礼。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