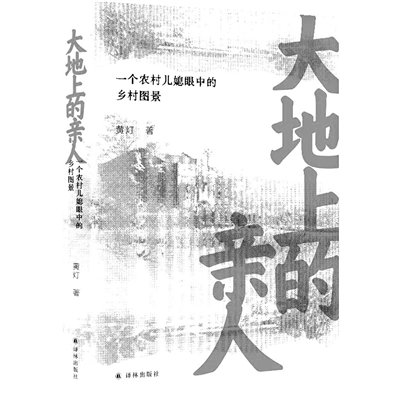主题: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作品分享会
时间:8月24日
地点:深圳南山书城
主持:作家、书评人 魏小河
嘉宾: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作家 黄灯
媒体人、作家 张小满
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网络爆火,引发全国范围内乡村问题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系统爬梳整理近20年来她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从丈夫家的哥嫂、姑姐、婆婆,到自己家的父亲、叔伯、子侄,再到外公家的舅舅、表妹、表哥,她在多重身份中转换,密切追踪50位身边亲人多年来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
前不久,《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在深圳南山书城,与媒体人、《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张小满,以及青年作家、书评人魏小河,围绕《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和内容,从各自鲜活的生活经验出发,聊到如何通过文字和行动重建与身边亲人的联系,如何看待当下乡村社会的变迁、对“打工人”的理解,以及非虚构写作等话题。
魏小河
从用文字重建到用行动 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魏小河:先请黄灯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黄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我们整个家族唯一的博士,我一直把我的读书上学的过程视为对我亲人的逃离。这并不是指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逃离,而是我越读越远、越读越远,我客观上跟亲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我有好多亲人也在广州打工,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城市,而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在读书,他们在打工,我们之间又没有共同语言,这个关系是不对劲的。
黄灯
2002年中秋节,我还在读博士,我的一个堂弟来看我。他比我小10岁,拎着一盒月饼和一箱牛奶来看我,对我说“你一个人在广州过节好可怜”。他当年才十几岁,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他觉得我很可怜。这是弟弟送给我的礼物,我当时心里好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没钱。我就问他说,身上还有多少钱?他说他很有钱的,还有50块钱。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好羞愧,因为在此以前我觉得应该离他们越来越远,对那个群体我天然很抵触,有点警惕之心。但是我堂弟在出生七个月就没有了妈妈,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写这本书最发自内心的一个动力,就来自这件事情促使我的反思。这件事情以后,在整个读博士期间,我跟我那些在广州打工的亲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每次过节都叫我去,我就会跑到广州的塘下村去跟他们吃饭、聊天、打牌。所以我前言为什么说“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就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和我背后那些没有读书的亲人,我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关系。
我在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是企图通过文字来建立关系,但是我在再版的时候加了一个序言,叫做“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家已经在老家建了房子,我经常回老家,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和我外婆的村庄逛,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化,几十年过去了,就像一场梦一样。对我来说,自己生命境遇的改变和亲人生命境遇的改变给我一个特别好的窗口,来审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甚至是审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写这本书源于一个很核心的动力,就是我企图审视我和我背后亲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读小满的书《我的母亲做保洁》的时候,我的共鸣感也很强。
用书写重逢亲人,更多的是记忆层面的
魏小河: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你怎么去看这句话,“用书写来重逢亲人”?
张小满:我大概只能认同一半。因为我觉得用文字重逢亲人,是写作带来的一个结果。我尽量不去凝视他们,而是要平视他们,看待他们的经历,但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呢。
对我个人而言,一个写作者能做的事是非常少的,那种重逢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上的东西,或者是我在跟人沟通交流过程中的东西。我的这本书能够重逢到的亲人是哪些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代。我的大姨小姨,她们那些读了大学的儿子女儿们,也就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们,他们会看这个,会给我发来反馈,会跟我说“姐姐,原来我妈妈是这样的”。包括我写了我姑姑,我表弟就会看,他会说他的妈妈原来经历了这些。
张小满
在写这个书之前,我当了很多年的记者,我们做记者有职业上的要求。隐私这一话题,在当下社会中有点过度泛滥了,比如说有一些内容是为公共议题服务的,或者是为一个主题服务的。对于我来说,我写《我的母亲做保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意识,我不是写我母亲的事情,也不是写亲人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套城市叙事。一个农民母亲来到一个超级城市,怎么与这个城市嵌合,她的思想观念以及她所有行动怎么与巨大的城市产生反差,在这个反差当中去体现一座城市的清洁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干净的城市背后有哪些劳动力在维持它运转。所以我的这本书本身不是一个群像故事,而是一个城市叙事的故事。
非虚构的出版伦理,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它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我认为隐私其实是写作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写任何东西首先要为自己的主题服务,为自己的表达服务,要尽量去准确,去克制,因为有很多隐私是完全没有必要写的。比如说如果我把别人的微信号写出来,那么这个细节是完全没必要的。所以,我觉得隐私的话题本质上是一个人写作技术的问题。
回望村庄的变迁找寻自己的故乡
魏小河:《大地上的亲人》写了三个村庄的变化,在几十年时间中,随着时代的潮流起起伏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里面写到的很多亲人早早就出去打工,他们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村庄变得更加空心,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请分享一下回家时的体会和观察。
黄灯:我讲一下我的观察。因为我回老家是非常勤,一年回去好多次。先讲一下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是观察农村最好的一个时机。农村在过年时都很热闹,比广州、深圳那些很热闹的街上都要热闹。过年那几天,我们湖南汨罗花桥镇水泄不通,是堵车的。但等到过完年以后,尤其正月十五以后,整个村子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这是人流的变化。
第二,农村现在房子越建越好,确实也很大,但是人很少。好多房子特别好,很漂亮,但锁着门。这个房子如果放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器物了,也没啥用了,但有可能这个房子就是一辈子打工人的心血。很多人离开农村去打工,但心里面还是想着要回到老家有个窝,但那个房子建好以后,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回到农村,因为他们还得在外工作。
第三,这几年,尤其是我写完《大地上的亲人》以后,农村的路变得越来越好了,新农村建设这一块功效是非常大的。因为路修好了,现在私家车也越来越多。我儿子很喜欢汽车,每次回家他就带我去观察镇上那些汽车,他说,我终于知道我们中国那些合资车的销路在哪里了。所以现在要真的再去写一本书,重新去观察我书里面写到的三个村庄,应该变化是特别大的。
魏小河: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谈到了故乡,那么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故乡感,才会让一个人活得更加有充实感或有意义吗?
黄灯:我觉得故乡感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不要盲目去有乡愁。故乡就是来处,就是根,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来处,或者说他是有来处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会更笃定一些。一个人的存在感与他的来源是有关系的。
一个人如果有故乡又认同自己的故乡,而且他还有故乡可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故乡还有亲人,跟自己有关的亲人,年龄越大他就越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可能你们年轻觉得还无所谓,巴不得越跑越远。
张小满:我基本上认同黄灯老师说的。大家要经常去寻找故乡,或者是去追问自己的故乡在哪里,但是要尽量少陷在乡愁这样的情绪里面。乡愁其实有一点诗意,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东西有乡愁,但是故乡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认同,是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确认我们的故乡在哪里,其实是确认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或者身份的一种重要起点。
比如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总觉得我们那个地方很贫苦,我要逃离那里。为什么后来在我更年长一些之后,我会回过头来去直面它,去写它,而没有去逃避它呢?这个过程是一个人真正能够成长或者变得成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回望、一种认同。哪怕是不认同,但整个过程对一个人是非常有意义的。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