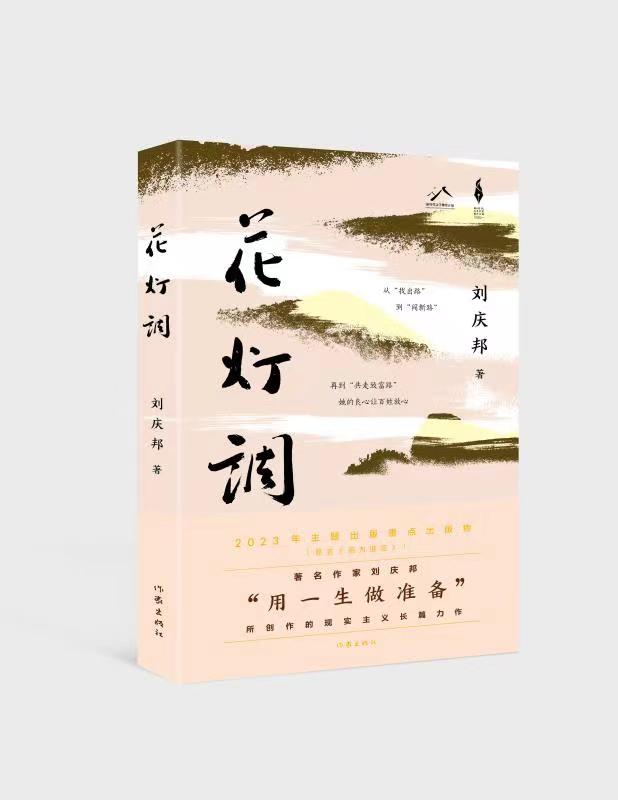文/刘庆邦
牛想喝水,自己会喝。牛不喝水,强按头是不行的。就算把牛头按得牛嘴触到了水面,它不张嘴,奈何?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某件事情,他心甘情愿,乐此不疲,才能做得好。如果他推推托托,别别扭扭,恐怕很难做出什么好活儿。写东西也是如此。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每写一篇东西,写什么,不写什么,事前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选择过程,也是说服自己的过程。不管写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散文,都须先把自己说服,然后方可动笔。春风不吹,花枝不摇。自己不服,何以服人?自己不感动,何以让别人感动呢?!
我刚刚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花灯调》,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其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好几天,我照样写作。在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说服自己,不是靠对自己讲多少大道理,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和自己所经历的事实都在那里摆着,你不服都不行。
用历史说服自己。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税赋,靠剥夺农民的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只是土里刨食,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只能是农民。这种悲惨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悯农》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普天之下,是农民通过种庄稼、打粮食,养活人类,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难道他们天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被剥削吗?什么时候才能根治这种历史沉疴呢?
好了,到了2006年,国家终于宣布,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从此结束了“完银子,交公粮”的历史。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农民种田所收不仅全部属于农民自己,国家还按田亩数给种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啊!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呢。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历史性工程。经过八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全地球、全世界、全人类的奇迹。此景只应天堂有,如今终于到人间。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进行的脱贫攻坚战,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必将载入华夏民族的史册。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此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难道不值得我们心悦诚服地书写吗!
用现实说服自己。我的老家在河南,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夏季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了一片泽国。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之后,村里的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很少,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度日。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的衣服,或是打满补丁的衣服。有的人好不容易做了一件新衣服,为防止衣服早早被磨烂,在做新衣服的同时,就在膝盖处和臀部打了补丁。更有甚者,有人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做不起,只能向别人家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
改革开放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般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还没穿破就淘汰掉了。要说问题,新出现的是衣服过剩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问题。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在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二姐的大儿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小超市,村里给其他村民发了购物券,鼓励他们就近在超市里买东西,以增加二姐大儿子家的收入。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用中外对比说服自己。全世界有一百九十七个国家,八十多亿人口,其他国家怎么样呢,还有没有绝对贫困的人口呢?我去过肯尼亚、南非等一些非洲国家,知道非洲几乎每年都面临粮食危机,大量人口在贫困的荒漠里挣扎,每年饿死的人都数以千万计。在坦桑尼亚,每天都有大约一千五百个儿童被活活饿死。我看过一幅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的照片,题为《饥饿的苏丹》。照片上,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头儿童趴在地上,在儿童身后不远处,立着一只和儿童身体差不多大小的秃鹫。食腐成性的秃鹫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那个濒死的儿童,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把儿童吃掉。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一幕。不光是欠发达国家存在饥饿的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有人填不饱肚子。在美国的西雅图,我看见有一个上岁数的男人,在街边的垃圾桶里扒来扒去。我以为他是捡废品,不料他是捡食品。扒到别人扔掉的半块面包,他当时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前面的街道上,我看见夜宿街头的流浪汉,身边放着一只纸杯,期望路过的人给他往纸杯里投一点钱。要是不缺吃的,那个美国人不会去垃圾桶里捡垃圾食品。同样,要是吃得饱、穿得暖,那个德国人也不会不顾脸面地在街边乞讨。这些贫困现象的存在,在非洲主要是自然条件不好和资源匮乏造成的,他们还没有能力实现脱贫。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原因造成的,他们不大关心穷人的死活。而在我国,“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共产党人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脱贫攻坚,才消除了绝对贫困,使全国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个人认为,贫富是相对而言,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都会有差距,不可能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水涨船高,再穷的人也不会穷到哪里去,至少可以做到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行不愁、上学不愁、看病不愁。举例来说,我还在农村老家的时候,去我们那里逃荒要饭的人很多,每到吃饭的时候,端着豁边子瓦碗挨家挨户要饭的人一个接一个,让吃饭的人都吃不安生。近些年我再回老家,连一个要饭的都看不到了。说起要饭,大姐说,要饭是舍脸的事,现在家家的白馍都吃不完,谁还去舍那个脸呢?对于这样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会有记载。可作为史料的记载,往往是客观的、简单的、粗线条的,一般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正好可以为历史做一些细节性的、情感性的、艺术性的有效补充。
自己说服自己。相比以上三个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似乎更重要一些,它是从外因到内因,从客观到主观,最终要落实在自己说服自己上。不必隐瞒什么、回避什么,我自己就曾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我九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贪吃的时候,可生产队的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可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爷爷一坐在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一些小蛤蜊,一嚼壳嚓嚓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黏液给我们喝。黏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是什么味,黏液就秃噜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皮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刮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的咽了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拉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煳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尽管有些饥不择食,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收拾,我还是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皮细腿。为父亲送葬时,当队长的堂叔担心我摔不碎老盆,替我摔了。去学校上学需要翻越一个干坑,每走到干坑前,我都视为畏途,翻起来十分吃力。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如果不写,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
总的来说,我国的脱贫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民生学、人权学、哲学、文学和人道主义运动方面的意义。对“运动”这个词,我们还心有余悸,往往讳莫如深。其实“运动”是一个中性词,而不是一个贬义词。运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它有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脱贫攻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言,真的很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以前的运动不同,这场运动不再是革命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福利性的。我之所以愿意用人道主义为这场运动命名,是因为以前有些运动不但不人道,反而反人道。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是文学的宗旨之一,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文人应该发出的真实的声音吧。
不少朋友、读者和兄弟姐妹对我说,我已经写了不少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现在的农村变了,跟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劝我该写一写现代农村生活的小说了。是的,五十多年来,赶上了能持续写作的好时候,我已经写了大量乡土题材的小说,中短篇小说且不说,在写这部《花灯调》之前,仅长篇小说就已先后出版了六部。《高高的河堤》写大自然对少年儿童心灵成长的滋养。《远方诗意》描绘农村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平原上的歌谣》记述中国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存韧性。《遍地月光》反思“文革”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伤害。《黄泥地》揭露国民性中的泥性。《堂叔堂》用一个个人物承载近代、现代和当代农村的历史沧桑。我每年都回老家,对老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动在心上,是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可是,不是我想写就能写。有了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不一定就能付诸写小说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写作契机的问题。小说主要是写人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好比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树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情感;并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新闻报道就可以承担,何必还要写成小说呢?我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驻村第一书记,以第一书记为主线,就可以把整部小说带动起来。
我还想过,回我们老家住上一段时间,详细了解一下我们村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并着重了解一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情况,看看能不能为我要写的小说中的挂帅人物找到一个原型。有了立得住的原型,整个小说工程方可以启动。还没回老家,我先后分别给几个堂弟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我们村从县里派下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是有的,但人家基本上没在村里住,他们对第一书记不是很熟悉。村支书也是我的一个堂弟,说起来,别的堂弟几乎都对当支书的堂弟有看法,说了不少负面评价的话。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担心写脱贫攻坚的计划有可能会落空。兵怕无头,将怕无主。小说中如果缺乏主心骨似的人物,既像无头的兵,又像无主的将,只能是一堆素材、一盘散沙。这让我想到文学创作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熟悉生活,可对某个地方的生活又不可太熟悉,太熟悉了,会先入为主,形成固定的观念,很难产生陌生感、新鲜感,影响想象力的充分发挥。
重燃写作欲望的契机出现在2020年的春天。这年5月,遍地鲜花盛开之际,《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作家,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市实地采访。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作家们马不停蹄,连续走访了不少地方,并走访了一个从深度贫困村脱贫的山村。去山村的路上,中巴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拐来拐去,驻村第一书记不失时机,在车上就开始给我们讲她的扶贫故事。她是一位女书记,她所讲的为争取扶贫项目多次流泪和哭求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印象。我心里一明,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获得“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嘛!她在六姐妹中排行老二,人称二姐。看见这个二姐,我想起我们家的二姐。我二姐也是早早入了党,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还当过县里和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两个二姐的心性有些相像,写遵义的二姐,正好可以和我们家的二姐互相借鉴。我们只在那个山村走访了半天,所得到的素材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相差甚远,我必须再次去到那个山村,定点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于是,在两年之后的2022年春天,刚过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我就独自一人重返那个山村,在山村驾校的一间宿舍住下,一住就是十多天。在山村期间,二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差不多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一会儿。除了在她的办公室里聊,她还冒着连绵的细雨,带我在山里行走。全村共四十一个村民小组,我们几乎都走到了。她对组组户户的每一个村民都很熟悉,我们边走边聊,走到哪里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常常是,聊到动情处,二姐满眼都是泪水,我的眼泪也模糊了双眼。我不得不摘下花镜,用纸巾擦擦眼角,才能继续和她聊。深入生活的结果,我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为这部小说初定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也许有读者会问,为什么给小说起这么个题目?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听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手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二十八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任何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就转到容量较大的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当她读时,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不止一次自我解嘲似的对妻子说,自己写的小说,还让自己这么感动,真是不可思议。还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看到或听到某些段落,上次流过泪了,这次仍要流泪。按道理说,预知那个地方可能会流泪,是不是可以硬起心肠,避免流泪呢?可是,不行,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感情似的,到那个地方还是不可避免地流泪。这可能是艺术接受心理中的一个谜,我没能力解开这个谜。要说魅力的话,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当然,眼泪付出的多寡,并不能证明小说的优劣。据史料记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金与朱光潜曾就作品中的眼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巴金称赞曹禺的《雷雨》让他流了四次眼泪,朱光潜不以为然,在《眼泪文学》中提出怀疑:“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靠得住的标准?”巴金看后有些生气,写了数千字的《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为自己的看法辩解,并批评朱光潜“少见多怪,缺乏常识”。我很想读读巴金先生的文章,但十度百度,都没有查到。我个人认为,人类作为情感质量最高的高级动物,眼泪肯定是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情到深处,感到高处,不管喜怒哀乐,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流下眼泪。情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审美核心,一部作品能否打动人,首先要看他的情感是不是真诚、饱满。而眼泪作为饱满情感外溢的一种表现方式,它的动人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臆”,还有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得我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访谈时曾经说过,人只重视流血,而不重视流泪,是不对的。用刀子随便在人的身体上拉一个口,都会有血流出来。而流泪不是那么容易,情感上达不到一定程度,你就是打死他,他都流不出一滴眼泪。
在“泪为谁流”之后,还有血为谁洒,心为谁操,力为谁出,苦为谁受。其中的“谁”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之所以最终把小说的题目改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有色彩,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灯是民间小调,有地方特色,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每当一部书面世,有的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什么时候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2023年1月29日(正月初八)至2月5日
(元宵节)于翰高文创园和光熙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