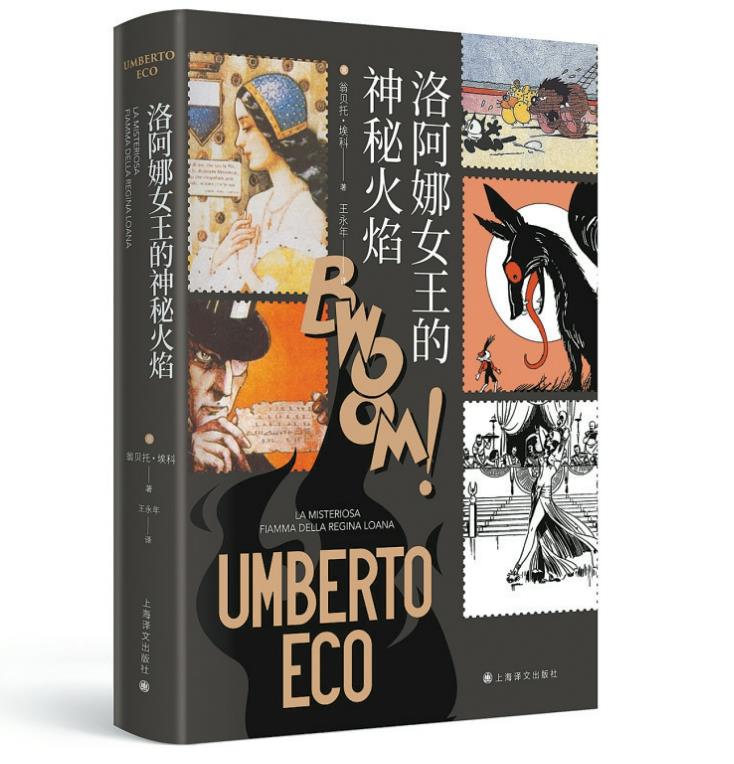翁贝托·埃科在小说《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的开篇,就种下了“反常的创造性”。这源于如潮水涌现的感官混乱,失忆失序。“我非但有失忆症,还可能有虚妄的记忆”。甚至,他想不起自己的名字,还不停瞎编错配。病人博多尼的叙述打开了知识的谱系——他看过很多书,像一部文学辞典,嘴里念叨着小说、人物与词条,回答问题依赖各种引文。“你知道,引文是我唯一的雾灯。”
从柯南·道尔,爱伦·坡,再到以实玛利,即使无意识行为也受控于这些文学路标。医生的戏谑如同作家自嘲:“下次我得把百科全书带来,据我判断,您的记忆力很好。只不过您记不起自己是谁了。”假如埃科生前患了逆行性遗忘症,大约就是这样。博学是一种泥淖,也是迷宫,学识负累反而编织更多幻觉,迷于津渡。引文,本质上是一种类比性思维:总是代替个人的新鲜印象、差异化描述,得出反射性联想。
巧妙的是,埃科靠镶嵌引文,实现小说的语境双关、意义之链。比如听闻女助手结婚,博多尼借用《审判》,说:“另一人拿刀扎进了他的心脏,拧了两下。”当她坠入别人情网,又引用“有人会摘你的花”。文本就像汇集了补丁与“弹幕”,非常有趣。所有潜文本,都作为链接,植入小说,达到意义的交互增殖。作家对叙述的大胆实验,我称其为:一个反常叙述者的自反性陈述。他考验叙事的极端限制与缺陷——即博多尼在丧失记忆和逻辑因果的病态下,如何靠知识累积,勉强连缀?
它意味着自我指涉的游戏——一个叙事者反而成为故事接受者,即客体化的主体。他“被告知”自己的经历,既不确定,又不可靠。小说充斥着妻子说是就是、大概应如是的叙述逻辑:“我未来的自传翻开了新的一页。执笔的是别人。”埃科似乎在暗示古典叙事者的通病:他们对人类、时代和世界了如指掌,却对经验性的自我构成不明所以。博多尼“听闻”自己的故事,包括家族成员、成长爱欲和经验事实,但一切都是表象。他能记住的只是父母的相片,而非父母本人。
《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翁贝托·埃科 著 王永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能指与所指断裂、实在和表象分离的危机。作家讨论重返历史对理解未来的奠基,观照时空观念中的身体感知。神秘的火焰,就是奇妙体感,仿佛在四维空间里,从内部挠到了幽门,如对女人泛起了新鲜欲念。洛阿娜女王是未知爱情、不明女人的观念物:“为什么她仅仅生活在我可怜的诗歌中?假如她不存在,我就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帕夏,把女人统统变成我假想的后宫里的皮囊……但是假如被神秘包围的确有其人,并且确实不为人知的话,又怎么样呢?”神秘火焰无法接近,即刻消融。没有形象,只有文字,诗的虚构把它写成文字而永存。
博多尼曾专修古籍史,和他的祖父一样,扎在故纸堆,开了一家“珍本工作室”。收购藏书、分析版本、赚取利润,这些话题都是埃科拿手好戏。他借收藏精微观察人心:等钱用的收藏家,竞争的同行,贵族的遗孀,盆满钵满的继承人……其中有智慧、狡黠,也有小聪明。病态,为故事赋予新奇,妻子和女助理全成了陌生女人,日常生活都变为闯关游戏。博多尼怀疑自己是否与西比拉曾保持过长久暧昧。他复盘情人间各式老套情状,因为失忆,没有羞愧。埃科用可能替换了事实,想象吃醋妻子和亲昵情人的多种场景。“它会不会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呢?”无法证实与证伪,糟糕的是,爱过却记不起来,便以为没有爱过。
如此,人物行为就包含多种义项,价值意义甚至完全悖逆。博多尼和西比拉,既可能放荡成性,也可能是一对绅士处女。“但是在这里,我四年的生命成了问题。”他改装了精神分析的套路,我称为人物正在“意识”他的潜意识。这位古董书商,是百科全书和“时间集成”的人格化形象。失忆之书,将故事本身变为目录和探佚。第二部“纸的记忆”,是重返儿时索拉拉宅邸,进入记忆岩洞的万千路径。此作的创造性,可视为意识流小说之新进展——知识流的自由联想,图像化的情节移涌。“仿佛一个单词能引来一千个,或者能添枝加叶扩大成一个内容充实的摘要。”
它衍生出超越文本的图像志——大量书籍插画、画报杂志,形成了记忆物证。作家展示追寻逝去时光中的恋物癖,繁复藏品都是自带历史、标记空间的索引。“图画会引起短路,擦出火花,一幅画能导出三千字。”描述性开始胜过叙述性,它开始对记忆进行理解、分类与编录。小说陷入对装帧、插图的描摹,或谓“看图作文”的模式,也不过分。它不断追问,画面的情节性如何渗透、形塑了自我意识,“我”的故事又在哪里?埃科探讨知识的来源生成,但并无秩序,混乱的词条通往博物学的幻象。“我从过去迷雾中慢慢挖掘出来的一切开始变成了我的现实。”
“我们生活在期待、注意和记忆三个时刻,任何一个时刻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两个而独立存在。你由于丧失了过去而无法朝将来延伸。”其实质说明,人的存在,也面临飞矢不动的古老命题,丧失动态关联与因果总体,是可怕的。“从长远来看,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却是另一回事。我不理解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什么意思”。它归结为,人只能是时间性的持存。
从深层看,小说潜藏了作家的自我批判与反思向度。书斋式、学者化小说,到底是高级设计,还是一种“技术懒惰”?小说里医生的阐述,完全可类比写作类型与技艺。他将记忆分为内隐型和外显型两种,前者对应生活常识的自然习得,后者则是语义的记忆。博多尼对书本内容一清二楚,却对自己的生活情节一无所知。“拿您的情况来说,这一类型的记忆似乎相当发达,讲老实话,甚至可以说太发达了,我只要稍加输入,您就会形成我不妨称之为学究式的记忆,或者援引一切陈词滥调。”
它指向学院小说家不断弱化情节性、剔除自我的生活性。“您没有丧失语义记忆,您丧失的只是情节记忆,也就是说您生活中的事件。”即使这不免过度阐释,但置于小说创作上,原理却相通。在埃科以往名作中,大多有假托和“迷古”之趣味。无论《玫瑰的名字》《波多里诺》还是《傅科摆》,会在海量文化符号里找到暗黑中世纪、修道院秘闻、神学历史的“拟境”,却很难发现作家自我的实境。
换言之,埃科偏于靠博学写“历史虚像”,他爱把小说乔装成研究、寻访或转译的扮相。《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揭开了他“无名”“无功”的写作心态,小说是自我愉悦与戏谑同行的手段。“这个世界的人们不是阅读就是写作,作家们写作,有的是出于对同行的蔑视,有的是希望自己写一些好东西,不时翻阅翻阅。”埃科属于哪类?他大概两者皆是吧。
(原标题:失忆之书与小说图像)
文/俞耕耘(作者为青年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