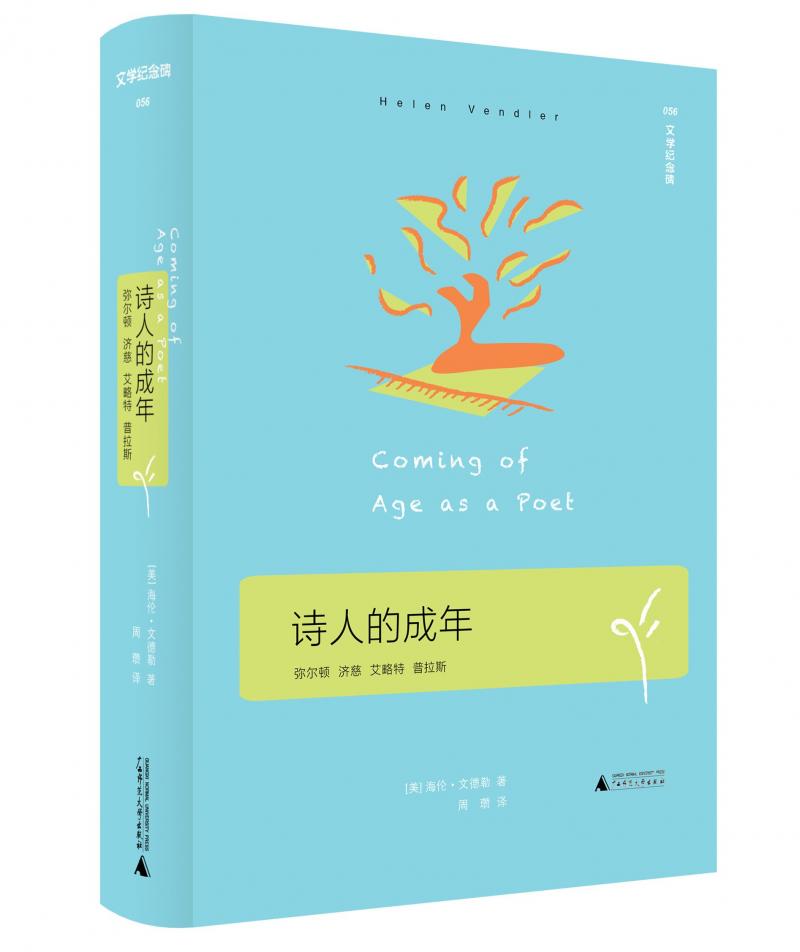找到一种个人风格对于作家而言即意味着成年。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最近推出的《诗人的成年》中,著名诗歌评论家文德勒从弥尔顿、济慈、艾略特和普拉斯的诗中分别选择了一首具有突破性的诗歌,四位诗人,四篇诗歌,四段创作之路。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其结构、意象和格律,她指出这些诗歌如何标志着每位诗人掌握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
由文德勒教授在“詹姆斯·默里·布朗讲座”基础上整理、增订而成。书中回溯光耀诗史的英语诗人艺术实践与试验的历程,阐释其在二十几岁青春年代如何沿循诗学传统的来路,在历史和现实中汲取话语与修辞,实现自己第一篇“完美之作”的关键性突破,摆脱先辈的重负与庇荫,在诗歌中极大延展时间和空间之域,找到连贯持久的个人艺术风格,在句法、语言节奏、想象力、文体、哲学和审美上达致成熟自洽的境界,并最终一跃而为举足轻重的诗人。
《诗人的成年》[美] 海伦·文德勒 周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 \ 2023年3月
文 | [美] 海伦·文德勒
译 | 周瓒
在本书四篇论文里,我分别考察一位年轻诗人,考察他们写出第一首“完美”诗歌之前必须完成的作品,而这首完美之作第一次完全成功地展现了一种明晰连贯的个人风格。对这位年轻作者而言,探索一种风格具有难以形容的紧迫感;在美学层面上,它类似于个人对身份认同的心理寻求,亦即寻求一种本真的自我以及展现它的合适手段。人类对认同的寻求被盲目引导;我们发现,作为青少年,我们经受过令人费解的,一系列显然随机的偏好、厌恶、迷途和逃避。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为何我们的感觉会在莫名冲动、悲伤和赞美的波浪中四处飘忽,只是后来我们才可能准备好,像华兹华斯一样,承认身份认同的形成方式有多么奇妙:
多么奇妙啊所有
恐惧,痛苦,和早年的困厄,
遗憾,烦恼,怠惰,全都混合
在我心灵中,我本该承担的部分,
也是必要的部分,以组成
这属于我的平静生命,当我
无愧于我自身!
(1850《序曲》, I, 344 350)
华兹华斯从早年的困苦、遗憾和恐惧中,觉醒为一个成年人,追寻一种宁静的存在,这种存在源于自我的自觉意识,不再被年轻人的情感变迁所惑。
在这段引诗中,华兹华斯细述了人类个体形成的正常过程。但对一个青年作者而言,其利害关系是双重的。年轻作者不可能不依赖风格的持续演化而追求一种朝向成人期的演进。找到一种个人风格,对于作家来说,即意味着成年。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无意识发生的: 在随意与有指向的阅读中,青年诗人不知不觉被一些前辈吸引,而发现另一些乏味无趣,对那些不久将会被发现的人毫无察觉,排斥一些他们觉得毫无魅力的前辈。但一位诗人的终极风格,一部分则是被挑选的(通常是对可获得的话语的反叛),譬如: 写风景而非写人;诉诸神话或相反;在一个封闭的逻辑形式内操作,抑或更直觉化地变动;接近或偏离大众化;个人化或非个人化写作;安栖于即将变成习惯的明确的形式或诗节;等等。
我们将见识四位寻求风格的年轻作者: 约翰·弥尔顿、约翰·济慈、T. S. 艾略特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细察这几位诗人写下的第一首“完美”诗作,我之所以视之为“完美”,因为这些诗富有信心和控制力,以及首要的——放松,作为诗人,每个人都迎来了他们的成年。我称这些诗为“完美”,因为它们以令人难忘的诗行发声,显示了一种明晰而安排得当的独特风格;人们不希望它们是别的样子。这样一首诗是读者能认出“弥尔顿式的”或“济慈式的”的那种诗: 亦即,这种风格显然是延续的,至少部分延续至这个诗人后来的作品中。那是一首即将在诗人全部作品中成为典范的诗作: 它的想象力如此独特而深刻,技艺又如此与其雄心相匹,在需要介绍这位作者的早期作品时,一位选集编者或教师很可能挑选它,而更年轻的诗人往往会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逮住它——从模仿到戏仿,但都反映了创造性的吸收。我选择四首诗——《快乐的人》《初读查普曼译荷马》《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巨像》,尽管它们创作于几位作者的青年时期,却展现了文学的持久力。(为了提升我们对于诗人在寻找一种成年风格时发现的感觉,我有时会把这些早期“完美”的努力,与完成度不足的,或之前的令人难为情之作,或更“进步的”后来之作做对照。)
我着手于此项主题,部分原因是人们普遍相信,任何写下的非齐行排列的文字都有理由被称为诗。从最广义——即韵文(verse)与散文(prose)的区分——上来讲,的确如此。但是,在其最充分的意义上,若要获得“诗”之标签,这个韵文片段必须达到近乎超人的完成度。它是一位作者的产品,这位作者无论多年轻,都已经在诗歌里度过了一段紧张(而成功)的自我学徒期。这正是爱默生深以为然的事实,在回应惠特曼送的礼物《草叶集》时,他推想在那卷诗集中,那些充分完成的诗歌是经历了一个“长长前景”的结果。(瞥一眼青年惠特曼《草叶集》之前的散文与诗歌,即可确认爱默生直觉的精准。)这种创作上先于一位作家最佳早期作品的长长前景,通常是有迹可循的(正如在济慈、艾略特和普拉斯那里一样),而有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我们知道,比如弥尔顿,历时数年锤炼其艺术,恰好在写出他最早的现存诗歌之前。弥尔顿在十二岁之前,与导师交换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诗歌;而在十六岁离开圣保罗学校之前,据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称,弥尔顿创作了“许多诗稿: 或许使得他很好地进入更成熟的年纪”。而所有这些诗作都失传了。
诗人学徒期的履历经常被读者忽略,这些读者只是在诗歌选集或选本中读到诗人成功的诗作,因此那些不可或缺的探索性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可能会从视野中消失。而如果缺乏在诗歌方面的学院训练,新的读者往往觉得很难将想象力和语言都很出众的诗与那些伪装成自由诗的胡乱分行的散文区分开来。在这里,我希望展现出,对于少数青年少作的尊重(所有诗都写于作家们二十多岁时)优先于任何著名诗作的创作,这些少作显示了他们私密、热烈乃至英雄般的努力和忍耐。创作中的艺术家赖以为生的这类孤独之作——它在内在紧张下的耐心,它对自身必然性的信念——都被艾米莉·狄金森简练地描述过了:
每个——它艰难的目标
必须实现——它自己——
通过默默一生的
孤独的勇毅——
努力——是唯一的条件——
对自己的耐心——
对反对之力的耐心——
以及完好的信念——
旁观——是它的观众的
专长——
但业务——被不赞同者
所协助——
“观众”和“赞同者” 稍后才来,并由此给予诗歌声名。但是“艰难的目标”和“孤独的勇毅”首先光顾这寂静的房间。
这位青年诗人需要在风格上取得怎样的发现呢?他需要习得一种支配性的风格规范(细致到技艺最微小的细节);伴随着对抒情诗媒介的这种意识而来的,是心理上逐渐察觉到那些关乎精确表达内在情绪和态度的难题。诗人也需要识别外在感觉世界的突出元素,这个外在世界肯定了他别具一格的想象力;设计他本人独有的时空轴;决定将居于其作品之中的生物或非生物;并且最终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宇宙学或形而上学的存在框架,在此框架内,这首诗的活动能够发生。让我稍稍谈论一下这些风格实验中的每一种。
首先,正如我已谈到的,在早年试验期间,诗人即已获得各种直观的技术发现。年轻的诗人同时(通常不太坚定地)在许多方面大步前进,学习如何明敏地使用声音(音节、词语、短语和诗行的声音);节奏(抑扬格和扬抑格,四音步诗行和五音步诗行,词间顿与断行,语调与措辞);句法(包括个人独特的句型);以及更大的形式单元,例如诗节与十四行体。 为了创造出听上去像是一种个人自我的声音(一种可以变化而且也确实在变化的自我,从心理学层面看,甚至每分每刻都变化),年轻的诗人会集中于技艺的磨炼——改变、改进和偏移已经学会的事物,发明新的途径。直到其中一些技巧开始(经过多次重复之后)本能地起作用,年轻的诗人才有机会写出一首出色的诗。诗人还需要学习掌握风格动机的连贯性和合理性: 一首诗不能在态度和态度间、声调和声调间失控地偏离方向。诗人必须发现对其不断展开的材料的适宜支配方式,以实践那种风格规范,弥尔顿在《论教育》中把它称为“用来细察的伟大杰作”。
伴随着在语言元素上展开的实验,诗人必须确认并为构成物质宇宙的地理与历史元素的显著存在找到词语,让这个物质宇宙有选择地在他的诗中得以再造,就像华兹华斯发现(地理而言的)群山和村舍以及(历史而言的)法国大革命与恐怖行动,将其作为他内在世界的组成因素。如我们所知,弥尔顿打算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诗人,最终会选择在他再造的世界中囊括神话和地理的空间及神学与历史的时间内所发现的几乎所有一切。这种无止境的容纳对于如乔治·赫伯特这样一位写私密对话的诗人来说大可不必;但是弥尔顿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映照他笔下那种能够触及他独特感性世界的广阔。
在他们找到贴合自己感受性的语境材料和抒情主人公之前,青年诗人们所经受的挫折,观察起来往往既滑稽又痛苦,当然,承受起来则更加痛苦。另一方面,一旦得到所需的细节,他们便欣喜若狂: 当艾略特在波德莱尔阴冷的都市场景中,准确地找到他需要的物质的卑污,在他的随笔和书信中,兴奋溢于言表。
在开发个人风格的过程中,青年作者们不仅要发明一种精心挑选的有关外部世界的言语拟像,而且还得为他们核心的精神困境找到一整套相应的象征对应物。我们知道,对于弥尔顿而言,是诱惑与美德之间的张力;对于济慈,是感官接受能力和通往“哲理”的艰苦意志之间的矛盾;对于艾略特,是讥刺的反讽和心灵的热望之间的冲突; 对于普拉斯, 则是“ 女性特质”与一种向往力量的内驱力之间的对抗。第一首“完美”之诗可能只显露内在于人的这种争斗的一半;尽管如此,它所揭示的东西是本真的,而且至少其中的一些将会持续下去。
至此,在我所做的讨论中似乎诗人只倾心于表达对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的单一感受,但是通常还有某种更大的共同体在他的诗歌中索求一个声音。即使年轻作者是位抒情诗人,而非史诗诗人或叙事诗人,他也必须采取一种社会立场,一个直面他人的位置。这种立场可能是一种拒绝(依据道德规范,如弥尔顿),一种包容(如在济慈的友情扩展中);或是敏锐但疏远的一种迷恋(如艾略特);或一种家庭控诉(如普拉斯)。谁会生活在青年诗人的社会世界里呢? 有时候似乎那个世界只是被血亲占据着(正如在洛威尔的《生活研究》中)或被神祇主宰(如在赫伯特的《圣殿》中)。确定一个人想象性作品中生活的居民,以及此人与那些居民的关系,是正视青年诗人的要务之一。作者们通常只是在最初可能会弄错这些在心理学上适合被描述的特定居民: 弥尔顿曾考虑写作关于英国历史名人的史诗,但是,他发现他的想象力更深地响应着那些有关圣经的叙事。在沉浸于田园牧歌的同时,甚至在理解全部代价之前,济慈就写下了从性爱结合的孤独到社会整体的悲剧的必要通道:
……在一个枝繁叶茂的世界的怀抱
我们安静地栖息,像两颗宝石蜷曲
在珍珠壳的壁龛中。
而我终究能否告别这些快乐呢?
是的,我必须舍弃它们以求
更高尚的生活,我要找到
人类心中的痛苦与冲突……
( 《睡与诗》,119 124)
然而,济慈直到一八一八年才将一八一六年的这个预言付诸实现,当他将文学忠心从斯宾塞转向莎士比亚。而在去世前,普拉斯已将向外凝视的方向从单一的抒情自我转向家庭群落———但是在她有关家庭的隐喻中(从大西洋巨缆到大屠杀),她已经开始撒出一张更宽广的社会网络。
最终,为了总结这份不断扩大的,需要学习与发明的事物的最小清单,年轻的诗人必须想象一种超越尘世元素、内在冲突和社会关系的世界宇宙体系,并为其找到一种风格。弥尔顿在此方面因其发明而著称;但是,即使像普拉斯那样困于家庭的诗人,也必须扩展自我,达致一轮统驭的月亮,或达致如这样的诗行所言,“固定的星星统驭一个生命”。①对于济慈而言(即便是否认),他也必须去描述北极星的坚定,必须通过他所声称的“神圣的季节”,认识到过程与死亡的必然性;艾略特则朝着旋转着的世界静止的时刻看去,这个世界被俯冲的鸽子所主宰。
这份通往一个成年诗人身份的风格路径的清单还可以扩展,但提醒读者的话我已说得够多,在诗歌中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就之前,一个诗人必须进行多少技术工作、内省和想象性的慎思。当然,当我们熟稔这位作家后来的作品,以后见之明重温它,这第一首“完美”的诗可以被看作某种偏爱之作。不过,我在这里总想放弃这种后见之明,而只期望走得像每一位年轻诗人那样远。我想看到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看到的,当他们设法在一两页间,上升到想象性的力量与审美的轻松。接着他们自然会继续获取更进一步的目的: 我们能在弥尔顿那里——当他从《快乐的人》前行至《幽思的人》——看到那些更庞大的雄心,包括后者有关学习和预言时代的幻象,这在前一首中是没有的。我们能在另一些诗人那里看到一种类似的更大欲望的增升:在济慈那里,是在他准备越过十四行体,写作第一部长诗《恩底弥翁》时;或者在艾略特的构想中,在他的普鲁弗洛克式二人组“你和我”之后,进入《荒原》中各式各样人物出场的场景;而在普拉斯那里,是对她自己早期作品中的“文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修订中。我们这四位诗人在写出第一首“完美”之诗后持续地改变。但是我们在此打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一个非凡的时刻,达到了如史蒂文斯(在《球状之初始》中) 所称的“拉紧最后一环的圆度”。
在详述中,对于新读者来说,我需要介绍一些学者们熟知的信息,包括熟知的事实与对这些著名诗作的看法。但是,在每个个案中,我希望能为我所处理的诗歌增添些新认识。
在这篇引言中,我完全没有论及诗人如何找到一个“主题”——抽象观念,或概念,或寓意,而它们会将声音推进为充满激情的言说。一个主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以下论文中,我会谈论与强力有关的内容,以及在每个个案中造就了这些被选择的诗作的有关概念。在诗人一生中,主题会不断改变。从来不会改变的,是诗人在每一首诗中的需要——无论是何主题——即典范性,一种与感觉压力相称的想象的象征对应物,一种匹配的、独创的技艺,安置在时空轴上的突出的尘世元素,社会关系(或由此生发的一种反社会关系)以及在这首诗的活动中隐含的一种形而上学和宇宙学。任何一首“完美之诗”都应展现这些元素中令人信服的一项优势: 没有它们,诗的主题就将缺少生机,它的寓意将转瞬即忘。我们作为读者,诗人作为作家,二者都参与了这一必要的信念,即,正是这种急迫的主题驱动着作家。虽如此,但正是写作赋予主题以生命。在这些完美而年轻的词语星群里,它是如何实现的,这是接下来的章节讨论的问题。
(节选自《诗人的成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