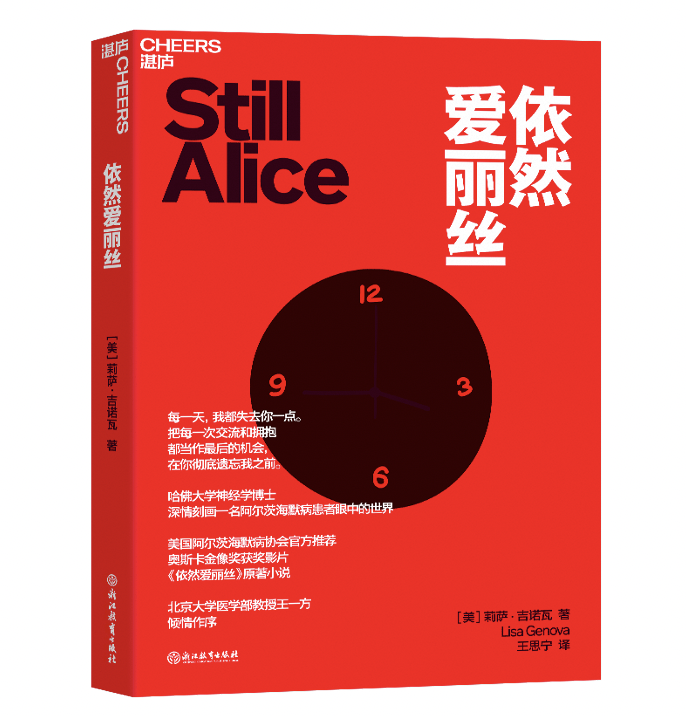爱丽丝第一次想到去那个地方看看是在确诊后一周,但她没去。幸运饼干、星座、塔罗牌、养老院她都提不起兴趣。虽然未来的每一天都在向那种生活靠近,她却不急于去瞥一眼。这天早晨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突然给了她足够的好奇心和勇气去看看奥本山庄园护理中心内部的样子,但她就是去了。
大厅没有什么吓到她的地方。墙上挂着一张海景水彩画,地上铺着一张褪了色的东方风格地毯,一个眼妆浓重、有着甘草一样深色短发的矮个女人对着前门坐在桌后。大厅简直像个酒店大堂,但是淡淡的药味儿以及没有很多拉着行李箱的来往客人和礼宾人员让它显得不对劲。住在这里的人是住户,不是客人。
“请问需要帮忙吗?”女人问道。
“啊,需要。你们这里收不收阿尔茨海默病病人?”
“收的,我们有一个区是专门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准备的。你想参观一下吗?”
“好的。”
她跟着女人走到电梯门口。
“你是在帮父母看吗?”
“是的。”爱丽丝撒谎了。
她们等待着。电梯和这里住的大部分人一样,又老又迟钝。
“你的项链真漂亮。”女人说。
“谢谢。”
爱丽丝用手指摸了摸锁骨和项链上的蓝色浆料石,这是她母亲留给她的新艺术风格的蝴蝶项链。母亲从前只在纪念日或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戴这条项链,爱丽丝也一样,把它留给特殊场合。但是她最近的日历上没有标记任何正式场合,而她爱这条项链。于是上个月的某天,她穿着 T 恤和牛仔裤试了一下项链。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她喜欢看到项链上的蝴蝶。她记得自己在六七岁的时候听说蝴蝶只能活几天,于是为后院里蝴蝶的命运哭泣。母亲安慰她说,不要为蝴蝶悲伤,它们的生命短暂,但那不意味着它们的命运悲惨。看着它们在阳光下,在自家花园里的雏菊间翩翩飞舞,母亲对她说:“你看,它们的一生多美啊。”爱丽丝希望自己能记得这段记忆。
她们在三楼下了电梯,走在铺了地毯的长长走廊里,穿过一道没有门牌的双开门,停了下来。女人指指在她们背后自动合上的门说:“阿尔茨海默病特别护理中心的门一直是锁着的,不知道密码就出不了这扇门。”
爱丽丝看着门边墙上的键盘。数字是上下颠倒的,而且从右到左反着排列。
“密码锁的数字为什么是那样的?”
“哦,这是为了防止住户们知道并记住密码。”
这似乎是没必要的预防措施。他们要是能记住密码,就不需要住这里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们家病人目前有没有这个问题,乱走和夜里不安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常见行为。我们允许住户随时四处走动,但也得保证他们的安全,防止他们走失。我们不会在晚上给他们打镇静剂或者把他们关在房间里。我们尽可能帮他们保留自由和独立。我们知道这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很重要。”
一个矮个子的白发女人走到爱丽丝面前,她穿着粉色和绿色交杂的花卉图案家居服。
“你不是我女儿。”
“抱歉,我不是。”
“把我的钱还给我!”
“她没有拿你的钱,伊夫琳。你的钱在你房间里。去看看你衣柜最上面的抽屉,我记得你把钱放在那儿了。”
女人用怀疑和厌恶的眼神看着爱丽丝,但还是听从了权威的建议,拖着她那脏兮兮的白色绒毛拖鞋回了房间。
“她有一张二十美元的现金,她总是藏起来,担心别人会偷走。当然了,然后她又会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儿了,总是说别人偷了她的钱。我们试着让她把钱花掉或者存进银行,可她不肯。有一天她会忘记自己有这二十美元的,那时候就消停了。”
她们摆脱了伊夫琳偏执的盘问,继续去参观走廊尽头的公共活动室。房间里的老年人坐在圆桌旁吃午餐。仔细看了一眼,爱丽丝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老年女性。
“只有三个男人吗?”
“实际上,三十二个住户里只有两个男人。另外一个是哈罗德,他每天都来跟他妻子一起吃饭。”
也许是又想起了童年时“亲女孩会染虱子”的规则,两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男人单独坐一桌,跟女人分开来。桌子之间的空间都被走来走去的人填满了。很多女人坐着轮椅。几乎每个人都是白发稀疏,凹陷的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显得更大了。他们吃饭的动作非常缓慢,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没有谈话,甚至连哈罗德和他妻子都没有交流。除了吃饭的声音,就只剩一个女人边吃边唱歌的声音,她脑内的“唱针”不停地在《银月之光》的开头跳动,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制止她,也没有人鼓掌。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