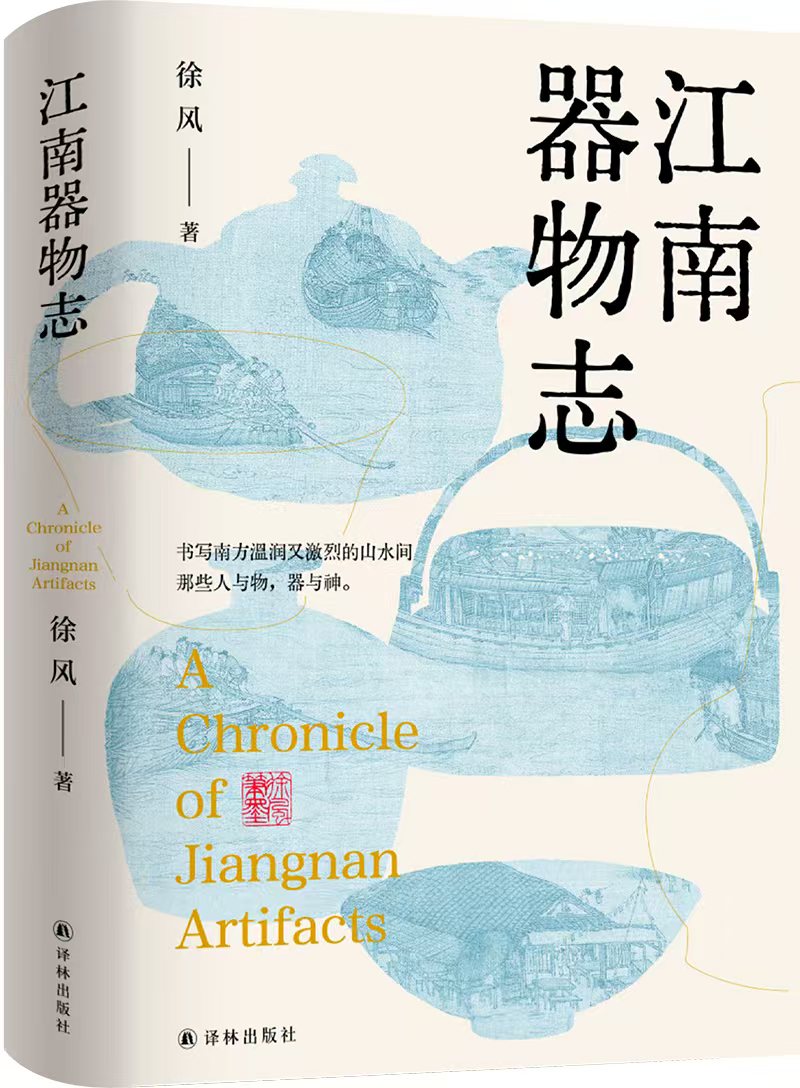继《江南繁荒录》《做壶》《包浆》后,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中国好书”作者徐风推出长篇系列散文《江南器物志》,本书经《收获》杂志“江南器物”专栏连载,由译林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并入选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此次,徐风将目光拓展至更广阔的江南器物谱系,以“器隐镇”为文学道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书写南方温润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
“器物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风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通过追究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以及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根系与旁通。作者以十年田野调查为根基,行走于多个江南文化现场,通过纪实与推演交辉的“器物志文学”叙事,让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举人的竹编考篮,毛竹里揉进汗渍的盐霜;素娥们的织布土机,缠绕着未尽的情丝;当铺门前的青石板路,凝固着无数人生的轻与重。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所言,“物质即记忆,一物一世界,通过这些与器物相关的风华、执念、恩德、慈悲,徐风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情义,一个地方的灵魂,以及那些至今难以释怀的心痛与欢悦。”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打捞“非遗”精魂,在器物的绵延意象中,《江南器物志》不仅复原了江南传统生活,也让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丰盈的折射,最终指向器物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与生活美学。
以物观世:“器物志文学”搭建江南版“清明上河图”
“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庭院、舟车、服饰……都是中国文化语境里永不破败的肉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单、食谱、药方、茶道、风水、方术、古玩、字画,亦是中国古人精魂里不可磨灭的诸般星宿,乃至茶馆、酒楼、当铺、钱庄、塾馆、文庙、诊所、会馆、别院……都是人世间必不可少的驿站港湾。”
《江南器物志》以一座江南古镇“器隐镇”为场域,用十个故事单元切入古镇民生的方方面面,通过对诸多器物的聚焦,开创性地建构了“器物志文学”的概念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传统的风物志写作,以器物为棱镜,深度折射江南地域的民生百态与精神脉络;将具体的“匠艺”实践,升华为承载“文心”与“人心”的精神载体,实现了从物质性到文化性的深刻跃迁。“器物托志,古今皆然;地理绵密,凉热同心。”本书是徐风融汇地方风物与个人思辨的成果,也是他在“江南器物”方向的深耕之作、创新之作。如评论家汪政所言,《江南器物志》既是徐风器物书写的上阶突破之作,更是思索江南风土与历史文化的深沉之作。
在徐风笔下,官人、细民、文士、商贾、民女、捐客、丐徒轮番登场,由人写器,由器观世。他深谙器物与生活的共生关系,每一件器物都成为开启特定社会空间与生活纹理的钥匙。从龙骨水车到犁耙锄钎,从碗碟盘盏到鼎龕鬲匜,作者在温习稻饭羹鱼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试图在人与物、器与神之间,“构建一条神性通道,去汲取一隅之丰沛,与广袤的世界进行无处不在的对话。”
作家的“小小的野心”,起始于用文字搭建、还原的一座烟火漫卷的江南古镇。这座“器隐镇”有着惊人的真实肌理——打谷场上的梿枷,在麦收季节里“吃”得满嘴油光;得义茶楼的紫砂壶里,漂浮着龙井的茸毛;当铺柜台的栅栏里,晃动着大掌柜老鹤般清瘦的身影;细竹刀游弋时,竹编考篮上的竹片跳来晃去;合欢桌桌面和桌腿的角牙间,暗藏栩栩如生的花果纹——借助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钩沉等种种考据,每件器物的形制都被精确复原。这种近乎执拗的考据背后,是三年间走访八座博物馆、翻阅百余册方志的积淀。徐风认为,一个作家无论从事何种文本写作,都应该与田野调查建立一种紧密的关系,忠于事实的文字,它不会撒谎,无论岁月更替、人事代谢。从真实的场域和细节中,那些“隐藏于江南广袤民间的风土情怀,古老传器中未被忘却的侠肝义胆”也渐次浮现。
器道相生:农具里的宇宙与针箍上的星河
“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我喜欢倾听他们的一声喟叹,在乎他们留在古物上的一枚指纹。”
徐风并非止步于对器物的形制、工艺(匠艺)考辨,而是着力于器物背后的“用”之哲学与精神投射。《江南器物志》通过捕捉器物与人的微妙互动,和对器物生命历程的追踪,将江南地域的“温润与激烈”、文心与世相娓娓道来。农民郑龙大抚摸耕犁上的磨痕,像在数念珠般清点着六十个农事轮回;新嫁娘触碰梳妆台上的宝蓝色铜镜,翡翠的凉意或许变成灼热的羞赧;赶考书生汤效祖的行囊里,鸡翅木油灯与青云剑并列而卧,“灯以照人,剑可鼓气”,如同带着半个家族的魂魄赴试……作为“器隐镇”这一江南文化标本的活性细胞,器物无声地陪伴着人的生老病死,其使用、流转、兴衰无不映照着地方的文明特质与民间生命力。
江南器物的精妙,也源于匠人“格物致知”的执着。江南器物从来不只是实用器具,书中描绘的那些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技艺,融入了对手艺与心性关系的深刻认知。从春秋时期的刀币,到明清的紫砂;从农家的蓑衣斗笠,到文房的笔洗砚台,每一件都承载着超越物质的文化叙事。这些器物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大音希声式地昭示着“器道合一”的东方智慧。徐风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梳理这些符号谱系,又用文学家般的敏感捕捉其中的情感脉动。江南器物有其独特的“用之美”,不在于炫技,而在于物与人、器与神的完美融合。
“器道相生”的哲学,如徐风在《跋篇·器物有灵光》中所言,“手艺人在器物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沉睡的灵性。”作者以文学之力重现了器物的光芒,点亮了器物的文学异彩,更在器物中找到了江南文化的闳约深美、民间生活的活色生香,和更为幽深的生命义理。青年评论家李怡雯写到,“这些器物所反映出的驳杂细节,恰恰是百年来江南地区民生的缩影。徐风以一人的无言映照苍生的变迁,尽显理性、包容的人文关怀。”当现代人沉迷断舍离时,《江南器物志》会带我们重新发现:老祖宗留下的每件器物,都是装着天地人的微缩宇宙。
叙事革新:器物长河里的中国精神
“我追踪器物成就生命个体的向死而生,我仰慕器物背后流淌的母乳般的中华文明。我在意为了一器之物在这尘世深处悲苦坚守的困顿生灵,我在乎小小器物里流溢出的满满慈悲。”
《江南器物志》最动人的篇章,是揭示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从“宁折不屈”的竹器气节,到“阴阳平衡”的医器美学;从“湮而不没”的包浆哲学,到“天落地捡”的扫地之道,器物不仅是生活的工具,更是修身的媒介——徐风在他的“器物志文学”中,展示了物质与精神的互文,以承载对民间精神的重掘与器物精神本质的叩问,为思考中华文明与地域文化的承续与再生,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样本。
散文能不能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江南器物志》打破了传统散文叙事的单一模式,精准把握了“纪实”与“推演”的分寸感:一方面扎根于扎实的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确保叙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丰满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成为叙事引擎,成为器物故事的释谜人和解密者,赋予冷硬的器物以温度与灵魂,让历史与情感得以鲜活演绎。
全球化浪潮中,传统器物面临着“博物馆化”的危机。但徐风没有停留在怀旧式的咏叹,而是通过器物演变的脉络,探讨传统如何参与现代生活建构。这些古老的器物智慧,在当代设计中正焕发新生。江南器物始终流淌着鲜活的生命力,在这种新旧交融的生机之间,“徐风打捞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仍在呼吸的生活仪式。”如果说器物是中国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而使用它的人们,则是让血脉持续搏动的灵魂。
徐风笔下的江南器物,最终指向了现代人需要共同关心的命题: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更需要懂得“敬物惜福”的生活艺术。所谓文明,不过是人与物之间那份相知相惜的温柔。雨打芭蕉,声如磬鸣;风吹麦浪,形似篆纹。真正的江南不在游客摩肩接踵的园林,而在这些“沉默的见证者”包浆温润的褶皱里。《江南器物志》不是简单的器物图鉴,而是一部引导读者重新发现“物中之灵”的启示录,从器物中听见江南先民跨越千年的低语,教会我们像古人般与器物相处——不是供奉,不是把玩,而是让青铜鼎与粗瓷碗同样映照出生命的庄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