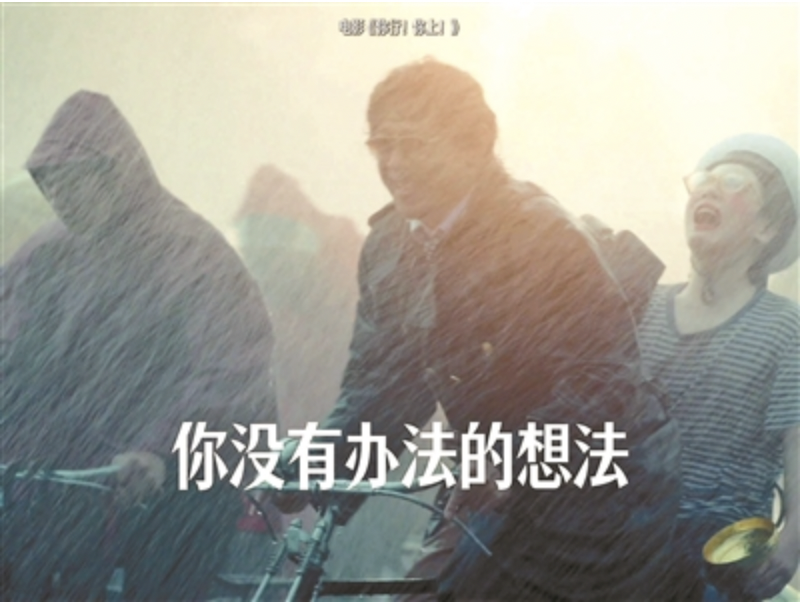姜文拍郎朗,是一个很奇异的搭配。
姜文是中国电影史中少见的不拘一格的电影作者,其电影狂放、恣意、谐谑。作为不世出的钢琴家,郎朗的演奏风格华彩、炫技,充满激情与力量。两个人都有强烈的抒情冲动和外溢的生命力。姜文遇到郎朗,显然不会只创作一部循规蹈矩的传记片。《你行!你上!》更像是姜文再施隐喻大法,将个人传奇化作历史的狂想曲。总的来看,风格依旧,但很难评价。
非常姜文范儿
《你行!你上!》原名《英雄出少年》。改动之后,更加口语化,也更加情绪化了。醒目的两个感叹号似乎在有意提醒大家,这并非一部讲故事的电影,而是一部渲染情绪的宣言式电影。
影片以郎国任、郎朗父子关系为主线,讲述郎朗从出生到成年前辗转学琴、少年成名的经历,时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至20世纪末。时空跨度虽大,但戏剧冲突浓度并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郎朗的成长之路实在过于顺遂。整部影片几乎是“练琴-比赛-获奖”这一桥段的重复演绎。
从影像风格来看,《你行!你上!》依旧非常姜文范儿。那些极致的浪漫主义与狂欢化的后现代主义手法,那种游戏与谐谑的姿态,还有满屏外溢的荷尔蒙,都是姜文电影的标志性风格。片中有这样一幕:郎国任和郎朗接到白宫的演出邀请,二人盛装出行,在寻找白宫专车的过程中手持乐器形如持枪,不料转眼又被戴着面具的同学们戏弄。这是姜文电影的独特魅力——用不断的戏仿与戏谑展开不断的解构,又与历史和现实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
再如,影片延续了姜文对于屋顶、天台等这类空间的迷恋。整部影片的第一幕是郎朗父子的天台争吵:不愿弹琴的郎朗执意跳楼,郎国任救子心切却不小心将儿子踹飞。此时,湛蓝色天空倒映在积水的楼顶,让这对剑拔弩张的父子像是在空中跳起优雅的舞蹈,远处背景则是蓬勃发展的都市里林立的吊塔。这一幕在片中反复出现了三次,意味不可谓不明显。
在姜文电影里,屋顶、天台是浪漫化的想象世界,是远离地面、对抗庸常的飞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屋顶是马小军游荡的自由王国;《太阳照常升起》中,疯妈在火车车顶大声呼喊;《邪不压正》中,李天然甚至在北平的屋顶跑酷。姜文是如此热衷于借助离地高飞的姿态,抒发浪漫而蓬勃的少年心气。《你行!你上!》的天台修辞法,以及反复出现的飞机刺破云端的飞翔,让人体会到一种野蛮生长、不断向上的燃烧的激情。
生猛但也用力过猛
然而,抛开迷人的姜式语法,影片的叙事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传记片理应深入传主隐秘的内心世界,去剖解和呈现独特的心灵。但显然,《你行!你上!》聚焦的是外部的父子关系,主角也并非郎朗,而是父亲郎国任。与永远不拘俗常、永远精神抖擞、永远斗志昂扬的父亲相比,“郎朗”这一角色几乎没有性格可言,登场必胜,缺乏内心挣扎,像是缺乏个人意志的提线木偶。
片中,幼年郎朗的演绎还颇为灵动,青年郎朗的表演就显得有些呆滞僵硬。“英雄出少年”的豪迈故事,本质上成了“鸡娃”父亲辅佐其子升级打怪的男频爽文。对于观众而言,郎朗式一路开挂的天才战绩既不可复制,也很难共情。
为了弥补戏剧浓度,影片用高密度的台词、快节奏的剪辑、浮夸式的表演,来营造一种感官层面的爽感。同时插入一些天马行空的超现实片段,制造如梦如幻、似真似假的气质。片中人物像是都打了鸡血,言行举止被刻意地夸张和放大。尤其是姜文操着一口蹩脚的沈阳话全程狂暴输出,给人一种生猛但也用力过猛的感觉。这让全片从头到尾都充斥着一种亢奋、癫狂、聒噪的氛围。创作者沉溺于自嗨,观众却看得很累。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形容香港电影的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用在《你行!你上!》这里,倒也是恰如其分。
由于《你行!你上!》将一意孤行的父亲郎国任作为主角,加上姜文浓烈呛人的霸道演绎,使得许多观众评价这部影片“爹味”浓郁,过于自以为是。这种评价,其实有些片面。
姜文电影常常以荒诞、戏谑的面目示人,因为他始终有一种解构权威的情怀。《你行!你上!》虽讲述父亲对于儿子的控制与规训,但又将其塑造成非典型的东亚父亲:吃软饭、诙谐开朗、不拘俗常,精神状态异于常人。郎朗成长的过程,是父子关系演变的过程,郎朗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而郎国任坐上救护直升机的结尾意味着父亲终将面对自己父权的失落。郎国任的魅力在于他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核,敢于用迷之自信向权威发起挑战。这是姜文电影的“爹味辩证法”:用解构权威的方式树立自我的权威。
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郎朗父子二人辗转沈阳、北京、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转益多师,快速地在21世纪之交跃上世界舞台中央,恰似我们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之缩影。从这个角度而言,影片的节奏是一种现代性时间观的体现:必须以奋发、进步、时不我待的效率,去追赶不断加速的时代与世界。克鲁兹学院的斗琴段落里,父子联手登台、二胡与钢琴合奏的一幕,像是现代中国之崛起的历史提喻。
除此之外,《你行!你上!》还有没有其他更深远的意涵?或许有,又或许本文的上述理解也是一种误读。姜文的作品历来是观众们的解读狂欢乐园,《你行!你上!》也不例外。在影片上映后两极分化的评价中,一边是“姜郎才尽”的感喟与批判,一边是拥趸们孜孜不倦地破解影片的深层隐喻以证明其宝刀未老,或证明自己足以看得懂姜文电影。观众乐此不疲地做起阅读理解,努力索解欧亚、王子曰、诸葛伯乐等诸多人物的象征,甚至将影片视作一整套的隐喻系统。那些漫不经心的元素或故弄玄虚的台词,似乎都蕴含着导演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
姜文向来擅长制造含混奇幻的梦境,每一个观众都有释梦的权利。因为艺术作品向受众敞开,受众赋予作品以多元的意义,误读也是艺术欣赏的常态。艺术理应是朦胧的、多义的、韵味无穷的。但如果观众将自己的过度阐释归结为导演的原意,并以此为导演辩护并巩固其权威,就有些不够客观了。况且,如果沉溺于索隐,影片的故事、人物与情感也就容易沦为符号的附庸。抛开影片本体不谈,非要去按图索骥、捕风捉影,岂不是舍本逐末?
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特格曾写过《反对阐释》一文,认为当代艺术的一大危险是过度阐释,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这提醒着我们,要注重对艺术作品最鲜活、直接的感性体验。无论《你行!你上!》有多么深刻的艺术隐喻,仅从影片的叙事与视听来看,它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就这一点而言,与其迷恋权威,不如相信直觉。
文/李宁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