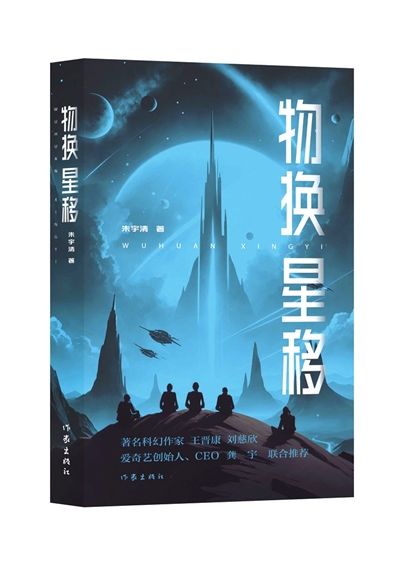科幻小说《物换星移》最近出版面世,作者朱宇清曾获第二届科幻星球奖,著有《天幕征途》等作品,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家、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朱宇清看来,科幻作品远非单纯的未来幻想或冒险故事。它如同一面独特的棱镜,折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科技发展及宇宙位置的深刻思考。它努力拓展认知的边界,让人们得以在思想实验室中模拟极端情境——从技术奇点到星际移民,从人工智能觉醒到文明存续危机。这种“预演”能力,赋予人们审视当下科技伦理、社会结构及环境问题的全新视角,是重要的危机预警和哲学思辨工具。同时,科幻作品也承载着人类最根本的渴望与恐惧:对未知的好奇、对进步的向往、对异化的忧虑、对终极命运的叩问。它激发想象力,启迪科学探索,是关于可能性的文学,更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严肃寓言。正如有人说:“科幻是唯一能严肃讨论人类结局的文学”,它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每一个“如果”的支点上,重塑当下的生存姿态。
《物换星移》是一部科幻长篇,讲述人类突破行星文明桎梏后,却陷入残酷的宇宙生存法则。星际超级政治、文化、暗黑组织等编织巨网,各文明在追寻永恒中与死亡共舞。随着星际文明高维战略浮现,霸主不过是更高维文明的傀儡。在跨维度对决中,谁将成为文明主宰,谁又将面临残酷的物种消亡?作品中的两名主人公坚信,每一个微小人物心中皆有火焰,火焰燃烧的一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虽然星空之下存在着阴谋与霸权,但爱一直是宇宙中最奇妙的存在。他们穿越血与火的星际迷局,用自我牺牲换来和平与物种的延续。作品化用中国文化中充满哲学意象的词句“物换星移”,与科幻设定物种更换、星系位移巧妙融合,发出了跨越时空的深刻拷问。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朱宇清表示,自己在创作时秉持着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想象力的充分释放,力求在保证故事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奇幻而又引人入胜的科幻世界。他还提到,小说中关于“第三物种”的设定以及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隐喻,是为了引发读者对科技伦理的现实思考。他认为科幻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引导公众关注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促进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科幻小说不是科技说明书
北青报:是什么契机触动您,有了创作《物换星移》的想法?
朱宇清:我常想,这世间人、时、事的变化以及世外的斗转星移,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是否有一天,智慧文明也能够让这些自然法则为己所用?那时的世界,个体与文明的命运又会怎样?
《物换星移》出版以后,我和一些作家做过不少交流,总体来说,他们认为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比如,将物换星移的传统诗意与物种更换和星系位移的科幻设定相融合、对物种进化奴役困境的思考、对第三物种的设定、对死亡的重新定义、对个体与文明存亡法则异化的思考、对大统一场论的构建,等等。
我个人认为,科幻小说不是科技说明书,不能让读者感觉冰冷而枯燥;你有了一个好的概念或创意之后,怎样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引发读者的共情与思考,才是最重要的。这很不容易。
北青报:《物换星移》中的“七界疆域”,是由数千万文明构成的生态链,既遵循丛林法则又存在平衡机制。您是如何避免让庞大的宇宙体系沦为“设定堆砌”,而让每个文明都有独特的生存逻辑?
朱宇清:在文明生态链中,每一个文明在其中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整个生态的制衡与竞争中,它既要有存在的合理性,又要面临不确定性的危机。由此,它自有属于它的命运悲欢。
放眼辽阔宇宙,文明在其间,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权力争霸结构。这是一个宏大的生态体系。我想在作品中尽力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星际文明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图景中,有政治机构、民间组织、民众个体以及科学、文化、宗教、暗黑组织等社会元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
北青报:“我是谁”是小说《物换星移》的核心问题,且最终没有明确答案。您为何选择将“身份认同的彻底消解”作为主角的核心困境?是否想通过这种极端的身份模糊性,探讨人类或广义的智慧生命存在的某种本质?
朱宇清:这是智慧文明时代发展的困境。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构成的要素愈加复杂,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未来,这种不确定性恐怕只会是一种加速度的趋势。身处这样的世界,每一个生命个体,要如何掌控自身的命运?即便你是所谓的强者,你是否能够真正穿透时代的迷惘与焦虑?对于更多的普罗大众来说,我是谁?我能成为谁?时代的洪流无法对无数的个体作答。
宇宙只是一种存在,它或许并没有所谓的目的和意义。智慧生命,作为宇宙的产物,又能否追寻到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北青报:“第三物种”作为机器与生物智慧的融合体,其自我认同危机极具张力。这一设定是否受到当代基因编辑、脑机接口技术争议的启发?您在设计时如何平衡“科学可能性”与“伦理警示”?
朱宇清:无论是生命智慧还是机器智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之下,自我的生存发展似乎总以消灭、征服竞争对手为必然之选择。如此,进化可能会成为一条通往奴役与被奴役之路。我想极力跳出生命智慧与机器智慧的二元对立,尝试第三种可能。当然,或许进化的终极螺旋没有终点。在科幻作家笔下,总有太多的可能,也因此,总要不遗余力地予以警示。
科幻的魅力在于想象
北青报:您如何在“科学严谨性”与“艺术创造力”之间找到平衡?
朱宇清:科幻的魅力在于想象。在科幻创作中,想象力或许比知识本身更重要。人工智能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越个人了,也许,留给我们空间和时间的,唯有想象力。站在科学的大地上,你尽可以去描画各种风景,只要你觉得自洽就好。当然有一点,你所想象的,一定要比现实超前一些。
北青报:小说中“虚空计划”对“虚实相生”的运用,呼应《道德经》的智慧,您在创作时,如何避免让哲学概念沦为“符号标签?”您曾说本书想“让东方智慧在宇宙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您看来,东方智慧下的科幻写作,核心特质是什么?
朱宇清:科幻写作漂洋过海而来,但显然,它不是某块土地上的专利。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拥有无尽的宝藏,一定能够赋予科幻更加丰盈的姿态。今天的中国科幻作家与读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一个哲学概念出现在小说中,它不应该只是名词解释;作家的工作,不是去解释这个概念,而是要让哲学概念推动故事发展,让科技插上哲学思辨的翅膀,带给读者更美妙的意象。
如同好莱坞大片,西方科幻写作中,套路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危机。而中国科幻的大地,似乎才刚刚苏醒,还谈不上春天。这块土地上,生长着太多的故事,随着中国科技的高速发展,总该有万紫千红的时候。我们悠久的文化是未来源远流长的根本。
北青报:科幻作品跨越数千万星球文明,容易陷入“宏大而空洞”的陷阱。您是如何通过主人公的命运等微观视角,让读者对“七界疆域”产生实感?在平衡“宇宙史诗”与“个体情感”时,最艰难的取舍是什么?”
朱宇清:小说的主人公即便是具备超能力的异能者,在超级强大的星际权力组织面前,也不得不沦为连死去的权利都无法掌控的棋子。个体与超级组织力量空前失衡的对比,他们在肉体死亡、精神死亡、物种消亡后的迷惘与挣扎,让人真切地感觉到无尽的星空,有若无限的深渊。治大国如烹小鲜。你可以将一个文明当作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生命去看待,或可避免流于大而不当的空泛。
星辰大海的自在远方,亦可能是一个个不确定性的死亡漩涡。既要表现出星际存亡法则异化下的残酷性,又不能熄灭微众心中的火焰与爱的涟漪,这充满挑战。
每个生命都应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北青报:小说中“物质陷阱”暗示科技发展可能带来自我毁灭,而“第三物种”又暗含对新生命形态的期待。这种矛盾是否映射了您对人类未来的真实态度?写作过程中,您是更被“宇宙的残酷”触动,还是被“文明的韧性”打动?
朱宇清:人类的历史,总在希望与毁灭的光影中潜行。对于每一个曾经活过又终将死去的个体生命而言,他们的一生不可重来。确然,我们希望每一个“只有一次”的生命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所以,要更多地警示黑暗与残酷的一面。
北青报:科技既是福祉也是终极武器,其发展充满巨大不确定性。如何防止科技成为“星空主宰”野心的纯粹工具?
朱宇清:科技本无善恶,福祸全在使用者。每一个微众心中多一道火焰,这大地之上、星空之下的黑暗便多消退一分。
北青报:小说中“蜉蝣计划”、“追光打击”等将自然现象武器化的战争形式令人震撼,这些概念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朱宇清:所谓道法自然。文明越发展,离自然越近。高阶文明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强大,战争的手段与外在表现也就越接近于自然。我更倾向于,超级文明的战争或许没有硝烟,或可称之为“自然化战争”。
北青报:小说主人公明知自己是棋子,仍选择“为民众而战”。在个体力量渺茫到近乎绝望的星际背景下,这种坚守的价值是什么?您是否认为“内心的火焰”,比如信念、爱,是抵抗宏大权力与命运洪流的唯一武器?
朱宇清:活下去、延续生命,是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赋予生命以希望与不可言说的力量。爱是生命的自我共情,让生命彼此产生纠缠,这种量子般的纠缠可以跨越时空,成为这个宇宙原本不曾有过的、最神奇的变量。
在更宽广的尺度下自我对话
北青报:您是什么时候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创作科幻小说对您有什么影响?
朱宇清:我从五六岁就喜欢天文,中学开始,又喜欢上了文学。这两者都可以充分激发你的幻想,它们在科幻的星空中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创作科幻小说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简单的、不必依附的快乐”。再有就是一种自我修炼,可以让自己变得心大一点,生活中不会太计较,心态比较平和一些,能够整天乐呵呵的。
北青报:您是否担心作品中硬核的科学理论技术,会因有“门槛”,而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朱宇清:一个好的科幻作者,理应站在读者的角度去写作。比如,你写到原子弹,不必把原子弹的材料、原理、构造、工艺、理论统统写出来。作者的任务不是让读者阅读专业说明书。读者在意的是,你所设定的科技是否具有足够的创意,能带来怎样的身心感受。我主张不要掉进喋喋不休的技术陷阱,尽量把深涩的科技理论知识,通过比喻、类比,具象化的方式,用简洁的语言,让其深入浅出地得以呈现。
北青报:哪些哲学思想、历史事件、科学理论或已有的科幻作品,对您构建《物换星移》这个故事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朱宇清: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沙丘》《银河帝国》《水星播种》《流浪地球》《西游记》《鲁迅选集》《通往奴役之路》《逃避自由》《乌合之众》《战争的艺术》《存在与虚无》等作品,都带给我不同程度的思考。
北青报:关于人类智慧文明的未来,您希望通过作品,最终传递给读者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最大的警示又是什么?
朱宇清:我似乎还没有资格给出任何答案,只是试图抛砖引玉地荡起一丝涟漪,期待在一些读者心中触发一点共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但并不必然要为现实所累积的尘埃所包围;我们可以不时仰望星空,在更宽广的尺度上去与自我对话。
科幻写作最难的是好创意
北青报:您认为科幻是“未来预言”还是“现实隐喻”?您更倾向于哪种创作目的?
朱宇清:在我的作品中,这两者都有。不过严格来讲,不能算是对未来的预言。未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我从不敢自诩去预言什么,只是探讨某种可能性,去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一些相互关系。
北青报:您认为科幻写作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比如科学逻辑自洽、避免套路化、保持想象力和新鲜感。
朱宇清:最难的是有一个好的创意。一个好的创意,能够巧妙地将科学理论、社会现象与哲学思想融合贯通,并构建一个好看的故事。
北青报:您认为当代科幻正在发生哪些变革?如气候科幻兴起、多元文化叙事、软硬科幻融合等,下一部小说您计划探索什么新方向?
朱宇清:科幻作者的队伍正在发展壮大,包括更多的孩子们也在尝试,这是特别可喜的事。科幻创作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精深。当下,科幻文学还是相对的小众文学。时代是决定性的因素。我相信随着时代与文化自信的发展、中国科技的进步,科幻文学的受众会越来越广。我的下一部小说即将完稿,内容和当前的世界格局相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