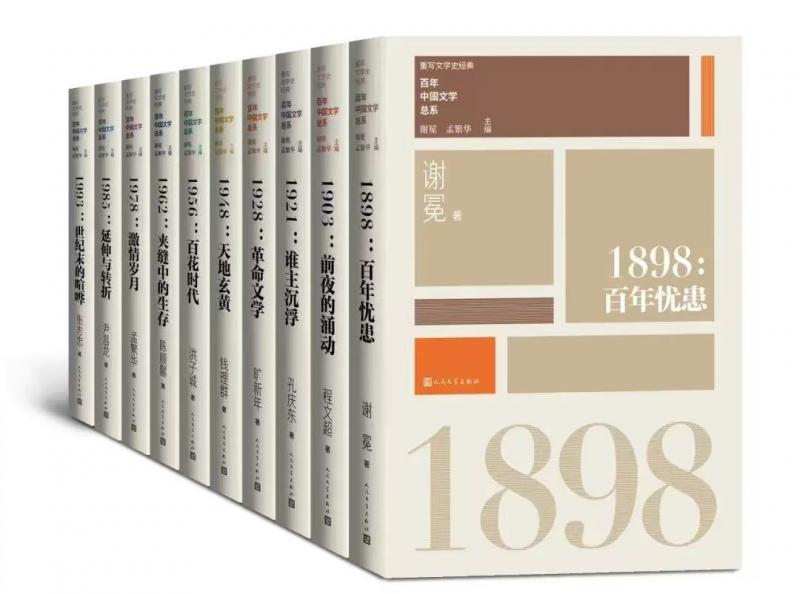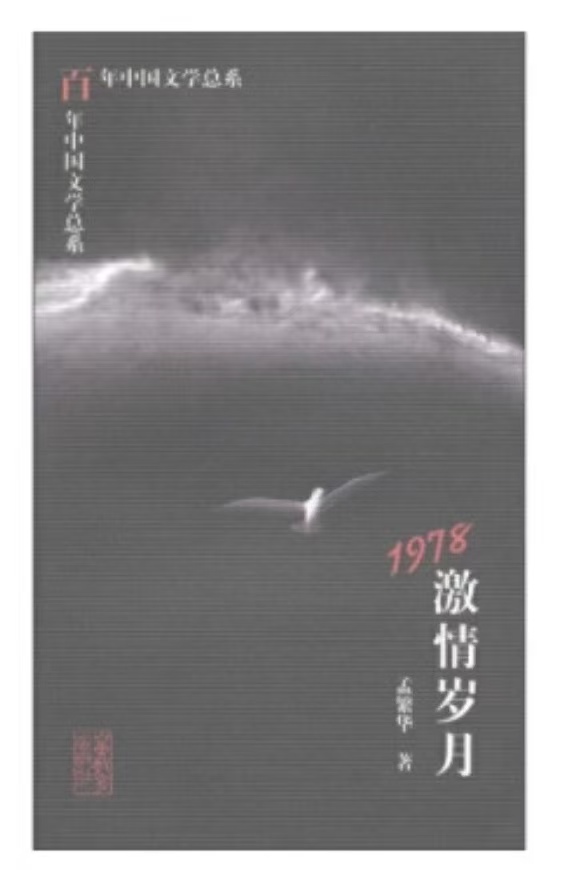一场大雨过后,天空清新而深邃。宽敞明亮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来自文学界、高校等领域的青年作家、学者,以及文学爱好者从京城各个方向赶来,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担任主讲的“艺苑沙龙”活动。“如何平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如何运用文学解决当今面对的新题目?”“如何在碎片化时代坚守文学创作的本心?”在现场,提问的年轻人大都神情激动,语气中难掩兴奋,令人印象深刻。
7月30日,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与担任学术主持的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贺绍俊,进行了一场“创造百年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新范型——《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谈,借这次丛书再版的机会,三位学者现场解读这样一部文学史经典著作,令读者直呼精彩,觉得特别有意义。德高望重的谢冕先生分享了丛书的创作理念和背后思考,强调了文学在反映历史苦难和社会变迁中的责任,并从他几十年的教育经历谈起,对当前文学的书写和未来发展提出了思考。
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共12卷,由谢冕、孟繁华主编,1998年首次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2023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发行,在国内外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参加写作的包括谢冕、钱理群、洪子诚、孟繁华、程文超、旷新年、张志忠等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学者,力图通过12个代表性年份把百年中国文学呈现出来。贺绍俊回忆说,“20多年前,突然看见这样一套文学史著作横空出世,当时大家都很惊奇,讨论得非常热烈,因为这种新的文学史的观念对大家产生了很大冲击。”
该书系的第一本是《1898:百年忧患》,这也给整套书定了主题和基调:百年文学实际上是百年忧患。对于确立这一主题的初衷,谢冕先生表示,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对这个时代负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我5岁的时候卢沟桥枪声响了,不断地换小学、躲避空袭、寻求安全、继续学业。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我们既然有过这样的忧患,就有责任把它书写下来。要是经历了苦难,不把它写出来,有愧于后人。”
为什么选择一百年?谢冕先生说正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太重要了,其中经历了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写作把一百多年来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人的感受呈现出来,为时代立下我们的一种看法。”
关于写作这部书的缘起,谢先生还表示,他在北大从事教育多年,做学问以后应该思考怎么样教育培养下一代学者,他认为比起讲授理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学科的方法,他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放入学生的必读书单,重视的就是黄仁宇研究明史的方法:“《万历15年》这个书对我影响很大,黄仁宇先生讲明代历史的方法对我太有启发了。我很早提供给我的学生书单,就是让他们掌握学习方法: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把它写成历史,而且通过这个历史,看到整个明代历史,甚至看到整个中国封建历史。”
“手风琴式”的写作,书写百年历史
贺绍俊认为,丛书选了12个有代表性的年份把前后勾连起来,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写法,称其为“手风琴式”的写作,伸缩自如,延展有序。那么,12位写作者是如何做到既能在统一主题之下展现个性,同时又挖掘细节后面的历史,勾连起文学文本和时代进程的?亲历过书系组织、主编的过程,孟繁华记忆犹新的是,谢先生鼓励大家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写,每一个作者都发挥自己的长处,自由书写。“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颐和园的石舫写起,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把军费造成开不动的船,帝国要走向灭亡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从冯至的日记写起,通过细节来表达历史。我写《1978年:激情岁月》时,看到一个报道说,当时的上海外滩,一米长的距离里面大概有两三对青年在谈恋爱。通过挤满了谈恋爱的年轻人这个具体的细节,表达一个时代的改变。这就是每一个作者通过自己对历史的观察,去书写百年历史。大家是用大文学的观念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对象来考虑,写的是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轮廓。”
谢冕先生也表示,书系的写作是开放式的、自由的,作者自己选题目、选事件,主编不说话,大家都在兢兢业业地写。“12本书的写作就是作者对某一年代、某一时段想法的鲜活表达,12本书写了100多年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
12个年头、12本书是如何确定的?孟繁华深情回忆了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他讲述说他1989年到北大做谢先生的访问学者,十月份,谢先生的学术沙龙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一个月做两次学术活动,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以及在京的一些重要批评家都来参加,“大家抓把椅子就坐在那开始谈,后来统计过,大概有140多人,成为北大重要的学术风景。”
孟繁华表示,丛书的写作当时还有一个时代背景:1985年前后文学评论杂志连续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以及在上海的陈思和等批评家的文论,希望能够用一个20世纪的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统一起来。后来,谢先生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希望能把20世纪的文学打通。
为此,谢先生有意识地在“批评家周末”组织老师和同学做与百年文学有关的报告,“从1989年到1995年,准备了7年以后,在北大召开了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研讨会。按照《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些著作的启发,谢先生做了整体部署,确定了12个年头、12本书的框架。会上我提出希望这套书能够填补空白、重估主流、纠正通说、发现边缘,得到大家的支持。” 孟繁华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当时那个会没有开多长时间,大家的思想非常一致,然后就各自去行动了。这次写作对我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谢先生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学术领袖,一个是能够提出这种整体的看法;另外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他那种学术的决心,那种坚定性,在今天看来都格外动人。”
让人们记住,是有分量的文学艺术
从文学本身来说,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还要有忧患意识?谢冕先生直言:“我想说做学问的人,他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苦难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苦难又是我们的财富。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出的中国文学,我们的前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寻找文学的药方,用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唤醒民众、救国救民、图强振兴。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文学的艺术形象和文学的想象力太重要了,要是文学没有艺术性,没有想象力,我们出不了好的作品。”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谢冕先生认为,一个好的文学家应该站在时代的潮头,关心周围,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们的苦难和快乐,应该给作品增加一些分量,有一种承担。好的作品最需要的是分量、是境界、是胸怀。他举例说,“我记住蔡其矫的诗《祈求》,记住路翎先生的《盼望》,这样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让我们心动。我记住《原野》,记住《爱是不能忘记的》,我记住阿Q、狂人、蘩漪……文学也好,诗歌也好,让人们记住太要紧了,这就是有分量的艺术。”
此外,孟繁华谈到这套丛书之外带来的启示,他坦言这套书出来之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百多篇评论出来,非常让人鼓舞。“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对百年文学历史的熟悉,我们也不可能发现新时期以来哪些作品值得我们记住,一百年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肯定哪些作品、拒绝哪些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义务来回答时代提出的命题,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主题没有文学,而塑造典型人物是为了推动我们的文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对谈现场,92岁的谢冕先生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记忆力惊人。在与读者互动环节,他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坚持”,他坦言,“这部书第一版封面设计是黯淡的海面,远处有微光,几只海鸥在飞翔。我就是学那个海鸥,在狂风巨浪当中飞翔,总有风浪过去的时候。有人说谢老师经历了那么多他为什么不说,我说我不会说,个人的一点点遭遇我真的没有勇气来宣扬。我写诗,不是为了发表,是寄托自己的内心。包括前年我摔倒了也是一样,做手术换了骨头,我说我不要躺着,我甚至也不用拐棍,我自己锻炼、自己走。后来那次开会,大家都很关心,结果我自己走进会场了,我很高兴地拥抱每一个人。说这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匆匆忙忙,我们力求健康地活着,但健康要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过好每一天。”谢先生的话音未落,现场响起掌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