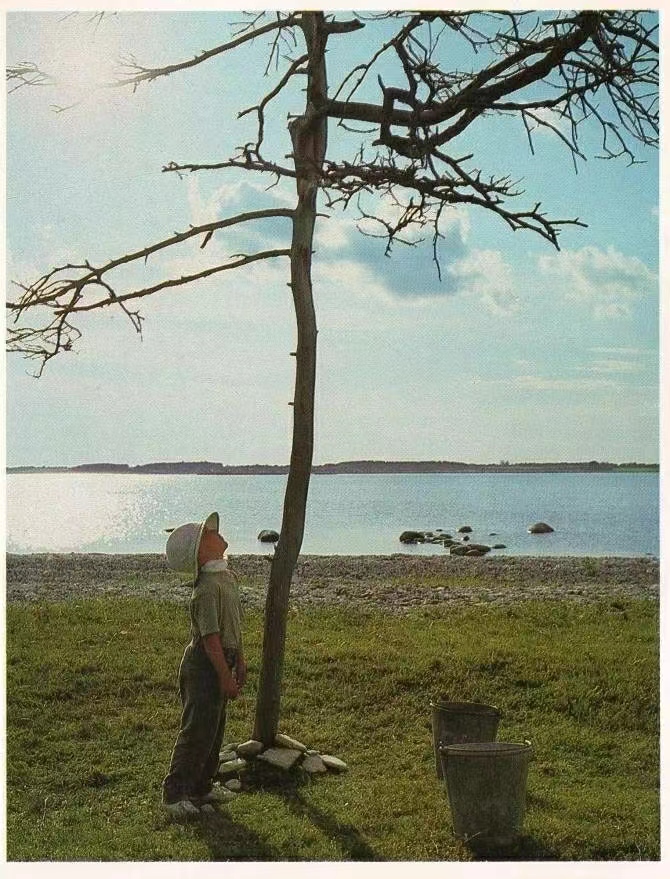
废弃的矿山好像和戏剧演出有着某些天然契合点,假如我们代入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演出遗址的话,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天然的自然风光以及自带故事的荒凉感尤其适合悲剧,险峻崎岖的山体尤其适合演绎那些失败的英雄和逃亡的罪犯故事。欧洲有不少废弃的矿区被改造成演出场所,法国阿维尼翁市西南角的布尔彭采石场,自从1985年英国大导演彼得·布鲁克在此上演《摩诃婆罗多》以来,就是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固定演出场所之一。2016年,法国导演让·贝洛里尼在这里首演了时长五个多小时、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法语版《卡拉马佐夫》。
当近日我们在曹禺剧场回看这个版本的影像时,方能够感受到此剧在这个环境中上演的不可替代的理由,以及它确实是一出成功的戏剧。但是,所有成立的理由都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原著开始讨论。
改编:导演理解老陀是伟大的预言家
显然不是伟大的小说都能被成功改编为戏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确实不乏成功的戏剧化实践。我们不难将之归于老陀小说的一大特点,有人称为戏剧性——因为他的作品中总是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场景,旋风般的“突变”,似乎随意选取局部就可以成一出戏。然而,折子戏再好也无法显示思想的完整,成功的版本首先来自于对作品思想靠谱的、整体的理解。简单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是“思想之书”。在哲学家看来,老陀不是把人物表现为“形象”,而是表现为思想;那些看似激烈的冲突,实质上是各种思想在交锋。这并不是说戏剧中的冲突是思想的对话。戏剧对话看似是角色在说话,但往往被“独白”的框架包裹在内,因为它被作者控制着并与作者同一。
这种交锋首先要在一个“自我-他者”的角度下理解。简略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人格”。这里的人格与宗教维度的“道成肉身”密切关联,与“位格”类似。人格包括了他者,却又各自独立;人格也只有包括了他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面容”。而戏剧改编最大的难度正在于,如何让这些“思想主人公”通过具体的形象呈现。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文本对一个导演最大的考验是:他是否想用哗众取宠来蒙混过关。让·贝洛里尼版本没有令人失望。导演理解这部小说,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预言了20世纪以及之后的人类灾难。实际上,法国文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认识得很晚(但思想界却很早)。不过,在纪德、萨特、加缪等人的诠释之后,老陀在法国逐渐有了很高的国民认知度。想想看,侯麦的《绿光》是一部关于人怎么获得幸福的影片,而女主人公通往幸福的媒介是一本《白痴》——想来很有道理,侯麦应该有他的意图。
同时,能做这样一部戏剧,相应的、有基本理解力的观众是很重要的,他们也是戏剧演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大戏从傍晚开始,天光尚好,在荒山峻岩间,观众和演员一起渐渐走进黑夜,走进这个“大罪人传”(了解老陀的“大罪人”指什么尤其重要),在天地自然间感受一场灵魂的拷问、精神的荡涤——“宗教大法官”动人心魄的滔滔雄辩果然如期而至(整个“大法官”全靠伊万的台词,没有借助任何舞台调度,但可谓淋漓尽致)。能否领略这种惊心动魄,就真的只能看观众自己的了。但不理解也无妨——是的,如果将这部作品敷衍为关于弑父的破案故事,或是一场“剧本杀”,当然是浅表层的理解。但即便如此,也是有意义的。
演员:看起来“不着调”却恰当准确
作为“80后”,又被称为“鬼才”的导演,让·贝洛里尼的戏剧的“花样”一直不少。但是《卡拉马佐夫》的舞美、音乐似乎并没有搞多少“花样”,而是比较简约。舞台空间由几个可移动、自由组合的玻璃“集装箱”隔开,作为情节发展的时空;舞台上铺了一条铁轨,这既像是废弃矿山本来就有的运矿轨道,又来自小说情节本身,同时铁路也是俄罗斯现代性的象征(这点尤为重要)。每个主要演员同时也是叙事人,他/她的叙事交代了情节,同时在叙事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在叙事中与“他者”相遇。导演的这一手法很巧妙,既使原著复杂的情节融于简要的叙事,又使得这种叙事呈现出老陀小说本身具有的“对话性”。此外就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花活”了。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戏的演员都太不着调:大哥德米特里是黑人演员;佐西马长老太年轻,甚至打扮不伦不类,和任何教都扯不上什么关系——当然佐西马长老的故事线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我们无需要求舞台剧面面俱到;格鲁什卡又太老;霍赫拉科娃太太是男演员反串的;扮演小学生科里亚·克拉索特金的显然是个中年大叔。但好也好在这里:这群看起来和原著八竿子打不着的演员却恰当地演出了小说中的那个“思想主人公”——这也是此剧最大的成功(本来,外部的逼真也不是这种改编应当追求的,不过这属于另外的话题)。简而言之,他们准确演绎了“思想主人公”的思想。
善意:怀着最大的悲悯望向“男孩子们”
可是,说了半天,这个故事又传达了怎样的思想呢?
我们不可能像短视频那样,五分钟就带您读完一本文学名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不那么被人重视的一条“复调”线索,即男孩子们的故事,去一窥小说堂奥。导演为我们完整演绎了这条故事线。
小说中,主人公阿廖沙对小学生(男孩子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了便于理解,笔者进行了缩写):
童年的美好回忆是最珍贵的……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为别人的苦难所流的眼泪,恶毒地取笑那些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人。但只要我们一想到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善意、怎样的友爱,就算最恶毒的人,也不敢在内心里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善念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经常会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刚一嘲笑,心里立刻就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温柔、最悲悯的一部小说。他怀着最大的悲悯望向“男孩子们”,他预感到他们将经历动荡、苦难的世纪;他痛心于他们被历史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迷惑,“大法官”就是为了帮他们识别出历史理性的虚妄;但同时他又怀着深切的同情,理解他们对不公正的痛恨、为崇高的理想所激荡,因为在这种激情中也包裹了善。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总会因为理直气壮、由理性算计推导出的理由将之践踏。但是,阿廖沙这里又说,他刚一嘲笑,心里立刻就会认识到“这是很坏的”。
此处千万不能理解为一道鸡汤,比如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听到人们说,坏人是没有良知的,因此他们过得更好,所以我们得“狼性”,云云。阿廖沙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是,人能够自由地走向善,因为人同时被赋予了道德自主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也包括了作恶的意志;虚假的自由意味着让渡出自己的道德自主,只会承认恶的法则;而真正的自由是将道德自主看作人的人格基础,人选择善正是发自人的道德自由的天赋,这种天赋不建立在任何理性的基础之上。阿廖沙知道可以对小孩子们这样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成人更“非理性”。
线索:孩子们是成人故事的“童声声部”
当小男孩伊柳沙像一只小兽一般咬阿廖沙的手指头,甚至咬到了骨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出他高度的理解与悲悯:这个孩子只想惹怒对方,因为对方姓卡拉马佐夫。而卡拉马佐夫家的大哥德米特里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辱了孩子的酒鬼父亲,不顾孩子一再苦苦的哀求,让他本来就因贫穷而遭遇的孤立和霸凌、因为被唯一的朋友科里亚抛弃的痛苦、因为被诱导而给看门狗茹奇卡吃藏了大头针的面包而造成的罪恶感(科里亚正因为如此而宣布和他断交)雪上加霜。
压在这个瘦小孩子身上巨大的不公正,使他只想证明自己可以凶狠地回应这个世界。但是阿廖沙以宽恕回应——并在伊柳沙重病之际,引导他那些平日的死对头们一一来看望他——老陀之所以如此写,是因为孩子们的故事是成人故事的“童声声部”,孩子们的天性使他们迅速就抛下仇恨(阿廖沙生动地用“游戏”来说明这一点),释放出他们对这个不幸男孩的全部的爱,就像一群小天使一样。
甚至包括科里亚·克拉索特金。这是一个少年版的伊万·卡拉马佐夫——他引诱车夫碾断大鹅的脖子,这与伊万引导斯乜尔加科夫杀死老卡拉马佐夫的模式如出一辙。科里亚深受各种社会激进思想潮流的影响,技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已经深入他的头脑,带有“社达”的印记。他声称自己“天生跟那种牛犊般的温柔劲势不两立”,否认、贬低历史、文学等人文科学,只尊重数学和自然科学。多么熟悉的论调!但最终他还是主动找到阿廖沙,带给病重的伊柳沙以惊喜。那一刻似乎一切都被宽恕了,在这种气氛中的孩子们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友爱。
老陀生动地写了科里亚的自负,也写了他的自省和“罪感”,更描绘出他在一个启发性的、友爱的氛围里迅速恢复了一个孩子的本真的善。借这个“童声声部”,老陀温柔地再次传达了他有关神人类的观点,即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神人(基督)和人神(敌基督)两种因素,但“人神”其实是包裹在“神人”之中的一个虚假的、诱惑性的、扭曲的形象。只有克服这种虚假、诱惑,走向完善,才能成为“神人类”。否则,“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暴君(丽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向完善,哪怕是最凶狠的人。因为完善也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但是,首先需要的是对理性的飞跃——这就是伊万欧几里得式的头脑所无法接受的。
嬗变:两对情人一对升华一对沉沦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走向完善,我们才看到老陀为我们揭示的每个主人公精神的嬗变。导演让·贝洛里尼显然理解了这一点,即老陀人物的精神肖像都是动态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扮演小学生的时候并不会有多少违和感——因为这个演员准确演出了科里亚的那种矜持感:他不允许自己展现温柔、脆弱的一面,但是在真诚的善意面前,他这种矜持的、故意好勇斗狠的防线被击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动人的情感。并且,他没有刻意去模仿孩子的形体,夹着嗓子说话等等,反而更令人接受。
每个人都能走向完善,意味着十恶不赦如老卡拉马佐夫这样的人也在内。实际上在老陀笔下,那些看起来凶恶、“咋呼”的家伙反倒有可能隐藏着羞怯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对善的向往——这种向往有时候会以粗鲁的、试探的方式表现出来。相反的,那些表面上的乐善好施和崇高有可能隐藏着真正的傲慢。对于浅层阅读者来说,辨识出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以作品中的两对情人为例——
扮演德米特里的黑人演员不仅有着小说主人公又大又黑的眼睛、炙热的眼神,还让观众看到了他粗野行为之外的“底线”,即罪感。他在凌辱了伊柳沙的爸爸后惊觉,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野兽,也是罪感让他在“弑父”的边缘止步。这是他走向“神人”的重要一步。格鲁什卡行为中的放荡有着对被波兰军官抛弃的不甘和复仇心理,但当她一旦意识到自己仍然具有真正的爱的能力时,她就会转向升华。她和德米特里都经历了一个对肉欲的超越:他们怀着对彼此的爱相拥而眠。
而伊万·卡拉马佐夫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无法超越自我。伊万知识分子的傲慢和秘而不宣的利己主义使他拒绝超越理性;而卡捷琳娜实际上除了自己谁也不爱,德米特里的背叛令她狂喜,因为她需要这种渣男的辜负,来衬托自己忠贞的美德,以及作为牺牲者的一个崇高的道德高地。这个形象是入木三分的,我们看到演员完全理解这一点。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伊万的“大法官”是用无辜者受难的眼泪来折磨自己。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拒绝一种无条件的、超越理性的飞跃。这一对怨偶走在“人神”的道路上,并将受到更加痛苦的折磨。
“童声声部”作为成人世界的复调音乐,更清晰地传递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意图。最后伊柳沙葬礼的描写是催人泪下的,更是给人信心的。作为预言家,老陀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科里亚和阿廖沙之后苦难的命运。戏剧本身并未走入老陀的信仰维度,但是,它无疑在“欧洲现场”依然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毕竟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能够告诫自己守住底线、免于邪恶,能够使人相信道德准则一直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了。我们也可以记住阿廖沙的这句话:“我们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诚实,然后永不相忘。”
文|张晓东
供图|新现场
摄影|Christophe Raynaud
编辑/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