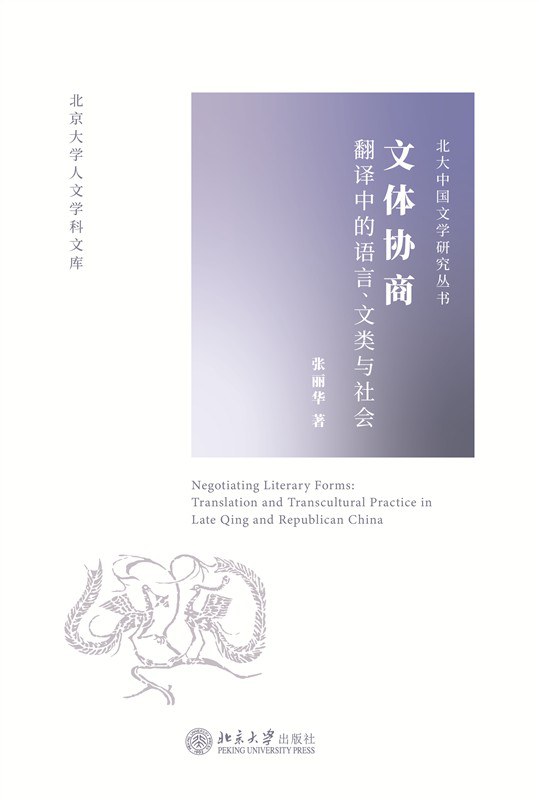收到张丽华的新书,想起我认识她已经20年了——这话写来,自己也吓了一跳。2003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读博,师从陈平原教授。张丽华是2001级硕士生,比我早一年入师门,较真论起来我该叫她“师姐”,可她总客客气气叫我“师兄”。当时感觉她是规规矩矩的典型好学生:上课一直坐第一排,永远在认真做笔记;行文乃至言行都有老师们的风范;平时师门组织活动,常由她安排指挥,往往周全妥当,万无一失。自然,我们的老师们也对她十分信任。后来她去海德堡访学,又到新加坡做博士后,那时我也毕业参加工作。此后听闻她留北大任教,我第一时间写邮件去祝贺她。
此后逐渐在学术舞台上时常关注到张丽华的表现。我觉得陈老师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女弟子里,与我大概同时期读书的几位,尤以袁一丹、彭春凌和张丽华最为英杰挺生,学术成就突出,令人钦佩不已。彭春凌完全投入到近代史领域,这几年深耕章太炎思想研究,将之与近代东亚的中西学术比较进行了深度结合,每有新论均凌厉刚猛,显得内力深厚。袁一丹则兼顾文史两个面向,既有史料发掘和辨析,又处处保留着对于情感与言说方式的文学关怀,且擅于独创命题,不断探索着学术史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可谓招数千变万化,猜不透她接下来会搬用的武器是“狼牙棒”还是“绣花针”。而张丽华仍是中文系学者规规矩矩的治学路数:她上本书是基于博士论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这本新书则是谈文学翻译与现代文学文体形成之间的关系。她本色当行,招式都是稳稳当当的童子功,足够精确而且犀利——如宋代禅师宗杲说的名言,“我有寸铁,便可杀人”。
书中各处不都体现着这种眼光的犀利和分析的深刻吗?比如在第一章“导论”里要对“文体”进行界定时,首先引用的是钱锺书《管锥编》论支谦《法句经序》的一段话。作者评断:“钱锺书将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虚晃一枪的‘信’,视为翻译最重要的准则”(第13页),继而指出钱氏所强调的“如风格以出”、“得意忘言”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语言学及俄国形式主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见解相合,并斥“深信翻译可以如实地传递原作的风格样式,这背后仍有一种拂之不去的‘原著中心’的迷思”(第14页)。此说我也深以为是。钱锺书在别处转述过德国古典学宗师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话,谓“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Die wahre Übersetzung ist Metempsychose)。Metempsychose原出于古希腊文,指灵魂的转注,原与毕达哥拉斯学说有关;在十九世纪后期多用于翻译佛教术语的“灵魂转世”。这样一来,有可能证明好的翻译会有胜过原作的价值(《谈艺录》里确实举出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因为精魂也许原本寄存的躯体已经苍老丑陋(翻译之客方语言传统已走向衰落),可以转到一个美人少年的躯体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来(翻译主方语言通过翻译活动而得以新生)。有一个故事,波兰学生向英国学生炫耀:我们有很多种名家翻译的波兰语莎士比亚,而你们只有一种原文的莎士比亚;英国学生反击说:我们这一种就胜过你们好多种了。但谁也不能绝对否认,也许将来会有一个波兰语翻译家,译出来比原文更好的莎士比亚。因此,要求翻译家忠实于原作,本身就等于主动放弃“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此外,钱锺书还引述过一句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同样也可以支援张丽华对于“原著中心”之“迷思”的破除。
冯象曾说,翻译就是母语的“较量”。但张丽华贯穿全书的论述,使用的是“协商”这样的字眼,这某种程度上似乎掩饰或缓和了跨语际实践里的冲突性。“文体协商”之题(封面英译文作“Negotiating Literary Forms”),出自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形式妥协”(formal compromise)概念(第20-22页)。异质文化的冲突乃至“碰撞”(这是陈平原老师第一本论文集的题目),是大时代里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命运之宏观。而细致到中外新旧的文体、文类和语言之间的剥啄叩鸣,则是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人物们往往不能自察自觉的形势之微观。宋代佛道两教人士都爱说“啐啄同时”、“啐啄同机”,说母鸡孵蛋时,最后是和小鸡内外谐应一起啄破蛋壳的。文体的变化、改造乃至“破体”,如以“协商”之义理解,不妨借用这个比喻:与其说是异质文化的“较量”,不如说就是多方声音谐应于时代的节奏,最后商量出来的。
第三章专论周作人的《古诗今译》(第57-85页),分析周作人译古希腊女抒情诗人萨福和希腊化时期的牧歌诗人Theocritus(遵从张丽华书中的体例,不使用中文译名)的作品,认为他在言文合一的立场下,逐渐采用一种“口语”的方式,摆脱任何“旧文学的腔套”,以确立自己的“白话文理想”。在我看来,鲁迅早年译诗用的“骚体雅言”,何尝不优先于后来的白话新诗?又何必指认这其中的文言旧体之“弹性”就不能容纳足够的新变与进步呢?而萨福的抒情诗残篇和Theocritus的作品,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也算是新近出土的时髦文本——游离于近代民族语言文学传统之外的新鲜古物,正如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所激活的古典传统之外的中国古代文化一样。这种情况下,选择试验性的“口语”面对古希腊文本和少量的英文学术诠释资料进行译诗是不成问题的,这几乎等于是我们没有直接与客方语言展开较量与冲突。但是,假如周作人翻译的是已经有无数杰出近代欧洲语言译本的古典文学作品,比如荷马史诗或是古希腊悲剧,协商下来的效果还会一样吗?而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里曾专论洛布古典丛书本《希腊牧歌诗人集》,放言谓“Theocritus, Virgil所写景象,可与宋玉《好色赋》末句参观”;他又以南宋诗人毛珝《海陵之堡城》“相逢尽喜干戈息,白鹭飞来立战船”这样的诗句,来与Theocritus牧歌里类似的句意进行比较。至于读萨福诗歌残篇英译文的札记,可引段落更多,比如魏源《夜坐》里的“微月不生夜,众星相向明”来比较女诗人的“Around the fair moon the bright beauty of the stars is lost them when her silver light illumes the world at its fullest.”——足见中西经典佳作之间也并不隔。而张丽华指出这恰好就是周作人有意追求的“隔”的疏离效果,非常妙,实在更值得再三玩味。
拿到书时,我先读的是作者的后记。开篇第一句话,“我对文体的兴趣,大概源自某种天生的秩序感”,让我感受到她的生动与坦诚。时常觉得,学者的性情脾气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治学路数和立场。这种由从小对于“秩序感”的爱好,使她在书中也是如此体会和理解刘勰或是巴赫金的“文体”,即“指向一种相对稳定的对个体表述(或文章书写)有规范作用的结构与型式”(第16页)。当然,她更重视的是奥尔巴赫《摹仿论》的“文体混用”说,谓“文体正是在迁徙、流放的过程中,经历混合、协商和变幻才日臻完善,或者说变得更具创造性”(第18页)。就是说,虽然认可文体并非变动不居的秩序,但所有的变动是为了营造一种更好或更有效的秩序。假如后记开篇这句话让我这个不太懂秩序也不太守规矩的“坏学生”来讲,我一定会说:
我对文体的兴趣,大概源自从小对所谓“秩序感”的叛逆。
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体的创立,就是用来被尽快地破坏掉的,即如钱锺书《管锥编》里说的“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可我随后又在书中第九章读到,张丽华从陈寅恪的文学史论断里,早体会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谓的“百凡新体,只是向来卑不足道之体忽然列品入流”(第247页,引钱锺书《谈艺录》之译文),这里虽仅就小说一体的文类升降而论,实则可以放诸四海。
一部用心的新著作,其实处处反映着作者的细致考虑。假如不想只是为了完成一篇“书讯”的宣传工作,不太合格写书评的人往往怀有成见,为说些值得说的话找些自以为是的问题,打算像苍蝇一样“不叮无缝的蛋”。为了努力避免这些常犯的浅妄之病,我试图认真阅读张丽华的新书,写出自己的一点感想,虽然肯定并不成功。
作者:张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