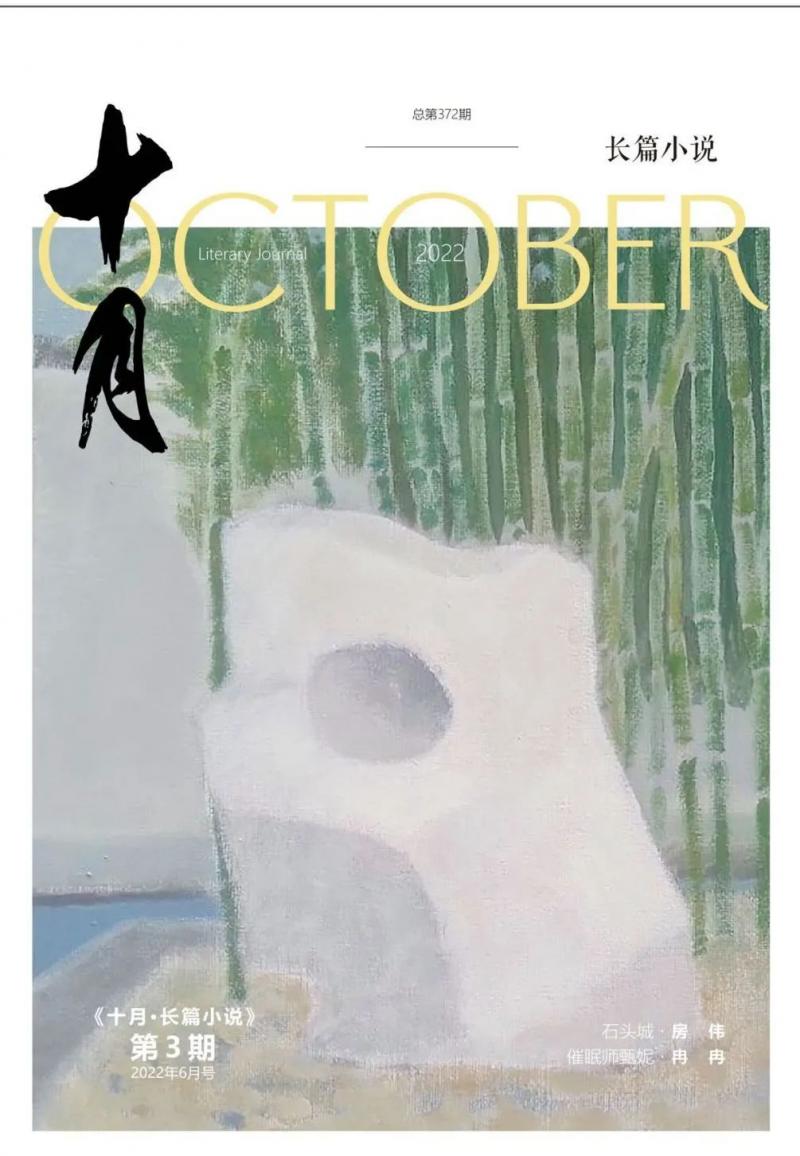1
青年作家房伟一直对抗战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2016年起,陆续发表了《中国野人》《猎舌师》等一系列抗战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后结集为小说集《猎舌师》出版。在短篇这种并不经常处理宏大主题的文体中,房伟依然在尝试重构历史,由此可见其对历史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对于当前抗战历史小说创作的不满构成了写作的另一重动力。他认为,“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而好的历史小说“应该体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精神,不能太过拘泥于意识形态”,“应有一种独特地域主体的特质”,“能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历史性和总体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文学的光芒与魅力”(《重塑历史的现代精神》)。兴趣与不满形成了创作的双重驱动力,促使他写下了系列性的抗战题材作品,以及这部长篇抗战历史题材新作《石头城》。
除了近几年的“抗战历史题材”中短篇系列作品,还有他的另外一个文本有必要回顾。2007年,房伟出版了长篇纪实性作品《屠刀下的花季》。这部作品写的正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部纪实性的作品以丰富的资料展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诸多残酷细节,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展现了战争之于个体的巨大破坏性。由这部作品可以看出,房伟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掌握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历史资料,这也为其以其它形式进入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在有关这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房伟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今后岁月里,也许是几年间,也许是十年,我一定要写一部我自己满意的,关于南京抗战的长篇小说。”十五年后,这粒文学的种子长成了大树,就是《石头城》。作为同题材作品,《石头城》与《屠刀下的花季》重构历史的角度与方式是不同的,后者更侧重于从纪实的角度展现更多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的纹理与场景。《石头城》则是用小说的笔法来重构历史,借助虚构之翼探讨历史事件中包蕴着的丰富议题,比如人民抗战、女性命运、战争创伤、文化对抗,等等。可以说,经过《屠刀下的花季》《猎舌师》等系列作品的实践与积累,房伟在《石头城》这部新长篇中进一步推进了他的抗战历史叙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他抗战系列叙事的一个集大成之作。
2
如何处理重大历史事件向来比较考验作家的叙事功力。历史事件的质的规定性具有不可化约性,它从本质上规定了叙事的边界和虚构的限度,将叙事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边界之内,并预设了诸多不可移动的骨骼性结构。这给叙事带来了难度和考验。而对于抗战历史这样的重大事件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形式多样、角度各异的文学叙事,关于抗战文艺的研究也已涌现诸多成果,如何摆脱“影响的焦虑”,重新发现新的经验和进入的路径,非常考验作家的智慧。
《石头城》以南京抗战为主题,但并不着意于以宏大叙事的方式重构历史,它选取的是微观叙事的方式,以一种低位视角,以底层民众为主体展开有关抗战的历史叙事。军需官、厨师、政府小职员、少年童军、教授、流浪汉这样的底层人物占据了小说舞台的中心,少年成为主要的叙事视点。这种叙事设置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微观叙事、个体叙事、人民叙事。这种叙事将“历史的重力”落在具体的人的身上来观察和表现,将坚硬的历史逻辑分解为更多具体的人的生命逻辑、情感逻辑,将有关人的故事、情感、生命、温度纳入文本。换言之,作品的重点是表现“历史中人”,而非整体性的历史本身。这种叙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使文本卸下了强大的历史规定性的负累,从而更自由地去逼近一种历史真实,一种细微、琐碎、残酷的生活真实。相比于正面的宏大叙事,这种微观叙事具有了更多的叙事空间和自由度,也由此获得了抵达历史深处的可能。
在具体的叙事结构中,《石头城》巧妙地选择了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的融合。《石头城》的叙事焦点在于书写战争语境下各行业底层民众的抗争与抵抗,尽管有抵抗这个共同的主题和精神向度,但人物关系的过度独立容易削弱反抗的整体性,而家族结构的置入,使得主要人物之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对比,也显示了家族这一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在危机时刻的稳固性。小说以蒋氏家族三代人为人物核心展开。面对共同的历史和时代危机,三代人留下了各自不同的抗战故事。
蒋氏家族的中生代是三男一女,坤典、坤安、坤模、坤瑶。四人的身份分别是军需官、厨师、政府官员、在校学生。职业的分散性确保了在更宽阔层面展现历史风暴来临时社会结构的震荡以及反抗的多样性。面对战争或者说死亡,每个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有自发的反抗,也有被动的反抗。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女性,蒋坤瑶拒绝了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命运安排,在民族危机来临时主动投入抗战的洪流。这种观念同时体现在她的爱情选择上,在众多追求者中,她先是有意于警探曾泰,而后又选择了有着郁达夫般忧郁气质的谢东山。这种选择既是情感层面的决定,同时又隐含着对于未来可能的一种预判。同样置身民族危难,作为当局政府体系一员的曾泰的反抗锋芒远不如谢东山来的那样惊天动地,酣畅淋漓。一定意义上,她选择了谢东山,是选择了一个共赴国难的战友,选择了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绽放方式,她的个体爱情与爱国主义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蒋坤瑶这一人物展现了启蒙理性浸润之下一代女性的觉醒与独立,是一个散发着精神光芒的现代女性。
蒋氏三兄弟的抗战是用不同方式完成的。蒋坤典从一名军需官被迫走到了前线,他本不想与死亡如此快速的拥抱,他贪恋着一种安逸的生活。但战争改造了他,从上海保卫战到南京保卫战,他从一个逃避者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抗战者。这种变化,既是战争对于人的改造的体现,也是人的性格弹性的一种显影,作者细腻地写出了这种变化,写出了一种精神的成长。小说的高潮大戏落在了厨师蒋坤安身上,历史的使命落在他的肩头看似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其实也蕴含着必然。尽管他本性上醉心厨艺,逃避战争,但国破家亡的环境决定了这种理想不再有安放的现实土壤,当家仇国恨的情绪逐步累积,他手中的刀就不再只是制造美食的工具,而成为实现复仇的武器。“猎舌行动”是一个厨师的高级复仇表演,也是非军事力量的极致抵抗。相比较而言,蒋坤模的反抗性是最弱的,他在战争中的人生路线高度契合着国民政府的政治路线,一再的后撤及至最后的出国,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政府当局行为的暗喻。撤退与逃离是其人生的主线。
如果说蒋氏四兄妹的抗战从不同职业、性别体现了民众的正面反抗。那么蒋家一老一少的反抗则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小说从蒋巽丰的少年视角展开叙事,并用极大篇幅写了少年童军的抗战。从实际的抗战效果来说,对战争局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蒋巽丰及其童军组织展现了抗战中少年的觉醒与反抗,这种反抗中孕育着民族未来的希望。
蒋氏家族的核心人物蒋乾中教授亦是抗战力量之一种。他的抗战不是向外的、直接的对抗,而是一种向内的、间接的坚守,表现为对于尊严和气节的维护,以及面对暴力和死亡的凛然不惧,他的抗战既是现实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中华文化传统形塑的高尚人格和精神硬度。
家族叙事成为了小说结构的主体,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将历史叙事家族化,同样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群体,比如流浪儿童组成的红山义勇,他们用飞蛾扑火般的战斗延长了抗战时间线,显现出一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再比如老姜头、封阿水、鲁大料、小剪兄妹等等,这些人物的笔墨虽然不如蒋氏家族成员多,但他们的故事亦有相对完整的脉络,这种群体性的人物塑像和故事,有效扩展了人民抗战的现实面积与精神厚度。
可以说,民众的抗战构成了《石头城》的故事主体和核心基调,这也是其有异于以往叙事的特殊之处。在已有的关于此题材的叙事中,往往更多通过展现伤痕的方式来反思战争,战俘的创伤、女性的创伤、孩童的创伤成为重要的叙事图景和反思镜像。伤痕叙事当然是反思历史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方式,但单向度的强调伤痕也极容易遮蔽历史的复杂性、削弱历史的立体性。相比于以往的历史叙事,《石头城》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伤痕叙事置换为了反抗叙事,更注重展现战争风暴降临时的反抗与斗争,而这种反抗的主体并不是以往宏大叙事中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是底层民众。尽管这种反抗无法真正扭转战争的大势,但它赋予抗战历史一种上升的力量,让人们从中看到一种浩大的来自于人民的战斗精神。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小说的艺术》)昆德拉强调的是小说要对未知的事件和人物勘探的责任,一定意义上,《石头城》就是这样一部照亮历史幽暗角落的作品,它把以往宏大叙事中被遮蔽的人和历史打捞出来,把他们曾发出的“历史的低音”作为主体呈现出来,赋予了抗战叙事更多的合唱声部,也赋予它更多闪耀着光芒的精神力量。
3
人民的抗战故事与反抗精神构成了作品的主线和基调,与此同时,作品探讨了许多丰富的文学议题。在谈到历史小说创作时,作者曾说,“我试图在中日民族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我希望既不贬低日本的优秀品质,看到大和民族的自强与内省,勇武与执着,也不忽视‘樱花背后的狰狞’,必须谴责战争的狂妄之心。同样,我们既不能过分鼓吹‘手撕鬼子’之类悲壮豪迈之下的滑稽自卑,也不能轻视中华民族淬炼血与火的勇气与韧性。写战争之历史,必须以强者心态对待血与火,以理性客观的思维看待敌我战争行为,方能超越简单的民族道德对立,反思战争,也反思自我,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建设民族自我的强大自信与独特魅力。”(《历史不在“别处”》)这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文学观。这种观念鲜明地体现在《石头城》这部小说中。作者在呈现战争的残酷、批判战争对人的戕害的基础上,同时以一种历史理性精神审视了所有卷入战争的“历史中人”的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作者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了许多带有“中间性”特征的人物,比如小林秋月、虎太郎辽。作品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摆脱了以往战争叙事中的符号化刻画,赋予了人物更多立体性甚至是矛盾性特征,通过这些人物展现了“历史中人”的复杂性。
小林秋月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她本身就是融合的“产物”。这种特殊的身份在中日尖锐对抗的背景之下具有特殊的反讽性。她在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命运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更是具有象征整体的功能。在战争中,她对于中国抗战的切实支持,她在日军慰安所的悲惨死亡,显示出一种融合进程的被中断与被撕裂。她的出生至死亡的过程,就是不同国族之间由融合而断裂的历史过程的显影。小说显现了战争在对政治关系的破坏之外所产生的文化层面的负面影响。在不同国族之间,除了对抗,亦有融合。而这一切,都在枪林弹雨中化为乌有。
小说的高潮大戏是一场美食盛宴,也正是由此引出一个别具意味的人物出场:虎太郎辽。他是一位日本高级厨师,精通厨艺,在日本美食界享有盛名。也正因此,蒋坤安与虎太郎辽的厨艺对决成为中日文化的一种对抗,是彼时中日两国在军事对抗之外的另一战场。但这一人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既是战争化的又是去战争化的。他的两个儿子参与了侵略战争并战死沙场,他对此并不感到太多悲伤,这是侵略思维和战争文化的显现。与此同时,在厨艺这种文化对比中,他又体现了超越国族对立的对于文化的敬畏和相互借鉴的期待。他并没有因为本国在战场的强势而欺凌中国厨师,而是共同演绎了一场平等的厨艺对决。尤其是最后关头放生蒋坤安的举动,更是对战争思维的一种摒弃,显现出超越性的人格精神。
在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中,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指一种因为丧失了个人思考而参与作恶的行为。这种恶并没有任何邪恶的动机,它是因为失去了独立思考而不自觉参与其中,因此也称为“恶的平庸性”。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也存在大量的诸如艾希曼这样的“平庸之恶”的行为。而虎太郎辽这一人物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对于“平庸之恶”的反抗性,体现出理性和思考能力的部分回归。他参与到战争之中,但并没有完全被战争思维的惯性所支配,而是形成了一种既内在于战争逻辑,又独立于战争逻辑的复杂思维和性格,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历史中人”的复杂性,也是人与战争关系的一种有效扩展。
小林春之这一人物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战争本身的复杂形态。作为侵略战争的一部分,小林春之负责的是文化征服与压制,他的文化同化计划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与霸权主义。他将蒋巽丰与秦小剪作为实验对象,最终都失败了。他的失败看似与战场形势变化有关,实际上也是文化层面碰撞的必然结果。以蒋乾中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培育出的中华儿女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他们可能被打败,但不能从精神上被征服。小林春之这一人物体现出战争本身的复杂形态,侵略战争在表层表现为军事的对抗与征服,但在更深层面上,侵略的最高形态和终极目的是文化与精神的征服。小林春之的失败反衬出中日之间在文化厚度上的巨大差异,尽管彼时之中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文化传统的积淀及其培育出的文化人格,并不像当局的军事力量那般脆弱,而是有着一种内在的稳定结构,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坚固性。
上述人物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房伟对于抗战历史叙事的个性思考和独特观念,他的抗战叙事始终具有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复杂视角,除了表现战争的残酷以及对战争的批判之外,他试图发掘战争中蕴含着的多元而丰富的内容,比如人性的复杂性、文化的对抗与融合、极端环境下个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等等。这种观念使他超越了建立在绝对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抗战叙事,打开了这一题材的更多叙事空间和可能性。
可以说,《石头城》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它构建了关于抗战叙事的一种新的叙事路径和美学观念。这是一种人民性的反抗美学,将惯常的围绕人民展开的伤痕叙事置换为反抗叙事,以此展现了中国人民面对暴力时的反抗精神和战斗精神。它同时也是一种人的美学,将“历史中人”置于叙事的焦点位置,着力写出了人在历史漩涡中的精神痛楚和心灵跋涉,通过有温度和行动力的人赋予了历史更多实感和质感,也由此将历史的肉身塑造的更加丰饶、更加多义,也更有温度。
文/崔庆蕾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