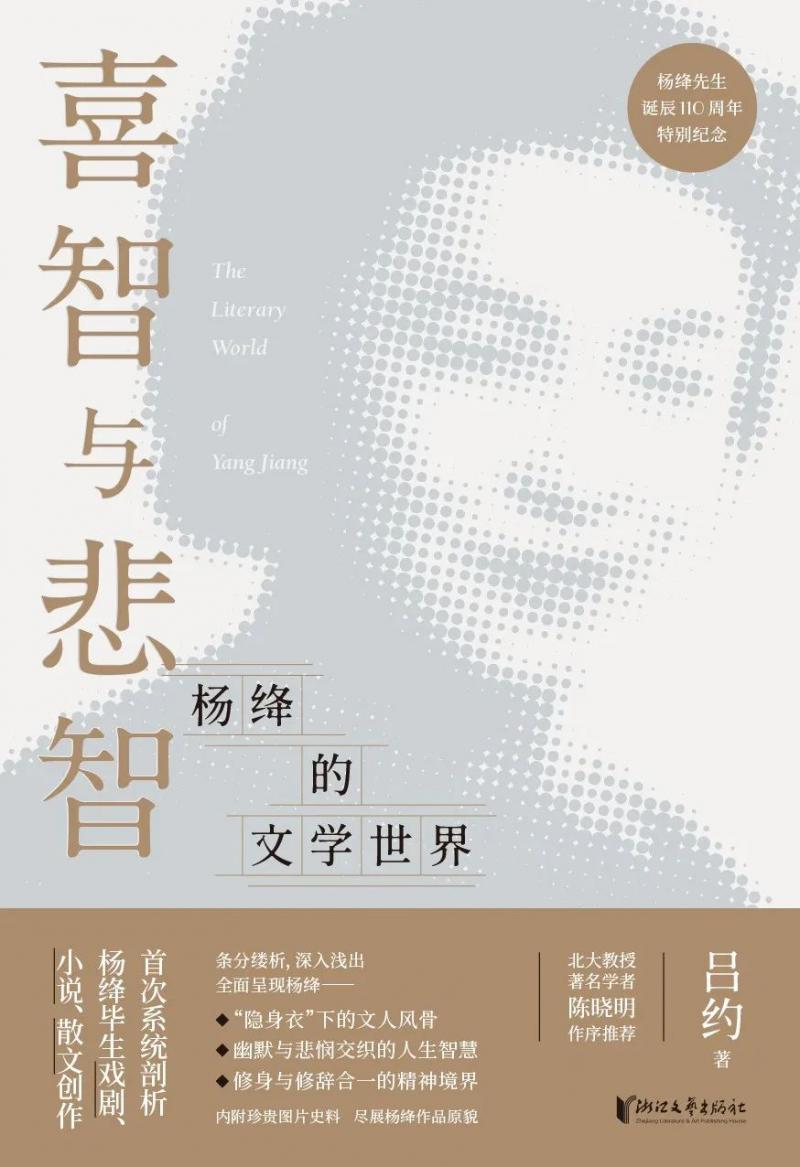不妨借由《喜智与悲智》这部著作,好好感受一番杨绛的文学世界,相当程度也是吕约的文学世界。然后,从中领略独属于杨绛和吕约的那份不可替代性。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又或深入浅出,这都是一件赏心乐事,因为它关于智与美,关于作为唯一的意义。
有的人似乎打一开始便给人年长持重的印象,身骨清癯,发梢莹白,对物质似无所感,对知识满怀敬畏,嘴角永远逗留着一抹认真、精致而从容的浅笑。杨绛正是这样一种形象,哪怕在二十多岁时已凭系列散文和短篇小说在文坛初试啼声。老人形象的杨绛,同时还是一个双声词般的存在。一段时间里,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其与爱人钱钟书势必携手亮相,“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二位先生以同频共振带来的权威感告诉世人,什么是智者乐、仁者寿。
以这般“大众印象”翻阅《喜智与悲智》一书,我的一大观感是,至少某种意义上,吕约是在苦心孤诣地打破我们的此类先见乃至成见,就以文本细读这种耐心、缜密、静定如纯手工艺般的研究方式——一种打破成见最牢靠、最不意气用事、最润物无声的方式。
《喜智与悲智》吕约 / 著;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首先,身为文学创作者、从业者的杨绛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管是否遭受冷落,缪斯就是缪斯,一个熠熠发光的存在,她可以不需要任何他人的依傍、搀扶亦或注目而独自闪耀。具体表现,从体裁到风格,由观世至察幾,由记忆至梦境,尽在吕约的抽丝剥茧中,从而,尽显杨绛的喜智与悲智。其次,杨绛很年轻,或者说年轻过,哪怕少年老成。其中以早年的戏剧创作为突出代表。不论是三部喜剧里的啼笑皆非,还是悲剧《风絮》中的疯魔成活,都痛快彰显出在两性情感、人格心理、家国道义上,杨绛脑筋急转弯般灵动的思维能力和点石成金的形象化能力;而其晚年作品如《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纵然姿态是回望的、总结性的,却毫无沉沉暮气,声调之铿锵,咳唾而成珠玉,与前期的文风和志趣有着高度的延续,甚至更为澎湃与摇曳。
照片里的杨绛总是含笑的,文字里,杨绛实在真心懂得何为笑,她深知笑里的五味杂陈、世态炎凉。某种程度上,由杨绛的作品看出去,那些字里行间中淅淅沥沥的笑意,比鲁迅来得冲淡,比钱钟书显审慎,比张恨水要落地,比林语堂更无为而有所为。笑是一种缓冲、一种体谅、一道影影绰绰的屏,在杨绛“笑的诗学”里,笑何尝不也是苦口的良药——正如夏夫茨伯利所言,“笑能温和地矫正人类的病”。所谓“也”,已然宣告了此笑还是一门智慧,进而是一种人与文的风格。
笑有抚慰的作用,笑也有增强嘲讽的效果,笑让人安心,笑也能让人胆战。在惨淡乃至痛苦的人生处境中,笑需要比悲伤更高的智慧。因此,欢愉之词难工,笑其实更累,喜剧演员到幕后,通常是角落里最不愿说话的那拨人。如果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正态分布的话,杨绛笔下的幽默或许能让她在更为切肤而险峻的现实生活中,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既非逆来顺受更非玉石俱焚的忠实旁观者,此或即自况之“隐身”,然后,牢牢记住、领悟,终而不吐不快。
笑的背后是镇定自若的魂。从小说、散文、戏剧创作到翻译和研究论著,诚如杨绛自述,无外“随遇而作”。正因为这份“业余”和从心,包括自称“无中生有”的小说在内的作品,纵然跨越不同年代及其风尚的召唤、蛊惑,均可谓出乎其性、其情、其智。时局大变、剧变之际的那份“不变”,我以为是因为本身实则在变,体裁的切换,重心的倾侧,隐与现的考量,它是一种微观的调试和休整,而且余地很大,就因这种闪转腾挪涵盖在同一个屋檐下——在现实意义上“我们仨”那有爱的小家,在象征意义上则是勤思善辨、博观约取的“大我”,一个拥有强大定力和自身运行原理的“小宇宙”。因此,杨绛文笔内外的绵延是有机的、活泛的,不添加、无残留,真真性情文章。
性情诉诸文章,文章贯彻性情。杨绛一路走来的文章与思想,并非走向释、道意义上的虚空和无我,杨绛的“隐身衣”并不是要让自我隐遁、匿迹、得道,甩手嘈杂扰攘的软红尘而兀自逍遥游,相反,她倒是不无贪婪地情愿多看看、走走、回想与展望,她对生活真心热爱但对“位置”无感,她对人心向善始终不愿放弃,她是人群里的人、“芸芸众生之一”,从未走远。在梦中亲临“孟大姐茶楼”后,其醒来的头等大事是不忘敦促自己,“及早清理”那些人生路上林林总总的“私货”。这正是杨绛创作的真实写照,于是才有了那么多的“记、纪、忆”。故而,哪怕走到人生边上,也报以极大的热情“自问自答”,她信她的文字和思想远比己身走得更加久远正如信文字和思想的力量本身,它们能够超越今生今世、一人一家,也因此,不切于一时一刻、乍红乍热,最终,自然而然地,她让自己成了难能可贵的唯一。
杨绛的语言同样给人一种“不愿与人群失散”的感觉。从语法到遣词,一概不设迷障,不用假嗓子,不起高调也不佶屈聱牙,无论是小说、随笔散文还是戏剧,都是要让读者舒适而畅然地抵达、贴紧作者的用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仅仅只是手段,作为目的的语言恰在语言进行的过程当中。脱腔而味存,这是高级而绝难的语言功力。在这里,语言是水,开出半塘荷花,养活一池活鱼,肮脏的归肮脏,靓丽的自管靓丽,全都在了这里。偶有风过,起波澜而不惊。你耐心去看吧,这无形无色的水,实在也是一番动静相宜的上好景致,配得上吕约的总结:“其语体融贯古典与现代、雅言与俗语,达到文质和谐、雅俗相生之境,实现了语言的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普遍性与个人风格的统一。”当中若隐若现“五四”的文学语言传统、古典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传统和民间口语乃至宣传语传统,它妙就妙在“融”(共时)与“贯”(历时)上,似乎有迹可循,却又无迹可求。
我从来不相信有完人,同样也不信有无瑕的作品。那么,为何我们会去读,甚至反复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让遗憾的归遗憾,让迷恋成其为迷恋?原因恐怕在于,某种无可替代的东西深藏其间,而它竟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息息相关,这便是文学最为神奇、瑕永不掩瑜的地方。你或许是个资深杨绛迷,或许只泛览过一些她的作品,又或许彼此的缘分尚未到来。无论怎样,我想都不妨借由《喜智与悲智》这部著作,好好感受一番杨绛的文学世界,相当程度也是吕约的文学世界。然后,从中领略独属于杨绛和吕约的那份不可替代性。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又或深入浅出,这都是一件赏心乐事,因为它关于智与美,关于作为唯一的意义。
文/梁豪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