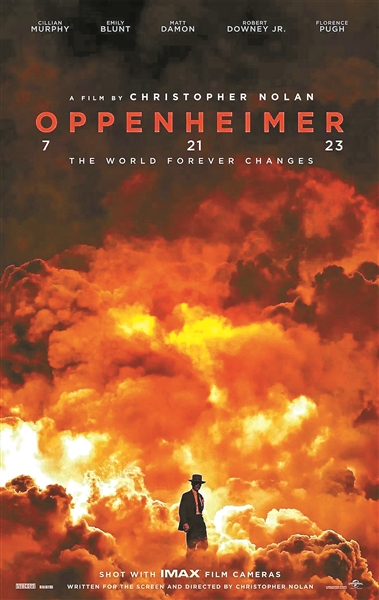看完《奥本海默》,很喜欢,我这一条看《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没哭的汉子,看《奥本海默》眼眶湿了好几回,这仨小时我基本一直坐在椅子沿儿上,两手对着搓搓搓,手心出了很多汗。
除了那些公认的好、牛、炸裂之外,我因为个人经历,在这个电影里面找到了一些私人的震撼和触动。
我大学专业方向是光电工程与光通信,学光学嘛,量子力学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量子力学很迷人,我的成绩也不错,我用业余时间翻了许多参考书和材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能具象地理解量子力学。然而直到最后我也毫无头绪,完全搞不明白,一脑子糨糊。
这个学科里面的概念太妖了,一会儿说猫是死和活的叠加态;一会儿说你观测它它是粒子,不观测它它是波,还挺害羞的。片子里奥本海默往墙上扔皮球和玻璃杯,那不是精神病发作,而是在面对量子力学中一个经典的推论(好像是叫量子隧穿):扔到墙上的皮球有一定概率会穿墙而过,而不是弹回来,当然,概率很低,近乎于零。
奥本海默一遍一遍向墙上扔着皮球,让我想起当年看着漂亮的数学公式推出这些完全颠覆生活直觉的理论给我带来的幻灭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天资不大行的学生在晦涩的学科上受到的折磨,而在奥本海默的深夜房间里,那是人类第一次触碰量子力学时的慌乱和不知所措。
而电影里登场的那些科学家——玻恩、玻尔、海森堡、爱因斯坦等,都是我们上学时的英雄。他们是人类的大脑,是文明的引擎。看到他们我也挺激动,甚至按捺不住想要成为电影院里最讨厌的那种叽里呱啦给身边人介绍背景知识的白痴。
核爆的场景很震撼,倒计时结束,像太阳般耀眼的光亮伴随着无边的寂静,魔鬼的面孔即刻显现。而在它的声音使者以340米/秒的速度慢悠悠地走过十公里给我们送来毁灭的口信之前,末日只给人类留下喃喃自语的最后半分钟。这半分钟该念咕点什么呢?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真好,太好了。买电影票一百,光这个镜头就值回八十。
电影里还有费曼,这个星球上如果有一个“人类有趣灵魂排行榜”,费老师应该在我心中排名前三。核爆的时候坐在车里用挡风玻璃抵挡辐射和涂防晒油的梗应该是来自他观看核爆之后给他妈妈写的信。这封信收录在费曼文集里,他说自己想要一个完整的观影体验,于是决定不戴防辐射眼镜。
这部电影的另一条重头叙事是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政治阴谋与个人利益。你看看,美国也会有施特劳斯这样的坏蛋,他们恶贯满盈、胸有成竹,他们看起来丝毫不惧怕时代,但他们怕《时代》杂志。
电影中科学家和军人对真理的坚定超出对个人利益的权衡也令人动容,观点的争论不混杂对人的道德审判,没有苟且的精致利己,这是科学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
泰勒承担了这部片子中科学家的反派形象,值得意识到的是,我们熟知的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就是泰勒的学生。即便泰勒做出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陈述,他至少没有像政客一样抨击奥本海默的忠诚和正直,也没有给他挖坑设局。他说,他不认可奥本海默的许多做法,他们二人也有诸多矛盾,却并不怀疑他的忠诚,除非看到确凿的证据 —— 真是一堂生动的科学素养教育课。
在施特劳斯听证会作证的那位小哥(希尔)也是一样,虽然奥本海默摔了他好几次笔,他还是选择站在政客权谋之术的对立面。他那张邪差一点点压了正的脸,一如曾经在 Live Aid 上唱起波西米亚狂想曲有魅力又不太好惹的样子。(希尔的扮演者拉米·马拉克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扮演皇后乐队主唱)
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人啊,还是要尽量做好人做好事。虽然人性复杂,我们总有光明和阴暗面,但在那些我们尚有机会摇摆的灰色地带,尽量做好事,做那些未来即便搬上大银幕供历史审判也不会感觉寒碜的事。
奥本海默在失去安全许可后,妻子嗔怪地问他,如同质问一个殉道者,大意是你把自己搞这么痛苦你挺牛的呗?你觉得这么做世界就能明白你吗?奥本海默平静地说:we'll see(注:英文大意“走着看”)——是啊,not now, we’ll see(注:英文大意“现在不清楚,早晚会知道”), 今天没 see(英文:看) 着,明天再 see see,别急。
片中施特劳斯在听证会中失败的消息传来时,助手告诉他带头反对的参议员叫肯尼迪,这个肯尼迪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他签署了向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的决定(费米奖就是以影片中出现的费米命名的,这个费米也是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导师),不过肯尼迪自己却在颁奖之前几天遇刺身亡。最终给奥本海默颁奖的是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姑且算是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活着的时候给他的一点交代。
直到去年年底(2022年12月16日),拜登政府推翻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正式为他平反。
值得一提的还有主角那双眼睛,我努力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听力支撑着自己忽略字幕盯着这双眼睛,太迷人了,他的野心、专断、赤诚、追求、信念、狡黠、痛苦、脆弱、恐惧、矛盾全写在里面。票价一百,这双眼睛又值回八十。
电影最后的情节,说施特劳斯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奥本海默跟爱因斯坦相见时说了他什么坏话,其实人家没谈到他,而是在聊科学伦理。
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彼时我所在的公司正在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办公室政治斗争,有一次我和大辉午饭后在公司楼下闲坐扯淡,远处走过斗争漩涡里的另一主角。事后没过多久我也卷进了这场闹剧,有人告诉我他看到我和大辉在公司楼下密谋,觉得我肯定提供了关键情报。
那天真实发生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淡去:在吃完一肚子碳水昏沉沉的午后,大辉同学非常认真地花了很长时间教我一种系鞋带的方法,以及解释这种系法不会导致鞋带松开的原理。
我至今依然这样系鞋带,捋着鞋带时偶尔会想到“密谋”这个词,然后咧开嘴笑一下。
文/邱岳(公众号“二爷鉴书”主理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