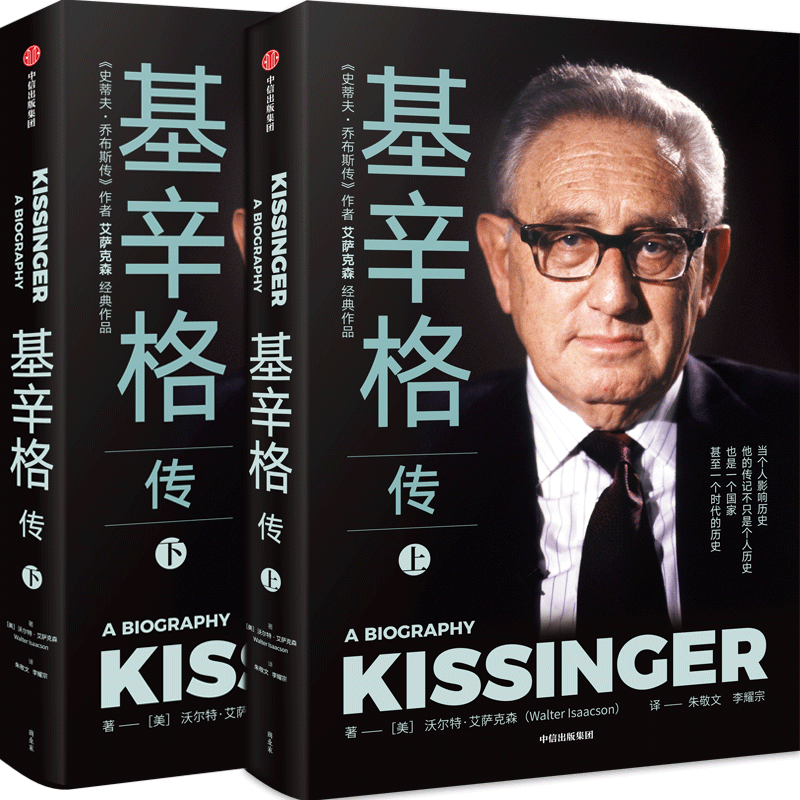1994年夏季,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如其人——读《基辛格传》”的文章,刊登在《美国研究》上。当时写作的动机和背景,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用笔名发表的原因,是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职,担心借写书评之机臧否美国的“大人物”,引起不必要的猜疑。那时评述的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基辛格传》的1992年英文初版。时过近30年,读到依据2005年第二版译出的中文版,又重读自己写的书评,颇有一些感慨。
1986年秋天我因公访问美国,在纽约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听到他的演讲,但内容记不得了。此后,我见过基辛格大概超过30次,地点包括北京、纽约、华盛顿、莫斯科、新加坡等,多数是在会议场合。和他的6次单独谈话和多次个人通信来往,则是2018年以后的事。
基辛格本人给我的印象,和我在这本传记以及其他书本上读到的基辛格,有很多重合之处。我所见到的基辛格,永远身着缝制精细的成套深色西服和黑色皮鞋,系着考究的暗色领带,佩戴黑框眼镜。他说英语带德国口音,音色低沉,语调平稳,微笑中露出狡黠。他的口头交谈同文字著述一样,用词精确,字斟句酌,很难找出破绽。
1992年春天,我陪同一位国内领导到他的纽约办公室(那时他的办公室还没有现在这样宽敞豪华)。他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照片说:“你们看,我把和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放在前面,把日本人的照片放在后面”。我当时就怀疑,如果日本客人要去他的办公室,他多半会调换相片的位置,把和日本领导人的合影放在前排,把中国人的相片放在后面,而且要向日本客人显示。这就是外交技巧吧。
我注意到,基辛格住宅的会客室里,装饰着不少典雅的油画和艺术品,但办公室的桌面和书柜里,更多的是同各国政要的合影,特别是美国历届总统在白宫接待他个人的合影。不过,拜登担任总统之后,似乎没有邀请他去过白宫。在基辛格的新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摆放着特朗普同他在白宫的合影,大概是有意为之。无论如何,基辛格的共和党色彩涂抹不掉,他自己也不隐晦这一点。他在本人的著述中,对尼克松、里根颂扬有加,也谈及他同共和党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等人共事的经历,却很少肯定民主党的政绩和外交政策。基辛格的好友多是共和党人,不少朋友和助手是犹太人。
基辛格的政治手腕,在传记中多有记载。艾萨克森写道:“基辛格的魅力和迷惑力、恭维和口是心非,都是他外交的一部分”。28年前他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5年8月,我陪同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去基辛格在北京下榻的宾馆拜会他。当年中美关系的敏感话题之一,是9月在北京怀柔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关于中国国内人权问题的争论。6月,中国公安机关逮捕了潜入国内进行非法活动的美籍华人吴宏达。西方媒体大肆炒作这件事,扬言如果中方不释放吴宏达,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就不来北京出席世妇会。不过,我陪同领导同志和基辛格的会见,谈到的主要是他们之间过去的交往等话题。谈话快结束时,基辛格似乎不经意地提起了吴宏达事件。他说:“我亲历美中交往二三十年,从来没有听过说有个Harry Wu(吴宏达的英文名)。如果让这种无足轻重的事情搅乱美中关系,太不值得了。中方有理由逮捕他,判他20年监禁。不过,你们关押他20年,美国国会就跟你们闹20年。我看不如把他判刑以后驱逐出境,结束这个事情。”
没过多久,这场危机就按基辛格建议的方式平息了,世妇会得以顺利举办。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明明是从美国立场出发,给人的印象却是替中方“解套”,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他出的这个主意,如果是从美国外交官的口中说出,或者经由美国媒体报道,结果很可能达不到目的。
中国人判断外国知名政治人物是否有影响力,往往是考虑“他跟本国政府关系如何,政府高官是否还去找他咨询”这类问题。其实,像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其作用主要不在于给本国政府出谋划策,而在于能够穿梭于各国政界和商界之间,运用本人的智慧、人脉、经验,为本国的长远利益服务。他的很多政策想法,都很难想象是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或授权的。这种“政治掮客”的独特角色,只有在民间组织有充分的空间、商业市场活跃的社会才会出彩。他虽然是外来移民,但对美国的忠诚却无可质疑。
1977年离开政界之后,基辛格身兼学者、思想家、战略家、企业家的多重身份,著作等身,直到百岁出头,仍然思维敏捷。有一次和他闲聊,说起足球,他说自己少年时代踢球,个人球技虽然不高,但会组织调动球队(此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现在还看德甲联赛,对某一球队情有独钟。谈起自己的长寿秘诀,基辛格首推家族基因,而热爱工作,永远在构思下一本著作,也赋予他的生活以无穷动力。
回看我当年写的书评,虽然因缺乏同基辛格的亲身接触而有些书卷气,但基本观察和判断还是站得住脚的。我想重复那篇书评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应有自己的尺度,而在评价基辛格时不能忘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这句话的不妥之处,是1994年基辛格才71岁时,我已经把他当成“历史人物”了,没有想到他100岁时,不但健在,而且作为传奇式的人物,继续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以下是我1994年写的文章:《政如其人——读
在1973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即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成为美国最受羡慕的人物。有关这位20世纪最有声望、最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的传记、专著,已在美国出版了近20种之多。其中《时代》周刊编辑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就其广度、深度和所引用的第一手材料来说,堪称研究基辛格的权威著作。
为完成这部长达近900页的长篇传记,作者曾采访了150多人,其中有包括基辛格母亲在内的亲友,有包括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在内的政要,有基辛格过去的助手和同事,还有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作者并搜集了有关基辛格的大量私人文件、信件、电话记录、工作日志、保密会议记录,甚至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基辛格本人亲自接受作者正是采访20多次,为作者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其他方便。如此丰富的原始材料,使本书得以全面叙述基辛格如何从纳粹德国迫害下的犹太儿童,成长为美国陆军反谍报机关的军士,又如何从叱咤风云的外交家,变成年收入高达800万美元的公司、企业、银行顾问。
真实性是衡量传记的首要标准。按理说,只要埃萨克森忠实于他苦心搜集的材料,本书的真实性就不应该有多大问题了。然而读罢作者附于书后的材料来源说明,才明白了一个外交史学者早该明白的道理:切勿迷信文件档案。从政之后的基辛格说过:“外交文件的记载向来很少反映现实。假如我过去就了解我今天所了解的情况,我决不会根据档案去写有关梅特涅的论文。”在复印机、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出现之后,伪造文件、炮制谈话备忘录以掩盖真相等手段,更十分普遍地被官方所利用,使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难辨真假。作者引用基辛格本人的话说,将来的学者将“无从掌握标准,去辨别哪些是炮制出来作伪证的,哪些文件是真正指导决策的。”书中披露,只要基辛格能发现秘密渠道,他几乎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渠道里留下真实记录。例如,在有关70年代的美越巴黎谈判期间,基辛格经常要他的助手安东尼·莱克(现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温斯顿·洛德(现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就同一次谈话,撰写三四份不同内容的谈话备忘录,交给不同的阅读对象。有一次,尼克松给基辛格发了一份“密电”,宣称将要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然后在另一份密电中指示基辛格将上封电报的内容故意透露给谈判对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解密”文件或未解密的文件尚且如此之不可靠,作者的采访对象说了多少真话,就更无法测知了。好在被采访者中,基辛格的密友和政敌兼而有之,可以对事实描述加以核对和比较。但无论如何,本书提醒我们,今后学者在判断什么是“历史真面目”时,必须慎之又慎。对于本书中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政治事件的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只能姑且读之。
因此,更应该引起学者兴趣的,是本书对这位具有多重人格特点的政治家毁誉参半而又富于哲理的评价。拿破仑曾说当年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的政策和阴谋诡计没有什么区别。在埃萨克森笔下,作为梅特涅崇拜者的基辛格,既会娴熟运用政策,又懂得使用阴谋诡计;既是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又是工于心计的战术家。他将学者的严谨和政客的狡诈融于一身,连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智谋过人。他的智慧产生于一种理论与灵感的结合,善于在抽象思维的框架里把握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埃萨克森的比喻是:“他像一只蜘蛛,在自己编织的丝网里,能够感觉到——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在世界某一角落里的一个举动,在另一个角落里引起了震撼。”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过去,研究者多把这种思想归因于他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时,对于欧洲外交史的钻研。本书作者则另辟蹊径,强调少年经历给他的政治行为留下的烙印。他是纳粹意识形态狂热的受害者。在他成长的环境下,互相信任和道德准则遭到无情的破坏,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基于性恶论,他懂得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稳定和秩序。在移居美国以前,基辛格在一封信里写道:“弱小是死亡的代名词”,“人们有时只能在谎言下才能生存。”他所崇拜的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相信的是人的直觉和灵感在历史中的作用,鼓吹的是权力意志。
逆境培养出来的基辛格生性自傲、孤独、多疑。在学术方面,他充满自信,不惧怕公开争论,敢于应付理论挑战。但在待人接物时,他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喜欢保密,长于欺骗。思想理论中的自尊,人际关系中的精神紧张,社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意识,反映到他的外交政策中,就是相信权力而非道义原则决定了世界秩序,相信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更高明,更有效。同时,基辛格认为,依据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外交宜于公开推行,而现实主义外交必然建立在拿领土、金钱和权力做交易的基础之上,必须采取秘密行动以至欺瞒手段才能达到互相妥协的目标。如果这种交易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或者拿到美国国会去讨论,当然会遭到挫折和失败。
书中提到,基辛格的权力意识,对美国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感,与尼克松的性格特点和政治需要一拍即合。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缓和中美关系、签订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东和谈等历史进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导演了一系列秘密外交行动,国际舞台上的轰动性新闻此起彼伏。基辛格觉得,只有绕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他1971年的首次北京之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方正式代表史密斯蒙在鼓里,才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在无数这类事例里,基辛格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外交成就,同时也埋下了同僚嫉恨的种子。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使美国政府蒙受耻辱,本人也丧失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基辛格在这一时期不断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外交决策圈里树敌过多,加深了尼克松的政治危机。基辛格骄横跋扈,在政府高层人缘不佳,以至于共和党1981年再次上台之后,他未能谋到任何正式的政府职务。
本书着力刻画了基辛格为了攫取权势,如何在政界中扩大私人关系网,利用他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不惜在同事之间制造嫌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一次,他对退休外交官哈里曼说,如果哈不再攻击尼克松,他会提议在政府中给哈安排一项职务。听到这次谈话的一位助手后来问基辛格,是否真的存在给哈里曼安排职务的可能性。基辛格回答说,他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决定该说什么话的时候,真实性是无所谓的”。
基辛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的是同样一种风格:用施展魅力、利益诱惑、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手法,在各国政治家之间纵横捭阖,为实现他的外交目标而不择手段。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他用奉承话讨好各国领导人,当着一方的面贬损另一方,企图让每一方都以为他在为自己出谋划策。他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技巧和个人性格。
虽然作者对基辛格的为人和政治品质颇有微词,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政策思想,甚至也没有完全否定他的道德观。作者指出,基辛格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日子,正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期。7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失道寡助,美国军力捉襟见肘,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地夺取势力范围。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基辛格的权力均衡政策可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成为出色外交家是时势造英雄。在作者的眼光里,就对国家安全的贡献而论,基辛格的历史地位应同史汀生、马歇尔和艾奇逊相伯仲;他和凯南可以并列为影响最大的外交思想家;他无疑是本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谈判能手。
那么,什么是基辛格最大的建树呢?本书的结论是:他有意识地参与创造了新的全球权力均衡,使美国在越南战争后保持了在全世界的影响,最终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在美国国内,他一方面顶住了鸽派和自由派要求放弃同苏联争霸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顶住了鹰派和新保守势力要求同苏联全面对抗的压力。他主张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与之缓和关系,以静观苏联内部矛盾的激化。7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40年代末的凯南一样,相信莫斯科只有向外扩张并夸大外部威胁,才能维护国内统治,而缓和加遏制的两面政策,将最终促使苏联解体。作者说,回顾这段历史,基辛格是胜利者。基辛格打开通向北京的大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给美国外交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把握全球均势的杠杆,亦功不可没。“当冷战结束时,这一现实主义的遗产帮助美国在一个新的全球环境中,以多权力中心和均势为基础而运作。”这样说来,基辛格的成功又是英雄造时势。
同时,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变化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基辛格的制约。他是特殊历史时期(美国在冷战中被迫采取守势)的特殊历史人物(持欧洲传统保守思想的美国外交家),而且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对权力平衡有着特殊敏感的共和党领袖,才会把他推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然而事过境迁,基辛格奉行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很快就被卡特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推动的“民主革命”浪潮所冲淡。直至今天,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必须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将维护全球政治稳定和推进西方民主取向的变革摆在同等地位上。
书中引用基辛格的亲密助手伊格尔伯格(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的话说:“亨利是一个主张权力均衡的思想家,他深信稳定的重要性,而这一目标是同美国传统格格不入的。美国人总是想追求一套道德规范的实现。亨利对美国政治制度缺乏内在的直觉,他不是按照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点办事的”。也就是说,基辛格将权力均衡作为外交根本目标,忽略世界民主化,不符合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他的秘密外交方式,也很难同当代美国政治的运转方式接轨。
但是,基辛格为维护美国实际利益而牺牲某些抽象的法治和道义原则,运用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在他本人看来并非违背道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世界稳定的最终目标。促进本国利益,保护世界不受战争威胁,是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外交家眼中的最高道德。他因签订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对基辛格玩弄权力政治的不道德行为加以抨击。在为自己辩护时,基辛格谈到他有十几个亲戚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因此体会到只有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他说,外交决策者的责任不同于人权斗士或和平主义者,不能按纯粹的理想来指导本国的国际行为。
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基辛格的处境,但拒绝认同他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埃萨克森认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既是弱点,也是优势,美国赢得冷战胜利靠得主要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作者和许多美国评论家一样,欣赏基辛格的卓尔不群,但又认为他所代表的权力政治观不足为训。这是本书的中国读者可以细心品味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应有自己的尺度,而在评价基辛格时不能忘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