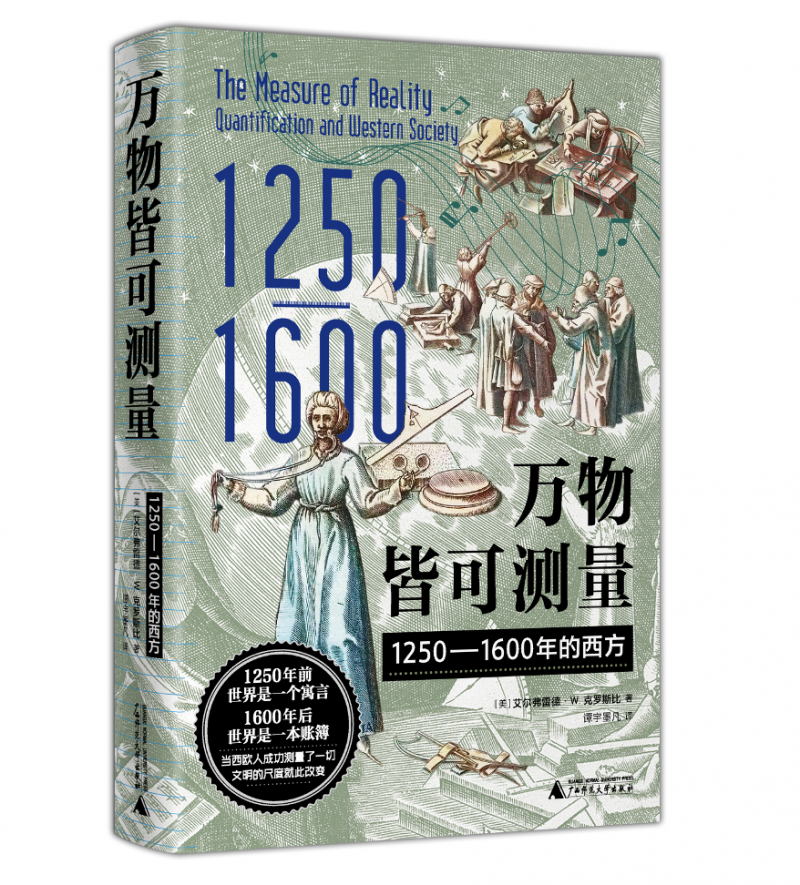公元9世纪中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西欧描述为“宦官、奴隶、锦缎、河狸皮毛、动物胶、紫貂皮和刀剑”的来源,仅此而已。一个世纪后,另一位穆斯林地理学家,伟大的马苏迪写道,欧洲人头脑迟钝、口齿笨拙,而且“越往北,人就越愚蠢、粗鲁和野蛮”。在任何一个久经世故的穆斯林眼中,基督徒正是这般模样,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被称为“法兰克人”的西欧人,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野蛮人,他们虽居住在欧亚大陆,却远离其高雅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偏远的大西洋沿岸。
六个世纪后,这些法兰克人就在数学领域和机械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至少与穆斯林和世界其他所有人不相上下,甚至还可能处于领先地位。他们正处于科学连同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既是他们文明的荣耀,也将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利器。可是我们要问,从9世纪到16世纪,这群乡巴佬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他们那种用法语来讲所谓的“心态”,到底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仔细研究一下16世纪的心态。这种心态只是结果,而了解了它,我们才能更好地知道要从原因角度探究什么。
……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选择是以视觉方式一次性尽可能多地感知现实,这是当时和之后几个世纪西方最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选择甚至延伸到了最不需要视觉和最转瞬即逝的东西上,那就是音乐。你可以在一页纸上立刻看到几分钟的音乐。当然,你听不到它,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并立即通过时间了解它的整个主题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要限制变异,是要减少即兴发挥。这种选择也体现在战争中,即为那些在战争恐怖阴云笼罩下的男人精心设计了行动准则。似乎就是从16世纪开始,西欧的将军会和兵头们一起在沙盘上推演战术。
我们应该将这种把事物、能量、行动和认知分解成均等部分并加以计数的热情称为什么呢?还原论?错倒是没错,但这个过于宽泛的范畴,并不能帮助我们将这种热情与其他事物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尼科洛·塔尔塔利亚在1530年代回答的一个问题,即大炮应该向上倾斜多少才能把炮弹射得最远。他从一门重炮中射出两个重量和装药量相等的炮弹,射角分别为30°和45°。第一个的射程是1,1232维罗纳尺,第二个的射程为1,1832维罗纳尺。这就是量化。这就是我们设法处理物质现实的方式,把芜杂的细节放到一边,直抓要害。
用W. H.奥登的话来说,我们生活的社会“对可衡量和可测量事物的研究有着狂热爱好”,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什么替代方式能帮助我们处理现实世界。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需要看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例子。我们选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因为它们颂扬了一种非计量的或几乎可以说是反计量的方法,还因为它们绝佳地体现了我们原始的思维方式。这二人比我们更重视人类的理性(reason),但他们不相信我们的五感可以准确地衡量自然。因此,柏拉图写道,如果灵魂依赖感官获取信息,“它就会被肉体拉进变化无常的领域,并迷失方向,开始感到困惑和混乱”。
这两个希腊人将材料(data)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可以十分确定的,另一类是我们永远不会确定的,此种分类标准与我们的不同。你我都会同意,日常经验的原始材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我们的感官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相信,有这样一类事物,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存在的,却不被这两位哲学家承认:这类事物足够均质,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对其进行测量,然后计算出平均值和中位数。至于说到进行此类测量时感官的可靠性,那我们就会明确指出在此可靠性基础上取得的诸多成就:动力织机、航天器、保险精算表,等等。这当然不是一个可靠的答案,因为我们的诸多成功可能是偶然的,可它却也是一个例证,说明了人类通常用来评估自己能力的方式:也就是问,什么可行,而什么不可行。为什么的确很聪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会回避这类有益的可计量物?
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古人对量化测量的定义比我们的狭窄得多,而且常常为了一些更广泛适用的方法而拒绝这一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陈述说,数学家只有在他“剥离了所有可被感知的性质,例如,轻重、软硬,还有冷热或其他可感知的相互对立的性质”之后,才能测量各个方面的维度。亚里士多德,这位被中世纪的欧洲等同于“哲学家”[在中世纪的神学作品中,如果只提到“哲学家”而不直呼其名,那就是特指亚里士多德。]的人,发现相比于定量层面,在定性层面的描述与分析更有用。
我们会说重量、硬度、温度“和其他可感知的相互对立的性质”是可以量化的,但无论是在这些性质中还是在人类心智的本质中,这种可量化的特点都不是固有的。我们的儿童心理学家宣称,人类甚至在婴儿期就表现出了天生的计数离散实体的能力(三块饼干、六个球、八头猪),但是重量、硬度等,并不是作为离散实体的数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们是状态,不是集合;而且更糟的是,它们通常处于流变之中。我们无法数清它们;我们必须用心智之眼去观察它们,通过命令(by fiat)去量化它们,然后计数单位数量。这很容易通过测量广延(extension)来完成——例如,一支长矛有好几英尺长,而我们可以把这支长矛放在地上,沿着其长段切割后计算它的长度。但是硬度、热量、速度、加速度——我们到底要如何量化它们呢?
对于祖先所犯的错误,我们总是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但要知道,可以用单位数量来衡量的东西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例如,14世纪,当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学者们开始考虑,在尺寸之外,测量运动、光、热和颜色等不太明确的性质的益处之时,他们还继续推进,突破思维枷锁,开始谈论对确信、美德和恩典的量化。事实上,如果你能在温度计发明以前就想到衡量热(heat),那还有什么理由能把确信、美德和恩典预先排除在外呢?
第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我们都接受一种假设,即数学和物质世界是直接而紧密相关的。我们接受了一个看似不言自明的事实,即物理学这样一门与可感知的现实有关的科学,应当像数学那般极其精确。但这个命题并非不言自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命题,许多圣贤都曾质疑过它。
超越用手指和脚趾计数水平的数学可能起源于测量的进步。那时的人们需要给粮食称重后销售,需要在底格里斯河和印度河之类河流旁的市场中记录羊和其他动物的数目,这些数目都很大;人们也需要判定节气,如此才能选择合适的耕种时间;在埃及,人们还需要在尼罗河洪水退去后勘测潮湿荒芜的田地。这些都要求发展出更有效的测量。但之后,实际的测量和数学开始分化,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分离。称重、计数和勘测都是世俗的活动,但数学被证明具有超然的性质,它令那些试图挣脱世俗束缚从而寻找真理的人陶醉。勘测员们一定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知道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长度平方的和),之后,他们中的某个人才认识到这一定理的哲学意蕴和神秘含义。勘测员认为,这个定理是超自然事物存在的证据;它是抽象的、完美的,而且就像迷雾和风雨之中出现的彩虹一样令人敬畏。之后,原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艰难地走出泥泞的田野,并很可能建立了一种宗教秩序。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纯数学和计量学一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柏拉图说,前者属于哲学,人们可以通过它“把握真实的存在”。后者属于无常的事物:例如,战争,士兵必须懂数学,如此才能妥当地部署军队;还有商业,店主必须懂算术才能记录买卖的情况。
柏拉图建议我们远离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是流变之物”,他希望我们转向“永恒之物”。他引导我们注意绝对的美、善和正义,注意三角、方、圆的理念,注意他所确信的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抽象概念。他相信,只有借助“纯粹理性”,才能获得有关此类实体的知识。这种理性可以通过学习数学来开启其获取哲学知识的旅程。他建议未来的哲人王学数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数的本质”。
很难确切地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可以看看具体的例子。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公民数量是5040人。该数字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可能代表了在不借助特殊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能同时听到一个人讲话的人数上限,但柏拉图选择这个数字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这个数字是从1乘到7得到的。这就是数学的神秘主义,而从数学的神秘主义走向数字命理学要比走向复式记账法容易得多。
亚里士多德倾向于认为柏拉图主义缺乏实质内容。与他的伟大导师相反,他尊重那些用脚踢大卵石并且凭感觉到的疼痛坚持认为脚趾骨折是石头存在证据的人。他相信感官材料,但对数学在解释这些材料方面有多大用处持怀疑态度。例如,几何学好倒是好,但大卵石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球形,棱锥也不是完美的棱锥体,那么以几何学的眼光看待它们有什么用处呢?聪明的人当然会看出,一块大卵石比另一块更大,也比另一块要圆或不圆些,但不会浪费时间试图精确测量像物质现实这样多变的事物。
科学(以及现代社会的许多其他特征)可以被定义为将具有柏拉图式精确性的数学应用于亚里士多德所谓未经雕饰的现实后得到的产物。但是抽象数学和实用计量学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古典地中海文明之中的某些人物(如托勒密)成功地将二者交织在一起,但二者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中逐渐解绑,并在中世纪早期彻底分道扬镳。如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中的天才人物,他们利用数学技术来分析和处理测量结果,取得了智力上的成就,但在这些社会中,理论和实践最终也开始分化。16世纪,当西班牙人抵达墨西哥尤卡坦和中美洲海岸时,玛雅人正处于智力的低潮期,而且不再完善他们的数学和历法了。等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达东亚,中国人早已忘记了宋代制作巨型时钟的技术,而他们的历法也有缺陷,这种缺陷一直存在,直到耶稣会士帮他们纠正为止。
记录表明,将抽象数学和实际测量相结合,之后又疏忽、忽略和遗忘,这种进步与倒退的循环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西方独特的智力成就是把数学和测量结合在一起,用其理解一种在感官上可知觉的现实,而西方人完成了一次信念的飞越,认为这样的一种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统一的,因此也易于接受此类检验。为什么西方成功促成了这二者的强制结合呢?
欧洲人是如何、为何以及何时从或开始从在测量上看很可疑的原始思想走到或至少走向勃鲁盖尔在《节制》中为客户展示的那些严谨的艺术、科学、技艺和技术的?欧洲人是如何、为何以及何时超越了简单的感官材料堆积,不再像林鼠那样只会收集闪亮垃圾的?他们是如何、为何以及何时把自己从对柏拉图式现实无尽而徒劳的抱怨中拯救出来的?本书的主要内容解决的就是“如何”的问题。“为何”的问题也许是西方文明中最难以理解的,它像一个被谜团吞食的谜,也是本书后半部分要探讨的主题。“何时”的问题也许是这三个问题中最简单的,我们可以试着马上回答。
至少在新石器时代,西方文明就对量化有了粗浅的认识(我的羊群有12只山羊,而你的只有7只),但又过了几千年,这种认识才变成一种狂热。托勒密、欧几里得和其他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数学家在测量和数学方面做出了成果颇丰的贡献,但在中世纪早期,几乎没有几个欧洲人了解甚至接触过他们的著作。西方人信奉《圣经》,其中说到上帝“按照量、数和重安排好了万物”(《所罗门智训》11:22),但1200年左右,西方人还是很少考虑或认真注意可量化现实的概念。
建造了哥特式大教堂的那些石匠师傅是例外,他们建起了比例舒适、几乎不会倒塌的建筑,但他们掌握的几何学知识纯粹是实用性质的。他们不知道欧几里得,但就像今天优秀的木匠一样,他们实践几何学的方法,不夸张地说,就是使用几个基本图形: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等等。总的来说,他们的传统是通过口头传递的,而说到工作中的测量,其实就是师傅用他的手杖指着石头说,“你得给我从这里切”。
之后,在1250年到1350年之间,明显的转变出现了,但这种转变更多与实际应用而不是理论有关。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把时间范围锁定在五十年以内,即从1275年到1325年之间。有人建造了欧洲第一座机械时钟和第一门大炮,这些装置迫使欧洲人以量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来进行思考。波托兰航海图(Portolano)、透视法和复式记账法出现的确切年代无法准确追溯,因为这些都是新出现的技术,而不是具体的发明,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三种技术最早都是在那半个世纪或其后不久就出现的。
罗杰·培根测量了彩虹的角度,乔托有意识地以几何构造绘图,而西方的音乐家,此前几代,一直写的是一种被称为“古艺术”(ars antiqua)的笨重的复调音乐,而之后随着“新艺术”(ars nova)的兴起,就开始写他们所谓的“精确测量的歌曲”。此后半个世纪再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革新了,直到20世纪初,无线电、放射现象、爱因斯坦、毕加索和勋伯格席卷欧洲,才又掀起了一场类似的革命。
定量的迹象出现于1300年左右的西欧,它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此后,西方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一个世纪的恐怖之中,人口崩溃、长期战争、突然的毁灭、名誉扫地的教会、周期性饥荒和传染病的浪潮,一个个接踵而至——其中最严重的当属黑死病,但定量一直持续着。在那个世纪,但丁写下了他的《神曲》;奥卡姆的威廉挥舞着他锋利的剃刀;沃灵福德的理查德制作了时钟;马肖创作了他的赞美诗;而某位意大利船长则命令一名舵手,沿着一条罗经航向,从菲尼斯特雷角穿越比斯开湾前往英格兰,选择这一航线的依据不是口头或书面的资讯,而是航海图;另一个意大利人,可能是我们说的这艘船的所有者,则编制了一份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就像看着一只受伤的鹰不知不觉地游离进了一团看不见的上升暖气流,然后不断地翱翔。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