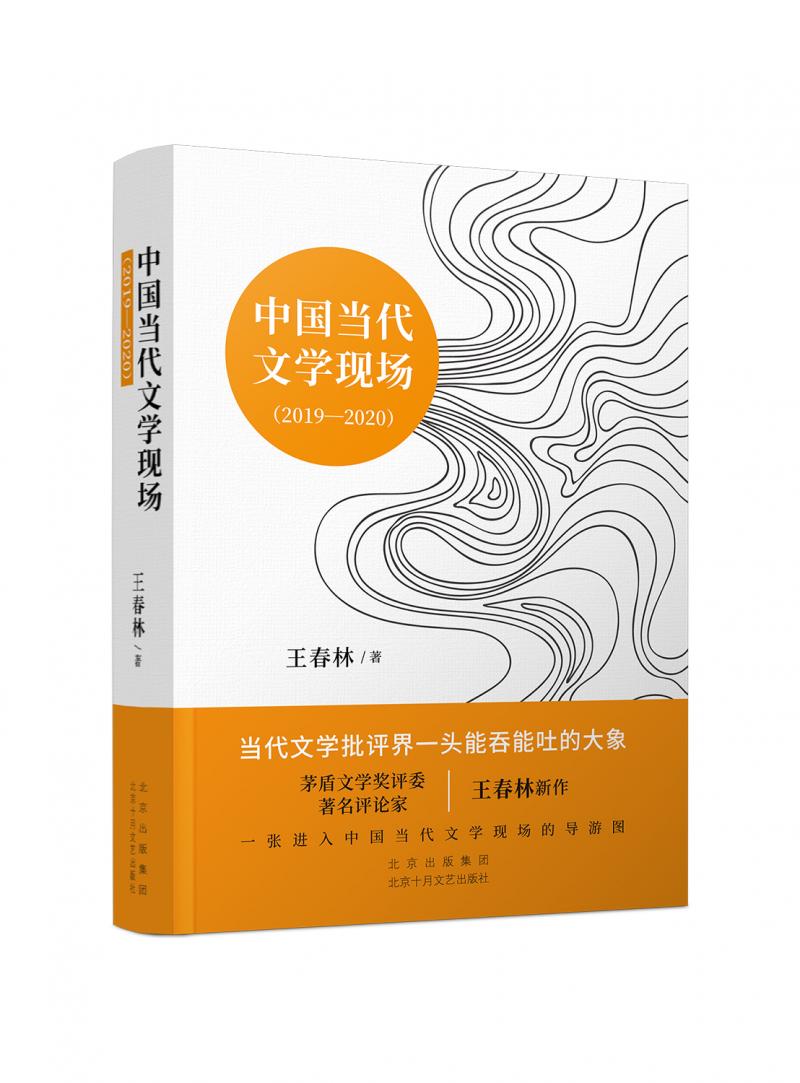《人世间》所具备的“史诗性”,所依循的理论标准来自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相关论述。然而,借用洪子诚的相关论述来衡量评价梁晓声的《人世间》,唯一可能引起争议的,就是第四点也即“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一般来说,一旦提及英雄,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战争,似乎只有在那血雨纷飞的战场上才能够产生所谓的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是显得多少有点狭隘了。我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相对于非常态的战争,更长的时段恐怕还是处于常态的和平时期。既然人类更多地还是生活在一种常态的和平时期,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常态的和平生活阶段,是否也同样还会有英雄生成。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只要是拥有相对丰富生活经验的朋友就都知道,在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要想做一个超乎于一般之上的生活英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很多时候,当历史形成了一种浩浩荡荡的蛮力向某种未必正确的方向涌进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幸掌握了真理并且有足够的勇气与这历史的蛮力相对抗的人类个体,就绝对称得上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形象。我们一定要设法破除只有战场上才会有英雄形象生成的狭隘观念,在一种广义的层面上,把那些日常生活中敢于逆错误的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类个体,也全都理解为生活英雄形象。如果我们以上的英雄观念可以成立,那梁晓声《人世间》中“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这部先后出现过四五十位人物形象的长篇小说中,最起码,周氏三兄妹中的大哥周秉义,乃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和平时期的生活英雄形象。
虽然小说一开始所讲述的,是20世纪初叶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贵族被迫迁居到远东大城市A市的故事,但严格说起来,这第一章的内容却不过是小说的序幕。整部《人世间》主体故事的起始时间,是第二章故事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具体来说,也就是1972年那个寒冷的冬季。从这个“文革”的中间时段开始,一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说差不多达到了半个世纪的长度。作家梁晓声对出身于A市著名的贫民区光字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英雄周秉义的人生书写,自然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作为市一中高三年级的优秀生,他原本是一门心思要考大学的。没承想,他的大学梦想却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变成了泡影。“上山下乡”运动前,身为“逍遥派”的周秉义,“除了躲在家里偷阅禁书,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上部,25页)“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上部,26页)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周秉义的成长过程中,“上山下乡”前这一段与女友相偕并肩读禁书的地下读书活动,的确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启蒙作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有过如此一种简直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一般的阅读禁书过程,从自己的家庭中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精神营养的周秉义,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能够在“上山下乡”成为兵团知青后的第二年,就被“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到周秉义要离家前往兵团做知青的时候,才会指着书箱特别郑重地告诉小弟周秉昆:“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下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遗憾的。”(上部,131页)事实上,在那个不正常的政治畸形时代,把爱情作为自己的精神宗教,不管不顾地追随“右派诗人”冯化成到偏远的贵州山区艰难度日的妹妹周蓉,之所以要专门写信给周秉义,也正是因为曾经在一起读过禁书的她,坚信自己的看似一意孤行,肯定会在大哥这里获得充分的理解。对于妹妹的行为,“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上部,180页)。在当时持有差不多相同精神价值立场的周秉义,非常理解,在那个“除了相信爱情”并不可能再相信其他什么的政治畸形时代,妹妹周蓉也的确只能万般无奈地把爱情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信仰来加以追求。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周秉义也更多地把自己和郝冬梅之间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类似于精神信仰的东西,所以,面对着在当时殊为难得的可以参军成为沈阳军区谢副司令员秘书的机会,他才会最终做出坚守在郝冬梅身边的选择:“他固然也是个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人,如果说郝冬梅是鱼,要获得熊掌必须失去鱼的话,那么他是那种立刻会对熊掌转过头去的男人。这与某些爱情小说对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些小说赞美始终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但道德律的禁忌并非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即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冬梅,如同基督教徒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圣经》。”(上部,298页)之所以能够养成如此一种习惯,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与郝冬梅之间其实有着太多共同的精神语言。唯其如此,他才会毅然在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爱情之间做出守护在冬梅身边的决定:“我未婚妻的父亲现在仍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而这不符合入伍的政审条件,所以我只有放弃此次难得的机会。”(上部,298页)说实在话,面对着如此难得的一个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周秉义的毅然选择放弃,一方面固然与那些爱情小说对他潜移默化的长期熏陶有关,但在另一方面,却更加充分地说明着他对内心里的自我道德律令与正义感的坚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作家梁晓声才会借助于叙述者的口吻,对周秉义做出这样的一些评判:“周秉义不是曹德宝(曹德宝是《人世间》中的一个人物),也不是于连,甚至没有弟弟秉昆那么一种蔫人的勇气。他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与皮埃尔。他本质上并不是那样的人,却很受这两个文学人物影响,在爱情方面尤其希望自己是绅士,很贵族。”(上部,309页)或许与天性紧密相关,实际上只是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的“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期一直头戴的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而设法适应”。(上部,311页)究其根本,梁晓声其实是在巧妙地借助如此一种方式给出周秉义之所以会显得那么“彬彬有礼”,会成为“不拘小节的平民”与“精神上的贵族”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在。
来源:十月文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