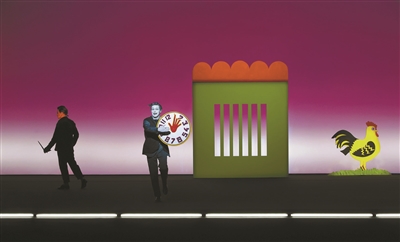7月31日,美国戏剧导演罗伯特·威尔逊在纽约水磨坊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3岁。
每当有年高的著名人物离世,社交媒体上常常有“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叹,多数都是习惯性的溢美之词,然而威尔逊让这句话有了真正的分量。
罗伯特·威尔逊 摄影/Yiorgos Kaplanidis
他不仅仅是当代剧场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更是一个时代的化身——一个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戏剧艺术边界的时代。
“我从未学过戏剧”
各大媒体发布的讣告都强调了威尔逊的多重身份,他不仅是一位戏剧导演,也是剧作家、视觉艺术家、建筑师、编舞家、演员、画家、雕塑家、影像艺术家、音效和灯光设计师。他有超过200部作品,跨越了传统的体裁:戏剧、舞蹈、歌剧、视觉艺术、行为艺术、视频、电影、音乐、杂耍。这种罗列不是为了彰显其个人才华的广度,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宣言,深刻地揭示了威尔逊先锋艺术实践的本质:他从不承认艺术学科之间的界限。
他曾经说过:“我看不到艺术和设计之间有什么区别。线条就是线条,空间就是空间。如果你是马蒂斯,你在画一条线;如果你是米开朗基罗,你在画一条线;如果你在设计一件衣服,你也在画一条线。”这种统一的视角使威尔逊能够自由地将对一个领域的洞察直接应用于另一个领域,而剧场显然是最理想的实验场域。
《睡魔》 摄影/Lucie Jansch
“戏剧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融合了所有艺术。”威尔逊在2022年接受采访时说道。在他的代表性作品如《聋人一瞥》《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内战》《黑骑士》中,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视觉艺术融为一体,完美地实现了瓦格纳追求的“总体艺术”。显然,威尔逊所理解的戏剧不是传统的以戏剧性文本为基础、以再现世界为目标的规范化样式,他不是按照既定的创作规则来选择合适的素材,而是在剧场持续探索表达的可能性。
研究者都会提到威尔逊的跨学科学习经历,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学习商业管理,转学到普拉特学院攻读建筑学,之后他又转向舞蹈,旁听了玛莎·格雷厄姆的排练,同时在纽约接触前卫艺术圈。没有被传统戏剧匠艺规训的威尔逊保持了原始的创作冲动,能够从根本上质疑和重新定义戏剧的边界。他直言:“我从未学过戏剧;我是通过实践学习的。如果我学的是戏剧,就不会创作我现在的这种戏剧了。”
用眼睛思考
威尔逊艺术创作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经历。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在一个极端保守的右翼社区长大,那里女人穿裤子是罪孽,去剧院也是罪孽,小孩收到的节日礼物常常是猎枪和牛仔靴。尽管那是一个与艺术世界相去甚远的成长环境,但自然环境却深深印刻在他的视觉感知中,他说:“得克萨斯的风景体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那是光,那是天空。”
美国学者埃莉诺·福克斯将威尔逊归入格特鲁德·斯坦因确立的“风景剧场”传统,称其为生态时代的田园诗,“在发达文化中创造了一个来自自然的脆弱意象记忆库。”这不仅是说,威尔逊作品中的意象元素,如明亮而空旷的舞台、作为主要构成元素的光影和天空、在虚空中点缀的引人注目的道具(犰狳、巨蜥和仙人掌等),都会让人联想到得克萨斯的广阔地貌,更重要的是,威尔逊的舞台不是人类行动的背景,而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人类成为风景的有机组成部分。风景不移动、不发展,而是在外部细节之间建立关系,比如树与树、树与山丘、山丘与田野;在威尔逊的风景剧场中,所有元素都保持独立的自由,没有等级制度,不服务于文本的阐释,因此要求一种视觉关联性而非逻辑推理性的感知方式。
要实现这种感知方式,威尔逊发现关键在于重塑时间体验。风景剧场不像戏剧性行动那样遵循因果逻辑的线性发展,而是通过极度缓慢的节奏和精确的重复,使时间成为观众直接体验的对象。从4.5小时的《沙滩上的爱因斯坦》、7小时的《聋人一瞥》到168小时的《卡山》,威尔逊通过延展时间来创造关联性感知的可能,让观众从线性的逻辑思维转向空间性的直观体验。
威尔逊认为:“如果你放慢事物的速度,你会注意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威尔逊的剧场里,当我们接近静止时,会比做大量动作时更能觉察到细微的运动。
“让观众迷失吧,这没关系”
威尔逊的作品常常引发争议,即便观众已经越来越熟悉他的舞台语汇,仍然不免感到一种无法阐释的焦虑。我在2014年才第一次现场观看威尔逊的作品,那是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出的《老妇人》,在那之前我已经间接地了解了他的许多作品,但现场体验完全是另一回事。《老妇人》是一部歌舞杂耍剧,碎片化的叙事中充满了荒诞、噩梦般的意象,我感到震撼和欣喜,但无法描述看到了什么。
《老妇人》 摄影/Lucie Jansch
也是那一年在北京举办的戏剧奥林匹克上,威尔逊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成为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碰撞。长达数分钟吃香蕉的哑剧和对贝克特文本的解构让许多中国观众感到困惑、失望、愤怒,甚至有观众在演出过程中大声要求他下台。这种激烈反应并非简单的文化差异,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理念的正面冲突,一种是强调情感表达和故事讲述的传统戏剧观念,另一种是威尔逊式的抽象、沉思的艺术体验。
威尔逊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曾说:“迷失是可以的!你不必每分每秒都去理解,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让观众迷失吧,这没关系。”这里的“迷失”当然不只描述在威尔逊的剧场中常常会有的迷离惝恍的状态,而是强调体验先于理解的感知方式。威尔逊深受苏珊·桑塔格“体验某事是一种思考方式”这一观点的影响,他不想发表声明,不想得出结论:“如果你看到日落,它必须有意义吗?如果你听到鸟儿歌唱,它必须有信息吗?”
争议并不总是消极的。威尔逊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被接受的过程,从最初的文化理念冲突到逐步的理解和接纳。
2017年的《关于无的演讲》在上海演出时仍有观众中途离场,2018年《睡魔》的演出则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响,观众开始适应他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和视觉优先的表达方法。到了2023年乌镇戏剧节上演的《H-100秒到午夜》,我们看到威尔逊的作品已经培养了一种新的戏剧接受能力,从追求明确答案转向拥抱开放体验,从理解剧情转向感受当下。
“威尔逊式”
在当代剧场术语中,“威尔逊式”(Wilsonian)已经获得了类似“契诃夫式”或“布莱希特式”的地位,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指向的美学概念。“威尔逊式”的核心要素已经成为实验戏剧的标准语汇:极度缓慢的节奏、精确的几何构图、强烈的色彩对比、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多媒体的综合运用等等。这些元素不仅出现在威尔逊自己的作品中,也深深影响了全球的实验戏剧。
这种认可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剧场艺术家中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与之媲美。
《沙滩上的爱因斯坦》 摄影/Lucie Jansch
当然,被广泛接受也可能意味着失去新颖性,商业化的成功使“威尔逊式”成为某种时髦通货。早在1999年,当德国学者汉斯-蒂斯·雷曼写作《后戏剧剧场》时,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威尔逊,认为几乎没有其他当代艺术家像他那样改变了剧场艺术,从根本上拓宽了我们对剧场可能性的想象;另一方面,雷曼也指出,在威尔逊后期的作品中,那些曾经极具新颖性的戏剧手段“失去了许多魔力,因为它们变得可以预见”。
尽管如此,每次接触威尔逊的作品时,我们仍然能够从熟悉中发现某种陌生,甚至感到一种奇异的慰藉。正如《H-100秒到午夜》所展现的那样,面对人类末日这样的终极焦虑,威尔逊仍然维持着他一贯的舒缓节奏,仿佛末日并不是灭顶的灾难,而只是一个沉思冥想的契机。
威尔逊用一生的时间告诉我们:戏剧不仅是娱乐,更是一种感受世界、理解存在的方式。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他的艺术遗产将继续提醒我们珍视那些缓慢、深邃、充满诗意的时刻——那是人类精神所需的养分,它更提醒我们永远保持实验的勇气,用新的创作回应存在的困境。
文/织工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