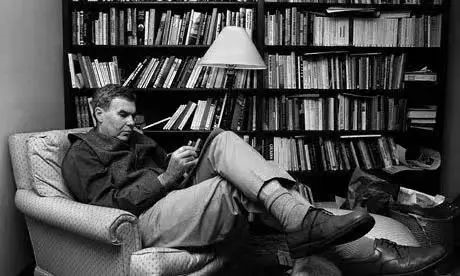★我人生的大部分都无关紧要,混乱不堪,没多少光亮能透进来。
★不过我希望我的小说吸引读者,让他们参与到故事中来,除非家里房子着火,绝没有办法把眼睛从文字上挪开。
★如果幸运的话,读完一篇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两行,能静静地坐上一分钟,思索刚才所读,也许心灵和智识能从之前停留的位置上挪动那么一丁点。
★随后收拾好心情,站起身继续下一件事:生活。永远的生活。
下文选摘自新经典文化推出的雷蒙德·卡佛最新杂文集《需要我时打给我》一书中《论写作》一文。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发现自己没法将注意力集中在长篇小说上。有段时间,我读得困难,也写得吃力。我的注意力难以持续,不再有耐心去尝试长篇小说。这段经历说来话长,在这里提起也很没意思。但我知道,我现在选择写诗和短篇小说,和这大有关系。
进去,出来,不停留,往下走。又或者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已年近三十,失去了所有远大的志向。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觉得是件好事。野心加上一点运气,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助力。太多的野心和坏运气,或是全无运气,那可就致命了。才华也必须要有。
有些作家很有些才气,我没见过哪个作家是毫无才气的。但对事物有独特和准确的看待方式,并能找到合适的语境将之呈现出来,那就另当别论了。《盖普眼中的世界》自然是约翰·欧文眼中的奇妙世界。弗兰纳里·奥康纳有另外一个世界,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眼中也有自己的世界。契弗,厄普代克,辛格,斯坦利·埃尔金,安·比蒂,辛西娅·奥齐克,唐纳德·巴塞尔姆,玛丽·罗宾逊,威廉·基特里奇,巴里·汉纳,厄休拉·勒古恩,他们也都各有各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好的作家,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来重塑这个世界。
我说的这些近似于风格,但也不全是。我说的是作家独特而毋庸置疑的标记,烙印在自己所写的一切作品之上。这是他的世界,仅此而已。要将一个作家同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这是方法之一。才华不是。才华多得是。但如果一个作家拥有独特的视角,并能将之付诸艺术的表达,这个作家的名字或许能留存一段时间。
伊萨克·迪内森说她每天都写一点,不抱希望,不怀绝望。总有一天我要把这话写在三乘五英寸的卡片上,贴在我桌子旁边的墙上。现在我的墙上就有几张三乘五的卡片。“表述的根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埃兹拉·庞德说。无论如何这都不该是写作的一切,但如果一个作家拥有“表述的根本准确性”,那么至少说明路没有走偏。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的卡片,是契诃夫一篇小说中的半句话:“……突然,一切在他眼前明了起来。”我发现这些词句既奇妙又饱含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明晰,同时又暗含微妙的启示。它们也带着谜一样的色彩。过去不明了的是什么?为什么又突然间变得明了?发生了些什么?最重要的是—现在呢?结局总是在这种突然的启悟中产生。我能感受到强烈的释然和期待。我曾无意中听到作家杰弗里·沃尔夫对一群写作课的学生说:“别耍小花招。”这句话也该写到三乘五的卡片上去。我会小小地修改一下,改成“别耍花招”。没了。我痛恨花招。不管是花招还是把戏,拙劣的还是精巧的,只要在一篇小说里露头,我就恨不得找地方躲起来。
花招本质上让人厌倦,而我很容易厌倦,也许是我的注意力没法长时间集中的缘故。但是极度精明矫饰的写作,或者仅仅是贫乏愚蠢的写作,都会让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花招,不需要把戏,甚至不需要是整条街道上最聪明的人。有时一个作家需要冒着被人当傻子看的风险,单纯站着,注视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落日,或者一只旧鞋子——带着绝对而纯粹的惊异。
几个月前,约翰·巴思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说,十年前,他小说创作研讨课上的几乎所有学生都对“形式创新”感兴趣,但是现在好像不一样了。他有点担心八十年代的作家又开始写那种家庭作坊式的长篇小说。他担心文学实验会和自由主义一道消亡。每当我发现这种关于“形式创新”的丧气讨论进入我的耳朵,总是会有点紧张。很多时候,“实验”成了一个幌子,用来掩饰写作中的草率、愚蠢和模仿痕迹。更糟的是,它变成了对粗暴对待和疏远读者的一种许可。
很多时候,这种写作并不能带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新消息,要么就只是描摹一番荒漠图景,仅此而已——零星的沙丘和蜥蜴,没有人。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小说实验是原创的,是来之不易的,是令人欣喜的。但他人观察事物的方式——比如说巴塞尔姆——不应该被其他作家效仿。行不通的。这世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其他作家如果打着创新的旗号,试图挪用巴塞尔姆那独特的情感表达或场面调度,只会陷入混沌和灾难,更糟的是自我欺骗。真正的实验者必须像庞德说的那样创造新意,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去发现事物。不过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与自己的神智告别的话,他们也应该与我们保持联系,将自己世界的新消息带到我们的世界来。
在诗歌和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用普通但精准的语言写平常的事物——一张椅子,一幅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只女人的耳环——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用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对话让读者脊背发凉——纳博科夫就拥有这种可以带来艺术享受的能力。
这种写作最让我感兴趣。我痛恨草率随意的写作,无论它们打着实验的旗号,或仅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笨拙呈现。在伊萨克·巴别尔那篇绝妙的短篇小说《居伊·德·莫泊桑》中,叙述者有这么一段关于小说写作的话:“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比任何钢铁都更具刺穿人心的力量。”这句话也该放到三乘五的卡片上去。
埃文·康奈尔曾说,他修改自己的短篇小说时会拿掉所有的逗号,如果过第二遍时重新加上的逗号和原来的位置一样,他就知道,小说完成了。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我尊重这样行事的用心。毕竟,字词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它们最好是妥帖的,和恰当的标点一道,表达它们应该表达的意思。如果字词承载了作家自身无节制的情感,或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不严密或不准确—如果它们在任何意义上模糊不清—那么读者的眼睛会直接从上面略过,什么都不会发生。读者自己的艺术敏感也就完全不会被调动。亨利·詹姆斯把这种不幸的写作叫作“弱规格”写作。
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他们赶工写书是为了钱,他们的编辑或老婆不是要分钱,就是要分手——总之是为自己没写好辩护。“要是多花点时间在这上面,我能写得更好。”我的一个小说家朋友这么说时,我简直目瞪口呆。放到现在一想,我还是同样的感觉,索性不去想了。这不关我的事。但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拿出自己全部的本事写好一个作品的话,还写它干吗呢?说到底,用尽全力的满足感和辛勤劳作的成果,是我们唯一能带进坟墓的东西。
我想对那个朋友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做点别的去吧。一定还有什么更容易,或许还更诚实的工作能让你赚钱糊口。要不然就倾尽你的能力、你的才华去写,别找理由,别找借口。别抱怨,别解释。
在一篇标题就叫《短篇小说写作》的文章中,弗兰纳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一种发现的行动。奥康纳说当她坐下来开始写短篇小说时,她常常不知道要往哪儿走。她说她怀疑没几个作家会在刚开始写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她以《善良的乡下人》为例说明自己短篇小说的创作方式,说她直到临近尾声,才知道故事的结局:
我刚开始写那篇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装着条木腿的博士。只是有天早上我正写着两个较为熟悉的女性角色,不自觉就给其中一个人的女儿装上了条木腿。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又加了个圣经推销员,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拿他干吗。直到写到他去偷木腿这个情节前十一二行,我才知道他要去偷。但一旦我发现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我就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多年前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就对她的—或者无论是谁的——这种写作方式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羞于启齿的小秘密,还因为这个多少有点不安。我确信这种写短篇小说的工作方式就是在暴露我自己的短板。我记得读到她的这些话时,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我曾经在只想好故事的第一句话时便坐下写作,结果写成了个不错的故事。接连几天,我都在脑子里琢磨这句话:“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我知道有个故事在那儿,等着被人讲出来。我能从骨子里感觉到有个故事属于这个开头,我只需要找时间把它写出来。我找到了时间,一整天——要是我想的话我可以工作十二个,甚至十五个小时。我也这么做了。那天早上我坐下写出第一句,剩下的词句便接踵而至。写这个故事像是写诗,一行,一行,再一行。不一会儿,一个故事就成形了,我知道那是我的故事,我一直想写的那个故事。
我喜欢拥有危险感和胁迫感的短篇小说。我觉得故事里可以有点胁迫感,理由之一就是这对小说的销售有帮助。必须有一种紧张的氛围,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有一些事情永不休止,要不然,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什么故事可言。在小说中,一部分的张力是由实在的字词创造的,它们连接起来,组成故事中可见的行动。但张力同样也来自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事物平滑的(有时是破碎动荡的)表象之下的景观。
V.S.普里切特对短篇小说的定义是“余光一瞥所见”。注意这个“一瞥”。先是一瞥。再是这一瞥被赋予生命,成为照亮此刻之物,或者,要是我们足够好运——又是这个词——这一瞥也许会有更深远的结果和意义。
短篇小说家的任务是将他全部的力量投入这一瞥中,充分调用他的智识和文学能力:他的才华,他的分寸感和妥帖感:事物真正的样子,和他感知那些事物的方式——与他人决然不同的方式。而这一切,要靠清晰准确的语言来实现。语言给细节以生命,将故事为读者点亮。细节要具体传神,语言就必须确切精准。有时词句会因精准而显得单调,但它们仍能传情达意。如果运用得当,它们能正中人心。
内容选自
雷蒙德·卡佛/著
姚卉/译
新经典丨南海出版公司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