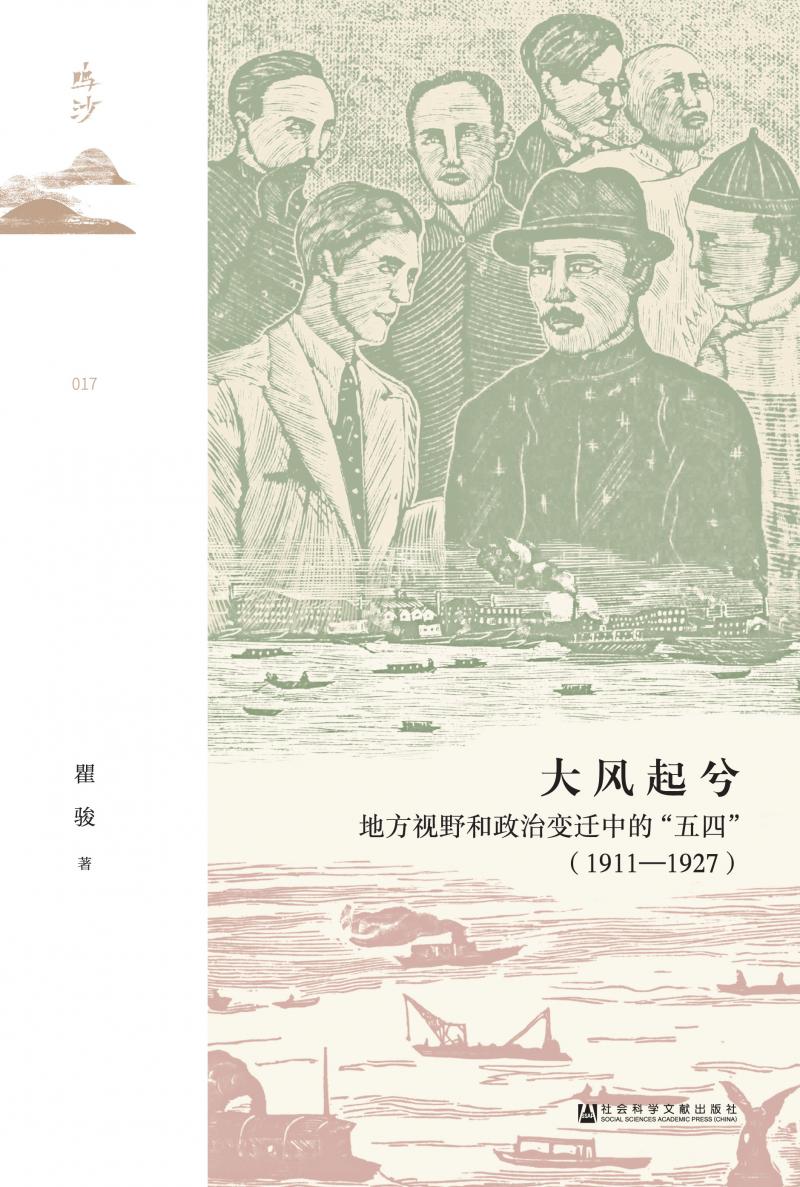这本书所言的“五四”或者五四运动是“大五四”的范畴,指大致从1911年开始,至1927年前后,持续近二十年的那些相关联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其关键词“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更精确的说法可称之为“长程革命”)和围绕它们的研究思考在绪论里有详细展开。不过从“史料形成”来说,绪论更多呈现我在2019年前的想法(当然做了补充并使其更清晰),本书成形的过程和近五年的一些思考需要在这篇自序里略作交代。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辛亥革命,讨论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互动,大致属于政治社会史的范畴,2007年完成答辩稿。200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不久会有修订本上市)。2017年,我出版了《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和《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两本书都大致属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畴,其中一些章节是第一本书的拓展和顺着第一本书的思考,另一些章节则对五四已有一定的涉及和关注。
就本书而言,它的写作由四个机缘促成。
第一个机缘是2009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蒙罗志田老师不弃,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以机会,参加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盛会。当时我的研究颇“自限”,定位为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五四属于没有积累,不敢进入的领域。而且手边还有清末民国教科书、现代国家观念普及和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流动等题目要做(形成的书稿至今还在文件夹中)。可以说,没有罗老师的关爱和督促,我是断然不敢“跨”出这一步。犹记得当时留校不到两年,工作同时要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外语培训,准备赴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参会文章是在上课、培训之余一点点挤出来的。打字打到眼睛酸涩时,常会望一望复旦凉城老家窗外的树影,虽然劳累但心情愉快,产出的作品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再思——以“转型时代”(1895—1925)学生生活史为例》。这篇文章是我进入“五四”研究的开始,所以若以“十年磨一剑”比喻,剑的质量如何由读者评判,磨剑确实已超过十年。
第二个机缘是2015年王家范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讨论会上的发言。先生无论是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还是对我个人的成长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5年的发言是先生给予我众多深刻启发中的一个。在这个发言中先生虽以“门外谈”自谦,但基本奠定了日后我从事这一题目的大方向。那就是:
新文化运动,是个全国性的题目,是牵动中国社会走向的大局性题目,谈的都是大思想、大人物、大趋势。作为读者,我常想到,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新思潮,除对大城市外,对于中国大多数基层民众、广大乡村和市镇的人群,究竟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似乎这类题目还比较少见。
对此先生提示要注意那些地方读书人,比起生产“新思想”的少数“精英”,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众”,常常被研究者遗落在“底层”。因此要“细分地区、时段以及各类不同性格的人群,做些具体细致分析”。
第三个机缘是2014年、2019年两次到台湾访学、参会。2014年,王汎森老师予我机会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当时老师正承担“院务”,极繁忙,但多次拨冗,让我有幸能充分聆教。老师议论的范围极其广泛,大到明清变局、转型时代,小到学界掌故、学人评点。其中我记忆犹深的是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我每天临睡前的消遣,是读十几页邓之诚日记的影印件。”以字迹难辨的邓氏日记为“消遣”,老师的学如海深可略窥之。2019年,老师又邀请我参加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的所见所闻对我的“五四”研究又有不小的推动。两次在台期间,陈熙远、王鸿泰、巫仁恕等老师对我亦多有指点、帮助,张罗琐事、操办讲座、邀请餐叙不一而足,实感之念之。正是依托这样的访学环境。本书的不少材料就得自郭廷以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等处的丰富收藏。本书第一章更是伴随着南港淅淅沥沥的热带雨声完成的。
第四个机缘是自2016年起,蒙王奇生老师、高波兄、袁一丹女史等抬爱,多次到北京参加由他们发起、主持的工作坊、讨论会。会上常有以往我不熟悉的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民党史的优秀学者,也多有社会学、政治学、近现代文学的相关优秀学者,这样的参与对我研究的提升大有帮助。本书第二、三、五章的初稿就是在这些场合得到了最初的批评和指正。
由此,本书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进一步“顺流而下”的产物,也是由若干机缘所推动的产物。若定位于当下,则本书在“地方视野”和“长程革命”下关注的大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近年来革命史研究一方面是“热”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冷”的。“热”的一面多有文章、综述可以发见,不必赘述。“冷”的一面则可以稍谈谈个人观感。比如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据熟悉的杂志编辑说组稿已相当不容易。2023年是“二次革命”110周年,全国更是几无相关的学术讨论会。这种“冷”与“热”的对比背后,其缘故仍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被研究者切割得太细碎,不把它看作一个连续性过程(即“长程革命”),而是过于按照政治力量的分野来条条块块地做研究,稍忽视革命的动力、氛围、环境、心态由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催生,可以在整体史的观照里做更多推进。
若具体到五四,情况就更为特殊。特殊表现在五四运动是不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仍然“需要讨论”。数十年来史学变迁的结果是多以“启蒙”“文艺复兴”等主题词讨论五四运动,而淡忘了为何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转捩点。一些“五四”研究是没有“父母”的,其所讨论的人物似乎只参与了五四运动,既没有参与过辛亥革命,也没有参与过“二次革命”;也是没有“子女”的,其淡忘了正因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革命环环相扣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之后历次革命的酝酿和展开,反而认为之后的历次革命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宗旨和目标,令其戛然而止;是没有“柴米油盐”,只有“风花雪月”的,其认为改变中国的贫弱状态不需要激烈的行动,不需要奋起救亡,只需要优雅地发议论、写文章、出思想就可以了。
正是由于本书关注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而革命的主体大多是那个时代寻找自己出路和时代出路的青年。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在乎的是能思考当时青年的思考,体会当时青年的处境。随着自己年齿增长,这样的思考和理解虽然变得越来越难,但有两个理由让我要做此努力。
一个理由是学界目前好讲“普通人”的历史、“失语者”的历史,这当然大致不错,也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这样的潮流和风气也带来一个问题——谁又不普通呢?有的人即使日后成为著名人物,如史学家钱穆,他也有“微时”,也有“默默无闻”之时。同时有的人年轻时虽然风光无限,煊赫顺遂于一时,但到中年却经受挫折,在人生后半程饱尝坎坷,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普通”?因此,怎么讲一个人的“微时”与“默默无闻”之时,又怎么讲一个人从意气风发到失意颓唐,一个人和一群人的青年时代都是合适的切入点。
另一个理由是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我熟悉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一些作品仅仅在做,并全力以赴地去做胡适的代言人、吴宓的同情兄、徐志摩的八卦爱好者。如此“做法”当然能够提供一些谈资,谱写一些心曲,满足一些想象,但离那个时代的基本人群和基本特征就有一些“隔”,以致字里行间常常对青年是“板起面孔”来的,是很有些“说教”味道的。
不错,历史研究确实重要的是“理解”,需要和历史人物“处同一境界”。但这样的理解不能只去理解那些精英,“处同一境界”的目的不是幻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不那么“高看”自己,把胡适等人当作“普通人”来研究,尽量戒除文字中的“说教”味道(虽然未必可免),是我对自己的戒律。
在这样的戒律下,本书一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讨论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社会的拓展。以往讨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对其如何经由各种渠道“下行”到各个地方,“下行”过程中新文化的主要受众为谁,在“下行”的过程中新文化如何改变了地方社会尤其是地方社会中读书人的生活,都关注不多,这一章即在此向度上展示“地方视野”对于五四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讨论五四运动“下行”至地方社会时,受其影响甚大的一个读书人群类——“地方老新党”的生命史。这些“地方老新党”与五四的互动可以形容为“人生中途突遇碰撞”,即让他们生命史剧烈变动的起点在晚清,五四到来他们继续面临剧烈变动,五四之后,剧烈变动仍在持续,一直延展到国民革命,延展到抗日战争,延展到解放战争。因此这批人一生中最大的感受之一可能就是“进退失据”,想跟上时代潮流却又难以跟上,想抓住上升之阶却又基本落空,因此无论是谈地方视野,还是谈长程革命,这群人的经历和心境都是复杂且丰富的例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为“地方”的反应,何为身处“变迁”之中。
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讨论五四运动“下行”至地方社会时,受其影响甚大的另一个读书人群类——边缘知识青年。由于个案太多,且前贤已有群像性的讨论。本书集中于一个典型人物——钱穆。钱穆对于自己的五四经历和相关生命历程有丰富的“日后回忆”和充分的“自我塑造”,集中体现在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里。本书做的工作是将《师友杂忆》中提供的那些细节重新放置到历史过程中去,复原“细节”的形成,重建历史的语境,以将一个日后的著名史学家,但当时尚是地方上的“小镇青年”的“五四运动史”与“革命接触史”重新呈现出来。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吴宓、与吴宓相联系的“学衡”诸人和他们的学生辈。关于学衡派的研究(此概念如何形成我在登刊于《读书》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说明)目前最明显的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史料“拿来就用”,且不分轻重、“揉做一团”地使用。一些研究不去分析史料的“形成过程”,也不去分析不同史料的“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利用未整理出版的资料就更无从谈起。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学衡”诸人和他们学生辈的研究变成了“自恋的舞台”、“悲情的出口”和“连续性系谱的幻影”,忽视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学生辈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大革命”时代里,且中国各方面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有鉴于此,本书较多利用未经整理出版的重要新史料如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以厘清吴宓等对于五四、对于新文化的个人的、“有限性”的观察,以及其观察时所凭借的诸种思想资源。进而讨论“学衡”诸人和他们学生辈的互动与离合,以期为五四的后期延展增加更为可靠,更合乎历史情境的一块拼图。
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的是五四如何与国民革命“相衔接”。本书以《中国青年》杂志为个案,分析了塑造五四革命的“新文化时代”如何递进到塑造国民革命的“主义时代”;以江绍原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民俗学家”的人物为个案,揭示了一个五四青年在国民革命中的境遇浮沉、政治参与与思想延续。在此基础上,试图略窥“长程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五四在“长程革命”中对一群人和一个人又意味着什么。
和以往著作一样,本书写作依赖诸多师友长期的、全方位的扶掖、奖进。许纪霖师对五四运动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有常年深入的研究和心得,近年多篇相关宏作给予我极大启发和提示。马自毅师退休后常游历海外,调养身心,她用“身教”告诉了我学术研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以其代替积极健康的整体生活。
许、马二师外,多年来众多师友对我的指点、帮助和提携难以胜数,常使我感念于心。这里要特别提及的:一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盛差偲兄。近年来自己的院系行政工作日重,只能利用零敲碎打的时间来做研究,较多依靠电子版材料。无奈这一两年遭遇困难,以往获取资料极方便的地方如“国学数典”论坛一朝星散,再无恢复之日,因此只能四处求助。在求助对象中打扰最多的就是盛兄。他则不厌其烦,每有索求必有回应,充分纾解了我的读书之困和获取资料之忧。最近研究若有寸进,盛兄厥功至伟。
二是武小力、李宗庾、潘璐、邵雨婕、韩千可、黄卓贤等同学。他们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承担了不少史料的核对工作和注释的修订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对书稿做了不少纠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向你们道一声感谢。
三是MY WAY小组、“铁锅乱炖”小组和“西山森林N园”小组。在新冠疫情的三年里,这些小组里凝结流淌的友情温暖且动人。
最后,必须要写的一段话是:一本书署名的作者虽然只有一人,但背后凝聚着作者家人全方位的支持和牺牲。因此所谓自己的“努力”实无足挂齿,这本就是你从事这项工作的“分内之事”。但家人的关爱和理解却非理所当然,不是天然就该享有的“福报”,当牢牢记之、惜之,并更多思考和实践自己对家人应做的“分内之事”,进而查漏补缺。
是为序。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