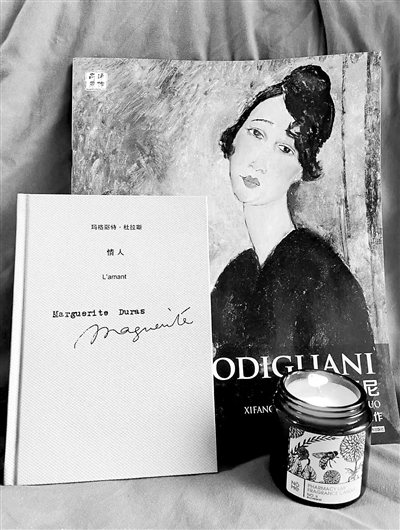廖斯婧黄荭毛尖
时间:4月27日18:30
地点:北京法国文化中心
主题:聚焦玛格丽特·杜拉斯:
从文字到影像
主持人:廖斯婧
与谈人:黄荭、毛尖
那栋属于她的房子,对她具有重要的意义
廖斯婧:纪录片《写作》是1993年杜拉斯去世之前拍的,那时候杜拉斯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黄荭:拍摄《写作》时,她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写作了。
廖斯婧:纪录片中她所在的房子呈现度很高,看上去那所房子对杜拉斯本人的写作非常重要。
黄荭:这个房子是杜拉斯在上世纪50年代拿了《抵挡太平洋堤坝》的电影改编权后买的。在此以前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而这栋房子是属于她的。
买房子这件事对经历过印度支那的杜拉斯来讲有着决定性意义。她说她是没有故乡的,因为她出生在印度支那,那是已经永远不存在的一个法属殖民地,故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乡,所以她经常说自己是身在无处。她买了这栋房子后,这栋房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故乡。
毛尖:还有一点,因为这栋房子属于大房子,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她母亲的包括她童年的一个梦想。她一生住的三个地方构成了她的整个人生,而且她选择这三个地方背后的心理机制都跟她儿时在印度支那的经历有很强的关联。
廖斯婧:杜拉斯常提到孤独,她一个人独居的时候,这种孤独感会加倍放大,但她也讲,只有在房子里她才会感觉到这种深刻的孤独,如果到院子里,孤独感就会减弱了。
毛尖:因为到了院子里,可以看到花草树木,听到鸟叫,听到街道传来的声音。
在那种绝对的孤独当中,杜拉斯会感觉身处洞底,这时候唯一能把她从孤独中捞上来的,其实就是写作。而写作本身又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让写作拯救自己,自己就要更加强大。杜拉斯要驾驭写作,因为她不知道写作要往何处去,她真正写作时,就在这个房子里,一定要写到底。她没有一本书是不写到底的,所以可以说这栋房子就是她的写作之所。在这里,她真正理解了写作的深刻意味。
她为写作而生,她具备了所有成为大作家的必要条件
廖斯婧:影片里她对写作有一段引述,我印象深刻。她说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就必须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的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如果丢弃就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这段话给我的感觉是,她觉得书是有生命有意志的,那么书从哪一刻开始成为书?从下笔的那一刻开始?作为写作者,如何理解杜拉斯对书的认识?
毛尖:很多时候普通写作者拿起笔是一个触动,比如生命中有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会促使他拿起笔写作。成熟的作家很多时候是一个动机,而杜拉斯是那种天生写作的人,她具备了所有成为大作家的必要条件,包括单亲家庭,是法国人但生长在越南,这些都促使她产生写作的冲动,再加上杜拉斯很喜欢钱,写作让她看到“钱景”。她曾经说如果不写作会去酗酒。也就是说如果不写作,她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她活着写作,重病在床依然会记下一些东西或者口述,让她的男朋友帮她记下来。
黄荭:某种程度上说杜拉斯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生活中的杜拉斯变成纸上的杜拉斯,所以她会讲: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那存哪里了呢?在书里了。
廖斯婧:她会陷入一个循环吗?她反复提到,是孤独造就了她的写作,但反过来写作会让她更加孤独吗?
黄荭:孤独是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尤其是像杜拉斯这样的写作。杜拉斯其实是情绪性的写作,她不能受到干扰,所以她写作的时候非常孤独,她只有在孤独中才能创作。她的创作没有计划性,她说她不能去谈论一本正在写的书,因为她也不知道要写往何处。她不会写提纲,也不会做计划,所以我觉得写作也不能拯救她的孤独,能拯救她的可能是朋友们的关爱。
电影是她拯救孤独的一个方式
黄荭:拯救她的孤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拍电影。写作是一个人的,做音乐可以两个人,电影是可以一群人拍的,所以拍电影某种程度上是拯救她的孤独的。
她的电影跟一般的电影非常不一样。她觉得商业电影没有任何营养,应该全部毁灭,所以她才会提出一种新的审美逻辑,她的电影非常决绝的时候,没有画面,只能听到话外音。跟一般电影相比,更少情节和人物,故事通过画外音串联,没有视觉冲击力,营造的是一种氛围。很多时候还是一镜到底,某种程度上她的电影是她写作的延伸。
廖斯婧:说到电影,我记得您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里有一章用了“杀死电影”做题目,所以她拍电影的一个动机是希望从写作的孤独中摆脱出来?
黄荭: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拉近母子关系。因为她儿子乌达没有固定职业,他向母亲表示对拍电影很感兴趣,所以杜拉斯就开始自己当导演,也可以给儿子找点事情做。
电影这样拍就死掉了
廖斯婧:毛尖老师对于杜拉斯的电影怎么看?您喜不喜欢杜拉斯的电影?
毛尖:如果2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装着说还蛮喜欢的,因为年轻时对那种自己不能理解的更要觉得里面有东西,但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现在我其实蛮讨厌这样的电影的。
我觉得杜拉斯是反电影的。比如说《印度之歌》,那么长,却只有70个镜头,其他全部用画外音进入。她的一个电影理念在当时可能是比较先进的,甚至我自年轻时也接受过她的理念,就是音画分离。很多人在电影中会采用一两分钟的音画分离,比如说一张全家福照片在桌上,看上去一家和谐,但画外音是夫妻俩在吵架。这种我觉得挺好的,但杜拉斯的音画分离坐到了非音画分离的位置上去了。
很多人赞美杜拉斯音画分离的电影实验,认为做成了电影风格。但我觉得她已经不是音画分离了,因为音画分离是需要建构在音画有张力的位置上的,《印度之歌》还有张力,里面阐述一个印度女孩一生的时候,用了太阳升起又降落的镜头,但后来她把同一段音轨放到另外一部电影中去了,这我觉得就是反电影的。电影做到这个地步,是杀死电影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不觉得杜拉斯是用电影来抵抗孤独了,她把电影做成那么孤独的东西,谁还看电影啊!
同时我从来不认为杜拉斯是反商业的,在那个小资买不起钻石的年代,她用她的小说让小资感觉戴上了文本的钻石。我们的青春时代那么爱她,被她席卷而去,因为在她的小说中看到了钻石的光芒啊。
还有,她用这么孤绝的方式来反电影,其实包含了她试图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从人群中拔地而起。她一直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量,这也是我们喜欢她的地方。但我这个年纪了是真的不喜欢她这么拍电影。我喜欢她的《广岛之恋》和《情人》,但都不是她自己导演的。我们今天还在谈论她的电影,是因为她是写作者杜拉斯,而不是导演杜拉斯。她的理念会留在电影中,但她的电影是留不住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约,不是有钱就能拍片的。
黄荭:她有建设性意义,她一直坚持小制作,认为小成本也可以拍出好的艺术作品。她的理念是不要被商业操纵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她给予了电影自主性,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她变成了联合作者,这就是我说她用拍电影来抵抗孤独,因为会有一群人一起投入在一件共同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她其实是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这跟她年轻时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样的,她一直都在身体力行。
毛尖:这我很同意。她的电影适合写电影论文,很多观点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还是觉得电影这样拍就死掉了。
看了她的电影,会更想去看她的小说
廖斯婧:杜拉斯对于电影跟文本有一个结论: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的决定性魅力就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她说我拍电影就是为了获取文本的创造性经验。毛尖老师怎么看她这样的观点?
毛尖: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在她自己的文本中是有可能性的。其实看了杜拉斯的电影,会更想去看她的小说。杜拉斯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生命暗部的人,我觉得电影是蛮有呈现暗部的能力的,但她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看了杜拉斯的电影会重新去看小说,因为在电影中没有得到满足。
黄荭:她的电影也用了很多黑,很决绝的黑,尤其《大西洋的男人》里那30分钟的黑。因为太黑了,所以我们希望在文本里找一点光亮。
廖斯婧:杜拉斯作为写作者是自恋的,这个特质在电影团队合作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她会与摄制组人员交流或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吗?
黄荭:她之所以会投身拍电影,其实就是自恋的结果。因为她对所有改编自她作品的电影都不满意,她还一直觉得自己被剥削了,所以要自己去拍。
毛尖:结果她也没拍起来。比如她并不知道怎么用电影去拍“暗”,她认为她写的都是暗,就拍30分钟暗。
廖斯婧:所以如何将文本语言转换成电影语言,她做得不够。
黄荭:对,拍片的时候杜拉斯也是很有主见的,她会贯彻自己的电影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她会一条道走到黑。
毛尖: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人格自恋挺好的,但一个导演如果是自恋人格是做不好的。因为导演是工作团队,完全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的话,真的就黑了。
黄荭:最初《情人》出品人是找杜拉斯做编剧的,后来一是因为她的身体出了状况,另外她也没有办法跟团队合作,所以出品人就换了雅克·阿诺来做导演。杜拉斯也完全不能接受雅克·阿诺的理念啊,她认为雅克·阿诺更注重的是历史细节和真实,而这恰恰是她所要摒弃的。真的就是一言不合,杜拉斯很快就被搁到一边了,阿诺自己找了编剧,很快《情人》拍好,大卖。
写专栏的杜拉斯和写小说的杜拉斯非常不同
廖斯婧:杜拉斯曾经谈到她眼中的写作,她说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去写已经被勘察好的、盘点过的故事,这在她看来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贫乏。您二位怎么理解她对于写作的这个认知?
黄荭:杜拉斯是感觉型的写作者,她是完全拒绝先有一个故事梗概的写作的。她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在黑暗中让故事慢慢成形,她喜欢的是这个过程。她认为这个过程是真正的写作。所以我觉得最吸引她的是从混沌中来,然后慢慢触及,再看写作走向何方。
毛尖:我很认同黄荭说的,也很同意杜拉斯关于写作的观点。因为如果知道结尾在哪里,我们就不要看了,就像今天的很多烂片。但杜拉斯不一样,她的男女主人公登场时,我们即使知道会发生事情,仍然会被席卷而去。
杜拉斯的小说不是走在主流道路上,她的用词狂野豪华,在死亡和活之间另外有一条岔路,这是杜拉斯特别激动人心的地方。我们看她的小说,会觉得好像又走进了青春期,那种胆大妄为,会有一种犯罪感,那种犯罪感是我们的青春,非常非常美。这也是杜拉斯特别迷人,尤其打动30岁以下阅读者的地方,因为她和青春期特别八字相合。
廖斯婧:杜拉斯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黄荭:她是对语言非常有要求的作家。我们读的时候感觉漫不经心,其实她有无数次的修改,从她的手稿就可以看到。另外她每天早上会去写作,比较自律和勤奋。她的房子总是很整洁,她一定要把东西都收拾好,才能够开始写作。
廖斯婧:杜拉斯有很多身份,她也写专栏,毛尖老师曾说专栏作家杜拉斯跟小说家杜拉斯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吗?
毛尖:一个作家很难有两种文笔,但是写专栏的杜拉斯和写小说的杜拉斯非常不同。
我自己也写专栏,我知道写专栏的生活是要有规律的。杜拉斯说当觉得自己要陷入疯狂、需要纪律性的拯救时,就会去写专栏。我自己也是,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知道有专栏必须要交,当把这篇专栏写完的时候,又会成为一个正常人了。
通过专栏可以看到杜拉斯的政治感,这是非常重要的。看她的小说会觉得她的道德观念比较低,她在小说中会纵容脏乱差的东西,但是进入专栏写作,她的政治感就比较上升,更正面性一点。
廖斯婧:我记得她在《外面的世界》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专栏作家,是为了走出写书的状态,她还讲述了第三个原因:想要揭露某群人或某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那么她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她是一个会为自己的写作附加道德感或义务感的人吗?
黄荭:她写作的源泉是她母亲,以及那块每年被太平洋的海水侵袭的租赁地。她在殖民地的生活,以及她母亲的故事,是她所能够认识到的最大的人生不公正,所以她认为总有一天要为此复仇,复仇的方式就是写作。这是她写在骨子里的生命底色,走向这样的写作,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
翻译杜拉斯,最快乐的是她的句子短
廖斯婧:杜拉斯的写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时评作品,她对于那些被忽视被遗忘被边缘化的群体总是很关注。她曾经说过,千万年以来默不出声的是女人,所以文学是属于女人的。我的问题是她写作的群体恰恰包括女人还是她自始至终有要将女性作为写作对象的意识?
黄荭:我觉得女性意识肯定是有的,而且杜拉斯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作家,她写女人,最终是为了写她自己。她自己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女性经历的典型标本。
廖斯婧:黄荭老师,您作为杜拉斯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觉得难点在哪里?过瘾的地方在哪里?
黄荭:作为中国译者其实是有优势的,因为杜拉斯深受印度支那文化的浸染,她的语言中有东方的音乐性,句子又特别简洁,我们东方的语言都有这样的特性。国内翻译过杜拉斯作品的译者很多,没有一个译者抱怨说杜拉斯太难译了,我们都是抱怨普鲁斯太难了。
最享受的是真正感觉到自己的译笔跟原作合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翻译任何作家对译者最好的奖赏。
毛尖:虽然我自己的法语全部还给我的法语老师了,但是我当年翻译杜拉斯,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也是她的短,我觉得这也成为杜拉斯进入中国的便利地方。杜拉斯的法文不是最主流的,她又是个语法的破坏者,就像她要破坏优质电影一样。她的破坏使她的法文显得简单,像我们这种初学法语的人也能翻译,这是让我们最畅快的。
不同时期的译本,新的解读角度
廖斯婧:今天杜拉斯在中国依然受到关注吗?如果她依然受关注,这一代读者跟八九十年代那一代读者的热爱是一样的吗?
黄荭:普通读者群肯定就是《情人》了,而且可能都不是文本《情人》,而是电影《情人》。
毛尖:《情人》这个标签她已经撕不掉了。
黄荭: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杜拉斯引进中国一直到现在,她一直都有新鲜感,不同时期译界带来的文本,还有新的解读角度,都越来越丰盈。围绕着她的110周年诞辰也出版、再版了很多她的书,包括她的作品很多被改编成戏剧、电影,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的阅读方式越来越丰富了,不仅仅是通过文本,这都拼凑起了杜拉斯的另一副面容。
廖斯婧:最后一个问题,在漫长地走近杜拉斯的过程中,你们对她的感受发生过变化吗?
黄荭:我最初接触到的是知识分子杜拉斯,所以我再看那么青春期的文本的时候,感觉已经打了疫苗。而且我很快开始研究她,研究者的角度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更冷静地去看待她所有的写作,看到文本底下的暗流涌动,所以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她的文字所蛊惑。
毛尖:肯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看了她的电影以后有点减分。但我觉得杜拉斯就是为这个世界的恋爱或失恋人口准备的,这个世界的恋爱、失恋人口有多少,杜拉斯的读者就会有多少。
当我自己走出最痛苦的青春期后,我和杜拉斯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一点。青年时代读杜拉斯好像会成为里面的主人公,因为杜拉斯不管是用第一人称写还是用第二人称写,她都很容易把你变成她的主人公,这一方面是她的能力,一方面也是青春期无可避免地被她吸引的地方。
我现在早已经比杜拉斯小说中的人物年纪大了,所以我能抵挡她了。另外,杜拉斯自己也在变化,她小说中最开始的男主人公苍白懦弱,但到《中国北方的情人》,男主人公已经霸总一样了,更高更帅,最主要还更上进。我们不变化怎么对得起她呢?供图/法国驻华大使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