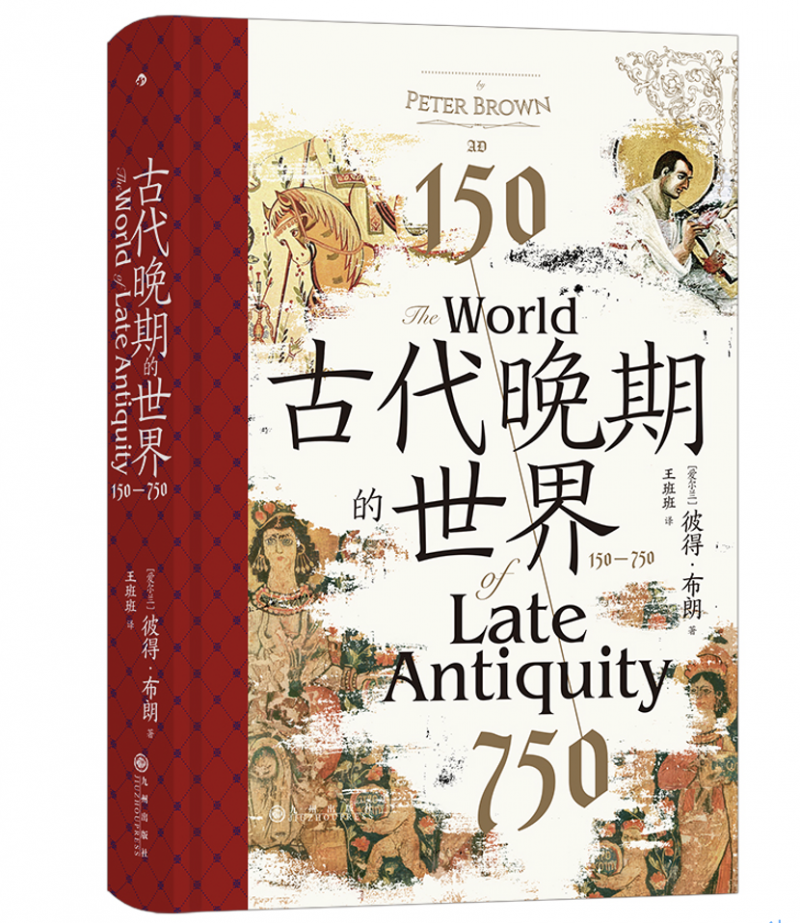268 年,一支来自多瑙河对岸的赫鲁利人战团洗劫了雅典。他们被史学家德克希波斯(Dexippus,活跃于253— 276 年)领导的阿提卡人自己打败了。这座被破坏的城市劫后余生。著名的市政广场废弃了;临时搭建的墙垣环绕着卫城。但德克希波斯并未在自己的公共碑铭上提及这场事变,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按时举办了泛雅典娜节(Pan-Athenian Games)。到了4 世纪中叶,雅典又一次成了繁荣的学术都市。当年轻的罗马王子尤利安以学生的身份造访这里时,他发现哲学已经像尼罗河的周期性洪水一样,在希腊各地重新兴起了。尤利安到来的一个半世纪后,基督徒们劫走了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哲学家普罗克洛(Proclus,411—485 年)梦到,雅典娜女神站在他身旁,询问“他的女神雅典娜能否在他的住所避难”。
雅典的历史表现了古代晚期文明的重要一面。在此时期,传统力量顽强的幸存与重组,以及对过去的重新发现,与我们之前描述的急剧转变同等重要。古代晚期复兴的东西所给予未来世代的,和这段时间的创新是一样多的。
希腊世界的知识阶层在3 世纪过着备受庇护的生活。哪怕在帝国国运最窘迫的3 世纪60 年代,哲学家普罗提诺还能在罗马元老们的恩庇下,不受打扰地安居在坎帕尼亚的一处庄园中,学生们依旧从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络绎不绝地前来。之后在4 世纪和5 世纪,异教哲学家和修辞学者们则在仍沐浴着希腊记忆的爱琴海边的城市之中蓬勃发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长传统,变化缓慢,仅经历过重组,且与过去并无断裂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比土地贵族还要稳定。
这些人自称“希腊人”,并称自己的信仰为“希腊主义”。他们修复了正统希腊智慧的受到威胁的堡垒。3 世纪末,他们已坚决地遏制住了精神上的蛮族大侵袭—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信徒对柏拉图主义的黑暗仿冒曾经吸引了先前一代知识分子;但3 世纪晚期的人们完全没有变得更为悲观、更倾向于拒斥物质世界,反而摆脱了这种暗黑情绪,并从未回头。诺斯替主义在学术圈中的失败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证明了古代晚期的贵族文化有能力打破一场在一个世纪前似乎会引发大规模“文士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 的运动。
6 世纪末,一大群“希腊人”依然坚定抵制着“蛮族的神智论”(barbarian theosophy)—基督教。在希腊世界,“希腊人”一词等同于“异教徒”,这对这些人的威望来说是一种赞颂。因此,在东部罗马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在希腊世界,君士坦丁彻底将国家机器基督教化了,4 世纪的帝国东部远比西部更称得上是一个“基督教帝国”,但异教在东部的文化生活中却比在西部存续得更久:广受尊重的“希腊人”仍在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数不胜数的小学术中心维持着学术生活,直到阿拉伯征服。在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东部的乌尔法[Urfa])郊外的哈兰城(Harran),异教的乡村士绅一直未受干扰地存续到了10 世纪。他们自己造就了希腊思想最后时代的沉思与不甘。在这片惊人的“希腊主义”绿洲,他们崇拜着一套名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三位一体神圣心灵;他们相信,君士坦丁值得鄙视,他狡猾地将基督教转变成了罗马多神教的仿品;他们也相信,基督教的兴起意味着希腊科学的终结。
这些“希腊人”令我们印象深刻,因为他们虽然面对着他们时代的精神乱局,却转向古代找寻解决当下焦虑的方式。他们安静地崇信着一个源自柏拉图并不断演进着的传统,这或许是古代晚期文明最令人宽慰的方面。毕竟,许多古典而开明的社会都因自己传统主义的重压而崩溃,给其直接继承者徒留噩梦与不安的记忆。罗马帝国得免于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希腊人”的复苏,以及他们与新的基督教上层知识阶层之间的对话。
虽然普罗提诺作为思想家是卓尔不群的,他的发展在这些人中却是典型。这位埃及人于205 年左右出生在一座行省小城,对诺斯替主义的接触远不是浅尝辄止。他曾与基督徒奥利金师从同一人。他也曾试图弄清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异域哲学。直到晚年,他才日渐平静地埋首于柏拉图的古老辩证之中。他的作品有着一位饱受困扰而坚定的人的吁求,他在中年时以严格、理性的约束,赢得了通往美好和明晰的道路。他的学生仍会问他那些前一代人问出的绝望问题:为什么灵魂被与这具身体结合起来?但普罗提诺不会给出现成的答案:他会坚持以“希腊式方法”——柏拉图作品支持的持续数日的辩证询问的方式—来推敲这个问题。
他的追随者们同样地掌控着他们时代的宗教边界。推罗的波菲利(Porphyry of Tyre,约232—约303 年)写出了一部极为渊博且具毁灭性的对基督教经卷的批判:他的批判点直到19 世纪“高等批判”出现前都无人超越。波菲利年轻的同僚,阿帕梅亚的扬布里霍斯(Iamblichus of Apamea,卒于约330 年)教育了整整一代希腊青年。如同很多当时和现在的教授一样,他欣然把自己表现为一位秘教的引导者(mystagogue);他有着受欢迎的教师应对反宗教者的粗暴指责时一样令人发怒的口才。但在君士坦丁在自己身边聚起一群基督徒廷臣的时代,扬布里霍斯还能够让一整代希腊士绅安心认为,他们的传统信仰能和最高级的柏拉图主义完美兼容。他对君士坦丁做出了报复。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代表,他天资聪慧的侄子尤利安,就受扬布里霍斯弟子影响,从基督教又归信了“希腊主义”。从361 年到363 年,“叛教者”尤利安做了皇帝(见本书第98— 101 页)。而即使是在帝国的公共信仰之战以基督教胜利而告终的一个半世纪以后,哲学家普罗克洛还会以雷雨后的静夜般的语气,仿写献给诸神的颂歌和完全异教式的《神学要题》(Elements of Theology) 。
“希腊人”在中世纪早期创造了哲学的经典语言,而直到12世纪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思想都不过是它衍生的通俗版而已。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重新发现柏拉图时,吸引他们热情的并不是现代古典学家心中的柏拉图,而是古代晚期宗教思想家那里活着的柏拉图。
简单来说,他们相信,在柏拉图和希腊诸多学府的知识学科中,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够控制冲突、维持绷紧的线的两端的方法,而围绕这两端的更为激进的思想家与更具革命性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却会容许这条线崩断。他们强调的是,通过理性沉思,有可能把握住可见世界的各个层级之间,以及与其来源独一神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也有可能通过思考“触及”那凝聚的中心,而之前人们是借助所有可见事物呈现的美而得以感受到它的。用一个简单的图像表述,他们把世界以及世界与神的关系,看作一个在绳子上迅速弹上弹下的悠悠球。对他们来说,诺斯替信徒切断了这根绳子:因为诺斯替派说,宇宙与善神之间、人的内在与外在之间、身体与灵魂之间没有连接。反之,基督徒则不许悠悠球转长:他们把注意力钉在独一神身上;基督徒们粗糙的一神论的怒目,排除了不可见与可见的诸神的彩虹般绚丽的表达,而太一的美恰恰必须要通过这些表达,才能通向凡人之眼。
要维系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之间的联系、不可表达的内在世界与其在外在世界中有意义的表达之间的联系,要坚持自然事物有可能由灵魂赋予意义—这就是普罗提诺交给其同时代人和后辈们的任务。主宰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无论是西方的圣奥古斯丁,还是在东方于约公元500 年写作《天国位阶论》(Celestial Hierarchies)的不知名作者(后世称其为“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都同样得益于普罗提诺热切维持的平衡。
对柏拉图主义者来说,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是神与宇宙关系这一难题的缩影。普罗提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典型。他下出定论:拥有身体的“罪”,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比投出阴影更多。实际上,身体是一件美丽的工具,灵魂透过它来寻求表达:人们必须珍惜并锻炼自己的身体,一如音乐家必须让自己的琴保持音调准确。这是一个紧张而敏感的理想,但绝非禁欲苦修的。在听从他的那代人赞助的艺术中,我们能看到普罗提诺的真意。这种艺术并非“彼世的”,而是观照“内在世界”的。帝国晚期的肖像画远非放弃身体的长处和个性,而是把它集中在了能让人从这具身体直达其心灵的入口处。它们的强调落在眼睛上。眼睛朝着我们闪耀着,展露出一种隐藏于肉身紧张气氛中的内在生活。古代晚期是扣人心弦的肖像画的年代。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一位古代晚期人创造了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自画像”之一:在圣奥古斯丁于397 年写成的自传性的《忏悔录》中,这位普罗提诺最优秀的拉丁读者将大师非人格的知识热忱,炼化成了欧洲文学第一部真正的“自画像”。
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代表了古代晚期柏拉图主义复兴的一支:这一支与现代人最为贴近。但对当时以及直到17 世纪的人们来说,柏拉图主义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对人类在整个宇宙中位置的态度。在“希腊人”的作品中,人类重新掌握了曾失去的与周边世界的亲近感。
诺斯替的黑暗展望、基督教的一神论以及晚些时候的基督教苦修主义,都威胁着将人孤独地留在一个意义已被排空的世界。对古代晚期的哲学家来说,世界已经不可否认地变得神秘。他们带着悲伤的思考注视着世界的美,如同夕阳沉落后最后的那一抹微茫余晖。但这个宇宙虽然神秘却是有意义的:它是来自神的象征。哲学家们将继承来的神话当作象征来接受(这非常像现代的核物理学家,他们并非自行创造,而是继承了过去那些朴素的、二维的中子质子轨道示意图,来为大众总结关于物理世界那令人眩晕的事实)。与基督徒们在冰冷的巴西利卡圣殿中“属灵崇拜”的空洞相对,异教哲学家们坚守着传统祭献的“由灵魂掌控的姿态”,一如燃烧着的祭坛将其祭品化为了上扬之火的简单明晰。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用来表述独一神与可见世界无穷无尽的表达之间关系之紧密的术语,得到了一再重复,这表达了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宇宙中对亲密感的渴求:哲学家们强调存在之间的“链条”“交织”和“交融”,将人与其可敬畏的根源联系起来。所有生物都回应着这个不可见的中心,如同莲花静静地向着升起的太阳开放。
在4 世纪,这种观念被看作罗马帝国所有文明的思考者们的桂冠成就和唯一希望。基督徒们也分享着这些观念,因为他们也自认是文明人。在知识生活断断续续,且缺少以异教为主体的学术环境这一坚固壁垒的西部,基督教知识分子成了几乎无人挑战的普罗提诺继承人:4 世纪中叶的马里乌斯·维克托里努斯(Marius Victorinus),以及安布罗修、奥古斯丁和后来的波爱修(Boethius,约480—524 年)都是希腊哲学与拉丁中世纪之间的桥头堡。即便在东部,异教徒教授们也发现自己对基督徒就像对异教徒自己一样慷慨授学:410—414 年任托勒密城(Ptolemais)主教的叙内修(Synesius)就经历了一场典型的从哲学家教室到主教席的平静演进。叙内修仍可维持与一位异教徒女士——亚历山大里亚的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见本书第114 页)的友谊。他在410 年出任主教,而条件是,他虽在教堂“述说神秘”却应能在私下自由地“如哲学家般思考”。
基督徒从其异教先师那里接管过来的,正是复兴的柏拉图主义中的这一要素,它把人从面对可见世界时的孤寂与无意义中解救了出来。2、3 世纪基督教护教士呼吁对一位不完全清楚的神的简单崇拜,这带来的刺目之光曾让世界濒临苍白,而此时世界又重新弥漫着色彩。奥古斯丁是通过阅读普罗提诺的《论美》(On Beauty)从摩尼教中得救的,这是一种诺斯替教义,普罗提诺也是从与之相似的教义出发开始了自己知识的奥德赛之旅。希腊神学家们发现,自己正在对神与可见世界关系的柏拉图式思考背景下,讨论着基督在向人展现时的作用与本质。人与神藉由可见象征物的“交织”,曾极大吸引了扬布里霍斯,而这也同样是比他年轻的同辈人圣阿塔纳修(St. Athanasius)在写作基督道成肉身时的基本关切。异教神祇的物质图像曾将神圣的美可视化并使其如此神秘而有力,而这种神圣的美的回音,也将同样的力量传递给了基督教的圣象。覆盖着拜占庭教堂墙面的画作:道成肉身的基督生平画面下方的、与视线高度齐平的人类圣徒;高大的天使将可见世界的主宰者基督—他那遥远的面容融入了最高处拱顶的金色—与横跨墙面一路向下进入人群的图像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组飞升的形象,正是由艺术可视化了的不可见世界那令人敬畏的感觉,激荡在裹缠于身体的帘幕中的灵魂里,发出的直接回响,而在皇帝尤利安站在他的诸神的祭坛前时,这种回响也曾使他激动不已。
安慰着最后的异教徒们的,是不可见之物的亲切与无形的存在感。像4 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乌合之众那样(见本书第114 页),宣称基督徒们通过毁灭神庙而“摧毁”了诸神的说法,对异教徒来说,就像是以销毁所有插头和开关的方式消除了电力一样愚蠢。诸神美丽的古典雕塑已被毁坏:但如尤利安所说,雅典人多年前就已经毁坏了苏格拉底的身体——“活着的塑像”——但他的灵魂永存 a。诸神也是如此。在夜晚的群星中,诸神找到了比终将朽坏的人造雕塑更适合他们漠然的永恒的形状。因为在群星中,地球上衍射的色彩都聚集成了恒定而静谧的辉光。恒星与行星安稳地摆过最后的异教徒头顶,成为远离僧侣大破坏的闪耀着的诸神雕像。纵贯中世纪,群星仍然高悬于基督教欧洲之上,令人不安地提醒着人们诸神的不朽。诸神在星期的每一日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的标志仍留在行星上;而这些行星则控制着文明人的行为直至17 世纪末。1300 年之后,人们仍然会以或多或少基督教式的形式,重拾那种亲近一个完美与不可侵犯的世界的震撼,而年轻的尤利安正是因此才背离了基督教。
坐下来,杰西卡。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
——《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场,58—65 行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