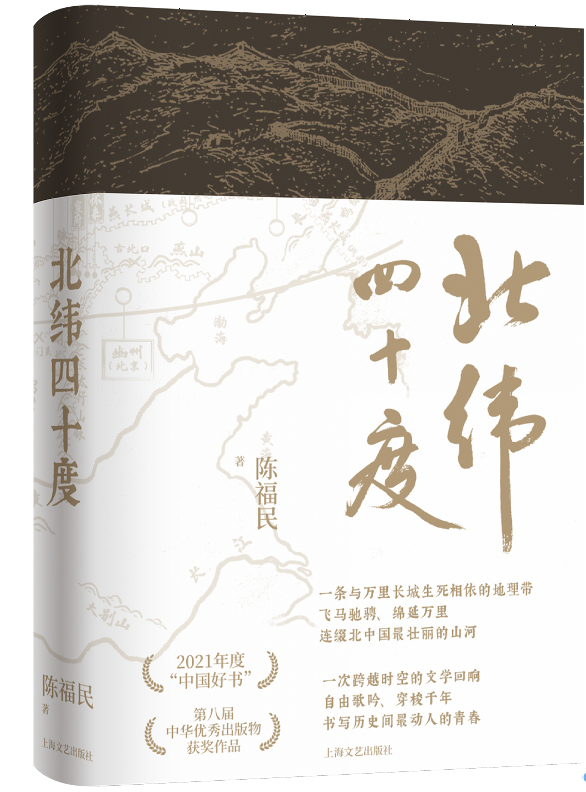一
一年多前,母亲与“死神”相约—她罹患了癌症,经受了恶性肿瘤患者都要经历的过程。己亥年正月初三那天,她“如约”走了,享年八十五岁。跟很多病人一样的结局,这没有什么不平常。
同时,像所有的癌症病人一样,她其实一点都不想承受那些毫无意义的痛苦,却又不得不一个一个承受完毕,一点都没少。在她还没有患病的往日,我们一起闲聊,不止一次触及过安乐死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我看到的一个案例:湖北武汉一个中年男子帮助久在病榻生不如死的母亲结束生命,随后自首,坦然去接受法律惩处。这个案例,我并不确认是真实事件还是虚构的“鸡汤”类文字,也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只记得当时母亲一再为那个被判刑的儿子打抱不平,抨击法律不公正,表示非常赞成这位儿子的做法。而在她病重后期医生和我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早点结束。
由于没有治疗手段,她不愿意住院,我们把她接回家,勉力做尽可能的护理与陪伴,并费尽周折给她找到了最新的美国抗癌药PD-1。在肿瘤复发疼痛度加重难以忍受的日子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听着她虚弱而揪心的呻吟又无能为力中捱过的,这种日子,可能算是世间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吧。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她用了很大的声音与父亲争吵,情绪激烈且有些夸张地指责父亲“自私”,“什么也不敢承担”,等等。我赶紧冲进“病房”去调停,只见父亲站在床边手足无措,虽然慌张但是立场坚定地摇着头,嘴里喃喃说“这怎么能行”……原来她在向我父亲讨要艾司唑仑片—一种常见的安眠药。她的意思,是要攒起足够致死的药量自己去结束。看到我进来,母亲转向我,表情悲愤交加。我咬紧牙关安慰父亲说给吧,我做决定了,我来承担一切责任。这个“决定”究竟是合乎她的心意,还是让她感受到人生真相的冷酷而更加绝望,我来不及细想。总之这暂时让她稍微平静了下来。为了减弱这个场面的尴尬与压迫感,我故作轻松对母亲开着玩笑:老太太你这是不把我送进去不算完啊。
事实上,母亲并没有机会吃那些药。因为虚弱和痛苦,她被折磨得连吃正常的药物都很困难,遑论吞服几十片安眠药。尴尬要命的肿瘤部位导致她无法坐起,也不能以正常姿势平躺,只能侧卧着,间或用残存的余力勉强调整一下位置,以便让自己舒服一点。而她每一次的挪移,无论是自主,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都是痛苦万状。在她病重后期,她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饮食极少,形销骨立,卧床挣扎,每一次大小便的艰难程度都不啻于一场酷刑,我们每天都要多次帮她清理擦拭。这不仅是要尽可能避免褥疮,更因为她生性清洁成癖,一点点感受上的肮脏与凌乱都不能忍受。这让她的痛苦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现在母亲走了,她承受了她生前所恐惧所厌恶的所有痛苦与屈辱,没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观去实施理想的计划,这对她是个非常大的遗憾么?她究竟是后来已无力完成,还是因为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怀着留恋而下不去手?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讨论了。但我知道,痛苦与恐惧,决绝与不舍,纠结与悔悟等等,一定在病痛之外给她施加了超额的折磨与惩罚。这似乎是一个警告:面对命运中的痛苦与折磨,没有什么人能够攫取到豁免权。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愿望和努力与实际结果成反比。
她在清晨的安睡中没能醒过来,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并不因此遗憾。在她生病前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拥有的共同岁月中,我们已经把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生问题,包括无可弥补的遗憾与感悟,都重复总结无数遍了。但我们都隐约明白,至少是心存疑虑:如果人生重新来过,那些后来被总结认识到的各种遗憾或者“错误”,真的有机会得到纠正与避免么?那些被认为是“宝贵经验”或“深刻教训”的东西,真的能派上用场么?似乎并不乐观。命运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赋予你应有的性格气质,然后让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你一只脚轻松快意,另一只踏进深渊却不自知。我们帮她清洗、整理,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我们都平静地忙着,没有人号啕大哭,甚至连过度的啜泣也没有。我一边擦拭母亲尚有余温的遗体,一边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妈妈啊,你放心踏实走吧,也该走了,咱们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熬了。这时,我眼泪默默流下来。
我这个告别语并不合乎母亲的真实想法。她热爱生活,非常想活下来。这种自然而然的抒情倾诉,在当时有不得不然的情境。人总是脆弱的,情不自禁就要暴露肤浅,而暴露肤浅通常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但我也不必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允许我暴露一次吧。只是,这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煎熬,我其实并没有权利代替母亲下断语。以此类推,任何人都没权代他人决定人生的意义,即便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
人生艰难,凡事尽量不要那么轻率下断语。
二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母亲的一生却过得有些不平静。她喜欢看书,喜欢UFO和外星人的话题,还特别称赞刘震云的小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震云讲起这件事,震云拿出《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在扉页上恭敬题写“请某某阿姨指正”送给母亲,这让母亲非常开心。母亲总是喜欢思考那些纠缠不清的大问题,反思她一生的得失—当然,经她反思出来的人生不说一无是处吧,基本上都是失败。她长期失眠,往往到后半夜还在看书或者冥想。我曾经跟她开玩笑说,您老人家本来是个朴素的劳动人民,却过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她平时的情绪通常都是严肃甚至压抑的,这一次难得大笑起来,然后沉默。
母亲1934年生于民国时期的热河省承德市(现今河北省承德市)。按照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热河省在黑吉辽东三省外,一向被认为是“东四省”,城市规模小到可怜的承德市,是热河省的省会。日本人继攻占东三省之后,于1933年3月向热河挺进,民国部队未战先溃,华北战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热河前敌总指挥汤玉麟(即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中的“汤二虎”),在搜刮掠取大量民脂民膏后望风而逃,热河全境就此沦陷。据母亲讲,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日据”时期的承德市做一个银号的小职员,支撑着六口之家。在她五岁时外祖父死掉了,外祖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自己的娘家讨生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中,尽管一直都有“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的批判性说法,但在血缘宗法制支撑下的“投亲靠友”观念,大抵还是国人遭难落魄时非常重要也比较行之有效的生存原则。在当今时代里,这种传统信任即便还未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至少也是日渐稀缺了。
母亲经常对我回忆起1940年深冬,外祖母带领她们回娘家以及到了那边艰难生活的经历。向北走出承德市不到十公里的关卡,日军拦截了孤儿寡母一行人,她们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的间谍,于是关进了普宁寺—承德人俗称的“大佛寺”中。她记得她那时发着高烧,躺在佛堂冰冷的地面上等死,但也许是有佛祖保佑的缘故吧,三四天之后她竟然奇迹般地退烧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上路。从承德市到赤峰市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承赤高速中间著名的茅荆坝开通了一条长达6.8公里的隧道,现在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在茅荆坝隧道开通之前,所有北行的汽车经过茅荆坝都要走盘山公路,海拔升高到1500米,气温骤然下降。每到冬季下雪后,茅荆坝都被往来承赤两地的司机视为畏途,我小时候就不断听到有冬季行车熄火的司机被冻死在坝上,或者司机不得不点燃满车货物取暖最终逃出生天的传闻。
1940年代,两地还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以她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自己雇车,于是娘几个两条腿步行。这条路,当年她们走了将近二十天。从承德到赤峰的沿途,大部分路段都人烟稀少。据母亲说,如果不是茅荆坝上一户贫困人家收留和周济了她们,她根本没有机会走到赤峰,很可能就冻死在茅荆坝或者沿途上了。最终,她们在赤峰的亲戚那里得到了帮助,熬到了共和国新政权的建立。后来,我多次听她回忆她得到的每一次帮助,大抵都来自贫困穷苦的人家。
童年的这些经历,显然对母亲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是过早地体会到了失去父亲庇护之后的世态炎凉,也许是兵荒马乱土匪丛生的年代在她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心理阴影,总之她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不安全感、轻度洁癖、忽忽不乐伴随了她的一生。她嫉恶如仇,憎恶权贵的趾高气扬与为富不仁,相信贫穷与美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源自个人经验的认知非常朴素也非常简单化,很多时候,她对公平正义、正直善良与“坚持真理”等等道德品质的信奉与强调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这些粗放的原则性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听起来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必然正确,也无法容纳那些复杂多元的有厚度的人性元素。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她眼中的“不公正”,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与环境相安无事。这一点,很可能使她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喜欢争执的人,也让她的一生吃了太多的苦头。她的亲哥哥大她将近十岁,不知为了什么事,母亲认定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在外祖母和几个妹妹最困难的时候“不顾家”“不负责任”,误解和怨恨使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与哥哥的关系相当冷淡 ,并发出过“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口”的怨言。这个心结直至晚年才释怀。而事实上,我舅舅本分厚道勤勉持家,辛苦了一辈子,无论经济状况还是工作环境,都远不如她。
随着“辽沈战役”结束,热河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3月,她在赤峰市参加了新政权的初建工作,这时她不满十五岁。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工资制,没有薪水可拿,但供给制首先保证了她能吃饱,日常也偶有其他食物带回家,外祖母和家里后来比较多地依赖母亲这份工作。那是母亲记忆中最充实也最幸福的日子,她被包围在一个特别有爱的集体中,受到了很多照顾。队伍中那些年长的大哥大姐都是穷苦出身,知道母亲家境贫困,大家都乐于帮助她,而最根本的帮助手段,无非就是节省下自己的食品物资送给母亲带回家去。用母亲的话说,“那绝对是真诚无私的”。她识字学文化并热爱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建立在资源短缺基础上经济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与人彼此友善相助的“真诚”,对她世界观的形成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她弄不懂太远大的社会理想,估计也不太明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从童年开始到现在的生活经验,似乎让她确信贫困与真诚、美德之间有神秘的联系。她因此热爱新政权和这个政权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或许就是属于母亲的朴素的“人民性”认知。
她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进入了共和国,可谓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大概今天很多人会嘲笑这份精神元素,或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或曰“左派幼稚病”。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但是在母亲那里,穷人与美德的直观经验是她进入新社会的钥匙。她并不知道,仅靠“真诚”“单纯”这类词汇是难以识别和驾驭事物的真实性复杂性的,她也不知道穷人不再那么贫穷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