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路内的长篇小说新作《山水》,聚焦路家几代人的浮沉往事。写作者在完成家族叙事的同时,基于司机、汽车的故事设定,同时也塑造出一种更新的公路叙事。
人活着大部分时间都是走一条已知的路
以往将公路作为重要叙事场景的国内外文艺作品,譬如《末路狂花》《得州巴黎》《落叶归根》等,公路叙事里所谓的“公路”不管是否有始有终,总归是一条线性的道路。在这条线性道路上的叙事往往都开始于人物角色面对日常行为的“放逐”,因而无论是要反映时代症候还是要剖析个体内心世界,大多数的公路叙事强调的是对规范、习惯、俗常的反对、抵抗甚至于破坏,它的文学力量有赖于对日常约束的解构。
《山水》当中,路家的家族史无疑是和汽车、公路紧紧相连的,但是正如小说中主人公路承宗自己讲过的那样:“人活着大部分时间都是走一条已知的路,反反复复走,人很少有机会选路,一旦选定,较好的情况是继续反反复复走,较差的结果是掉进沟里,腿断胳膊折。人所谓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听天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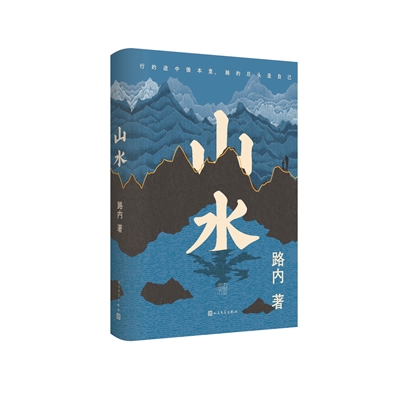
路内在小说中并不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公路叙事那样构建起线性的道路,而是让故事情节反复地在已知的道路上生长着。小说30万字全篇里所包括的地理坐标并不多,路承宗和他身边人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从吴里到上海这一片苏南天地当中,从苏联的嘎斯车、德国的亨舍尔到美国的道奇和雪佛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装公交车,不同汽车的轮辙都沿着重复的道路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之间往返着。从青浦到吴里,最远不过是随军运输去过的嘉兴、绍兴,路承宗40年驾驶生涯的轨迹全然被囊括其中。
《山水》的一处重要文学特质正在于作者路内有意识地限制着叙事场景的流动,这是小说与其他公路文学很不一样的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承宗和黄启宣在战时被征调为运输司机后的一次夜间长谈。黄启宣说:“那个镇像不像袁塘镇。”“这里的镇都差不多的。”路承宗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曾经的纨绔子弟此时心中不再充满遨游天地的放浪,而是迫切的思乡愁绪。等到回顾司机生涯时,路承宗又说:“开了十几年车,离家最远也就五百里地,其实日本也近,都谈不上远。”随车的少尉也认同路承宗的话,讲道:“这里,就是我到得最远的地方。”“越往前开越远。”行文至此,路内借路承宗之口对他一生的过往作以收束与回望,也通过路承宗、黄启宣、许先生等人物思考着作为现代化载具的汽车与世代栖居的乡土之间的平衡关系。《山水》的叙事也正因为这样,没有落入传统公路叙事线性延展的窠臼,路内的笔触更强调一种有限的回环,并且从地理的有限中力图开掘出每个人物精神世界面对时代变化的不同反应。
有限的场景流动,是《山水》叙事结构上有别于以往公路叙事的地方,是外部的“不放逐”。作品同样有着内部的“不放逐”,小说从始至终都在规避着同类型作品当中要求呈现给读者一个或者多个“自我放逐”的人物形象,路内笔下人物面对时代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对朴素的处世道德的执念
如前文所讲的,《山水》在空间层面是回环往复,而时间层面上,作者依然选择了线性延展。从路承宗意外地因为父亲路红祥的死而得到了黄启宣的那部汽车开始,他之后的人生乃至于整个路氏家族的家族史都与汽车、公路产生了高度的关联,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汽车与公路、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变革和路家三代人的命运三者构建起了一个富有文学阐释力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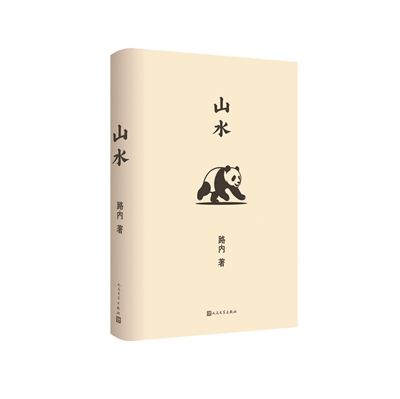
作为小说叙事主人公的路承宗,自他1936年踏上前往上海学车的那一刻开始,伴随着他驾驶技术的日益精进,他开始不断被裹挟进历史事件的洪流当中,同时也与周爱玲、黄启宣、许先生、柳队长、汪有光、逢阿大以及家中的养子养女们生发出各不相同的感情关系。可尽管路承宗是《山水》里所有关系的中心点、所有变化的见证者,但他在这40余年的时光里始终抱有两种执念生活着,一种是对驾驶本身的执念,另一种则是对朴素的处世道德的执念。
初到上海的路承宗跟着关师傅学开车,学成后,从机器厂学徒到给百货公司、电影公司老板当司机,从为抗日军队运伤员再到为福山大班效力,最后他成了人民军队的运输员,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洗礼,默默地回到了吴里跑起公交车的营生。有了坐标式的历史事件,路内笔下以路承宗的视点所展开的公路叙事自然而然地远离了“小我”的“自我放逐”,他写出的是路承宗是如何从袁塘镇的穷小子蜕变成为吴里人人皆知的司机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成长”——因为路承宗对于驾驶本身满怀执念,所以在大时代风云动荡的背景下,他始终想的是如何继续自己与汽车为伴、与公路为伴的营生。于是有的时候,路承宗的思想行动与外部的政治话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让《山水》的叙事风格变得有些新奇,甚至于在探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时具有喜剧的语调。
“看山水”背后的生活辩证法
而路承宗心中对道德的执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山水》写作主旨体现的一个侧面,吴里话里“看山水”所蕴藏的辩证法也从中才得以体现出来。在上海遭遇战事波及时,他顶住死亡的威胁也要将师傅的丧事办停当;他答应了杜参谋,所以哪怕自己无法平安回到吴里,也要和杜参谋跑一趟镇江;服务福山大班时,他觉得福山一家待自己不薄,小心呵护着大班与驹子小姐两人的秘密;而当遇到“我们的人”柳队长、许先生之后,路承宗则甘愿回报他们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几度走上战事前线……更为重要的,是路承宗在和周爱玲结为夫妻后,他放弃了像黄启宣家那样传统的宗族观念,他决定收养路志民、路国强、路国权、路国庆和路文贤这五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以至于吴里人一看到弃婴,就不自觉地想到路承宗一家。路承宗的种种行为既非趋利避害,也不能完全说是有着革命自觉,作为一名与汽车公路为伴的司机,他只是依从着自己内心想要做个好人的朴素道德观行事,他要对得起世事纷乱里别人给予自己的那份恩情。路承宗在这一路上,身处的阵营、驾驶的车辆、拥有的称号一变再变,但是他内心中始终还是那个袁塘镇上淳朴的路小路,这是贯穿全书而不变的。
而与路承宗关系紧密的两个人物周爱玲和黄启宣,都是从尚且优渥的家境突然间掉落到需要竭力生存的处境当中,路承宗的活法便成为他们所参照的生活标尺,影响着他们,使他们不再是先前的小姐、少爷。此外,《山水》还关注到了“父一代”与“子一代”之间的观念差异——正是因为路承宗对自己的处世哲学有着强烈执念,让路国强和杨子红、路国庆和袁芙蓉的感情发展增添了一份嬉笑怒骂的现实生气。
书中路内对吴里人所谓的“看山水”进行了意义区分,一层是说“目光高远,胸怀大不一样”,另一层则是说“冷静隐忍,善于鉴貌辨色”。纵观路承宗奔波在公路上的一生,他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习得了“看山水”的本事,可他似乎并不自知,这恰恰是因为《山水》的公路叙事不再以人物的“自我放逐”作为中心。路内选择用30万余字的篇幅细致地写尽路承宗和他身边人在40年间经历的一切,使得一个司机的驾驶生涯被道德、主义、良知、民间规约、家国使命等种种新旧观念包围着。在这几重观念的相互作用当中,身为读者的我们方才能够读出每个人物形象确切的文学坐标,也才能够领悟到“看山水”背后的生活辩证法到底意味何在。
文/刘溁德
编辑/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