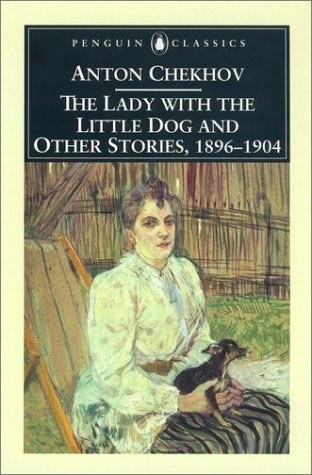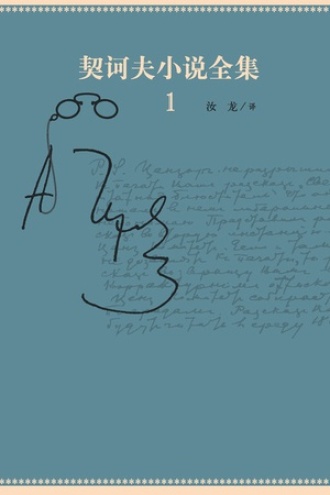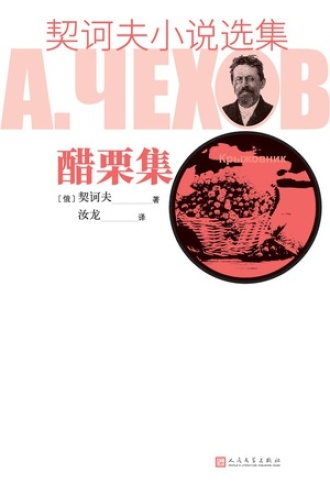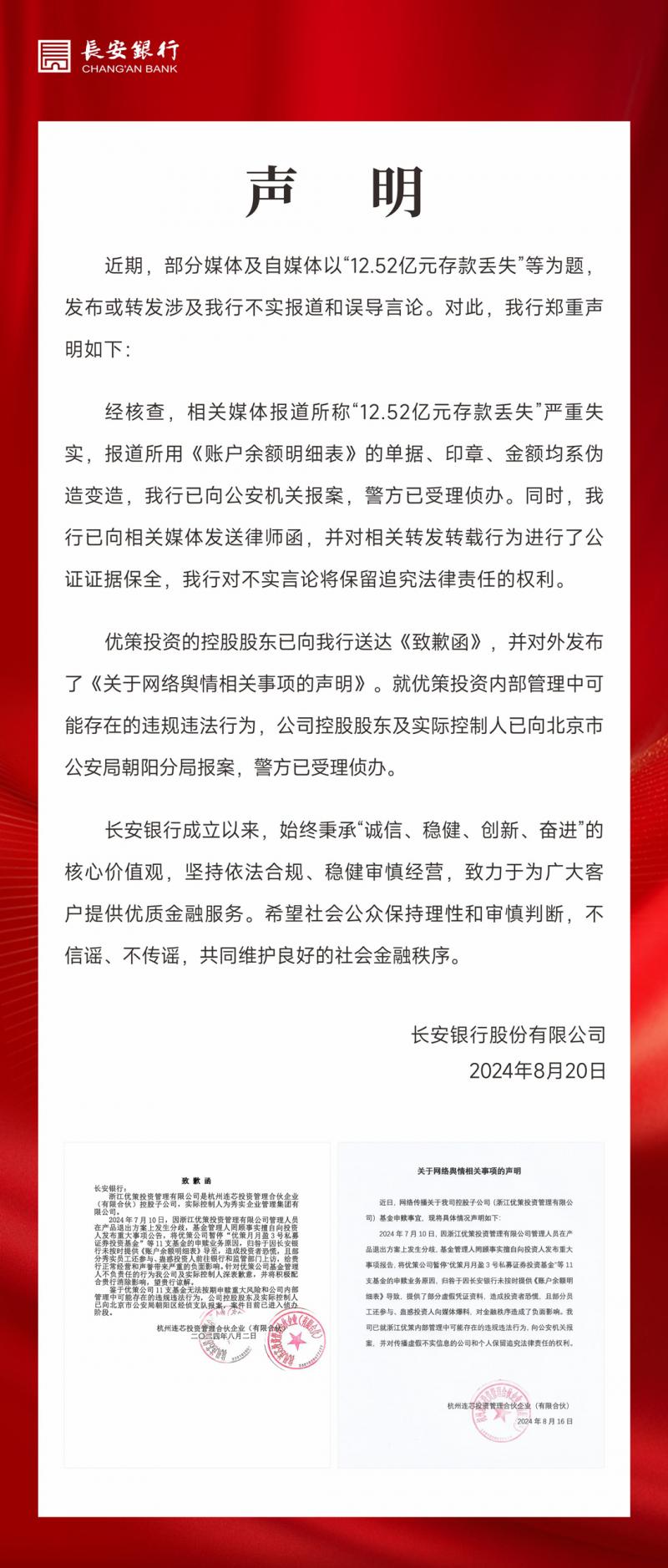在《洛希尔的提琴》的开头,契诃夫居住在亚科甫的脑海中,传神地描绘出他违背于常理的想法——“这些老头子却难得死掉,简直令人气恼”——即使他本人也是这些老头子的一员。作为一个靠制作棺材谋生的手艺人,死亡等同于他的生意,所以他热烈地期盼着死亡降临。然而他从未思考过自己死亡的可能性,他思考的仅仅只是他的生意,“到处都只有损失,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他的妻子离世的时候,齿轮开始转动,他才蓦然发现在52年的时光中从没关心过她分毫。自此,人物开始了思绪的漫游:思考自己锈迹斑斑的生活。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是损失,从死亡里得到的是好处”“人只能过一次生活,而这生活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就过去了?”而在他枯燥乏味的生活中,那把提琴是唯一的光亮。他最终把它交托给了洛希尔,那是他业已丧失的生活中一点可以延续的星火。
逝世120年后,契诃夫遗留给我们的“提琴”是那些直抵生活本质的不朽作品,尤为重要的就是他后期的那些臻于完美的短篇小说。在契诃夫的笔下,人生是一场硕大无朋的悲剧气泡,我们被这个透明的气泡囚禁而浑然不觉。只有在为时已晚之时我们才会想到去戳破这个气泡,然而一切都已追悔莫及。
契诃夫的悖论
契诃夫的小说是关于悖论的深不可测的渊薮。
首先是关于人物的悖论。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人物被划分为扁平和圆形,但契诃夫开辟了另一种观察人物的方式:从外部看,所有的人物都是扁平的,因为他们的人生连绵在一种本质上一成不变的、噩梦般的单调与暗淡上;从内部看,所有的人物都是圆形的,因为人的思绪是如此的复杂多变与无边无际,甚至于这种思绪涌出的原因都无法被探查。
契诃夫将生活进行划分:一种是公开的给人观看的生活,充满了传统的真实与传统的欺骗;另一种则是暗地里进行的生活,那是真诚的,然而却需要对外人弄虚作假遮盖真相的(在这里,真和假的界限也并非那么截然)。但扁平与圆形并非是全然割裂的,尤其悖论性的是,当人物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扁平人物时,他们就膨胀为了圆形人物,甚至于站立在圆心——即生活的本质。
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悖论。爱情可以毁灭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同样也可以塑造一个人生活的意义,但其结果不可知、原因不可解,没有人可以预知最终爱情会使人生漂流到何方。可以肯定的是,婚姻是恒久的错误。所有婚姻的内核都是腐坏,哪怕婚姻的对象是正确的值得爱的人。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在戴莫夫为科学献身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才意识到她本该拥有的幸福。契诃夫写下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令人动容却永远无法再倾诉的伤感想法:“她想对他说明过去的事都是错误,事情还不是完全无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因为那一潭死水的生活没有办法波动起涟漪,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寄希望于婚外情,哪怕明知道这种感情是无望乃至绝望的。人物深陷于这样的困境:他们的婚姻是不幸的,而他们逃离婚姻的结局同样是不幸的,即使他们真正寻觅到了爱情。
《带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少有的相对明亮的小说,古罗夫和安娜打破了道德的冰层,挣脱了各自并不合理的婚姻。“他们不懂为什么他已经娶了妻子,她也嫁了丈夫。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硬关在两只笼子里,分开生活似的”——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那婚外的爱情就是必然的。但小说的结尾依然是灰暗的色调:这份爱情到来得过于迟缓了,古罗夫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同时在余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里,这种私奔仅仅只是困难的开始,而不是圆满的结束。
人与人的疏离
在契诃夫小说中,关于人类生命最为永恒也最为深沉的残酷悖论是——当我们领悟到生命需要意义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无法再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时候,于是生命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浪费了。
契诃夫最好的小说的张力绝大部分构筑在关于生活的意义这一地基之上。当人物闪烁着关于“生活的意义”这一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变得空虚而饱满。他们空虚,因为过往的人生只是空壳,没有可以填充的意义;他们饱满,因为他们总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意识到这种空虚,他们用全部的身心去思索它、抵抗它,然而难以改变。我们对于生活,期待的是丰收,而获取的却只有荒芜。契诃夫赤裸而平淡地将这隐痛摊开展示,让他的小说密布了宿命论的乌云。这是无可逃离的人生必将无意义的极寒之地。
而对于所有人来说最为沉重的是,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永远无法宣之于口诉诸于人,即使我们满溢和他人交流的欲望并真的付诸行动,得到的也是永不理解的隔膜。不理解是永远存在的常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着无法跨越的天堑。
在《带小狗的女人》中,安娜在向古罗夫哭诉自己的思绪:“一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古罗夫觉得这话乏味,厌烦,无法理解。安娜离开之后,爱情后知后觉姗姗来迟。当古罗夫无法克制自己的想法而对一个文官倾诉“但愿您知道我在雅塔尔认识了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对方的回答是毫无关联的“那鲟鱼肉确实有点臭味”。从某个角度这个回答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隐喻,但古罗夫(同时也是契诃夫)在这种不理解中驶入了更为深刻的东西——“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头的谈话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时间,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头来只剩下一种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
在《古塞夫》中也同样有这样的对话,濒临死亡的巴威尔·伊凡内奇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一股脑地倾倒给古塞夫:“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古塞夫仅仅回答他:“这种活不难做。”甚至于人既不理解他人,也不理解自己,他们永远在生命即将凋谢的时候才会感叹:为什么自己最美好的生命就这么被浪费掉了。于是有了双重的疏离。
契诃夫关于不可理解性的最精彩的小说当属《主教》,疏离由社会地位的身份差异带来,即使亲如母子也显得陌生。只有当主教病入膏肓之时看到母亲细微的难以觉察的关切目光,原有的母子的“身份”才得以回归。而在主教去世后,响起的依然是洪亮欢畅的钟声,激荡着春天的空气,一切美丽与欢乐都不会因为他而改变。剩下的他母亲胆怯的话——讲到她有过一个当主教的儿子。她讲得胆怯,怕别人不相信,而确实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就是主教在这个世界上留存的唯一痕迹。
小说中的神秘
契诃夫的小说总是会染上一种神秘。这种神秘并非类似于奇幻小说般以非同凡响的想象力缝制的,而是关乎生活最本质的神秘——一种无法以所谓的理性逻辑判断的不可解释。
事件是神秘的。《带小狗的女人》中一个可能是看守的人走过来望了望就走开了,契诃夫形容“这件小事显得那么神秘,而且也挺美”。没有任何冗余的解释,只凭借这一句评论就让这个寥寥数笔的细节蒙上了神秘而优美的面纱——庸常的事似乎就逃逸出了庸常,从而升华成某种近乎于生活的本质的东西。就像告白时那两个在上方楼梯口吸烟的中学生,契诃夫让他们出现在那儿,在方位上造成某种压迫感,但并不参与故事的发展。这些事情仿佛脱离了故事,就这么倏然出现,又默然消散。
人物的所思也是神秘的。契诃夫小说中常用的一个短句就是“不知什么缘故”,如同在生活中我们会在某一刻突然做出自己都不知其缘由的事情或者念头,偏离了理性的轨道。在《姚尼奇》中,斯达尔采夫被他心爱的人哄骗到墓园。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气愤沮丧的时刻,但身处墓园之中他突然感受到了“宁静、美妙、永恒”“宽恕、忧伤、安宁”——在生活中总有那些神启般的瞬间轻轻地露出了门缝,得以让人窥见美的本质。在《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更是让人物自述不知什么缘故记得这一天,并清晰地记得所有琐碎的细节。思绪总会突然的漫漶,人们甚至走在街上就会体悟到某种真理的光辉或萌芽,并为之心醉神迷。
世界同样也是神秘的。契诃夫对于外部环境的描写分为两种:第一种他将人物的心绪辐射到环境上,环境与人物的心情交融,同时环境也可以激荡起人物与读者内心深处的感受;第二种则是环境独立于人物,无论内心的思绪如何澎湃变幻,环境永远优雅而美丽,这种美无法撼动。但人们的生活慢慢开始腐朽,与自然的永恒之美隔绝。
在《黑修士》中,自然的奥秘蕴藏着永恒的光辉。可是人呢,沐浴在这种光辉下,却只能发现生活的空虚。有时,这两者又难分彼此:在《文学教师》中,契诃夫用奇妙的因果关系形容“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因为浓香而变凉”。在《古塞夫》中,古塞夫死后,海洋甚至都有了死亡的气息,契诃夫用兼具形态和神韵的比喻描绘道:“像磷火那样发亮的白色泡沫。”小说的结尾是壮丽的环境描写,似乎死亡都变得那么美,一切都归于大自然,大自然也摇曳着颜色、情感。这种带有情感的颜色之美“是用人类语言无法表达的”,死亡在这里都显得不悲壮;亘古不变的大自然让一切都消失,世界永远比人更加永恒。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最为神秘的,也是最令人难解的就是寥寥数页的《大学生》——这篇小说也是契诃夫自己最得意之作。《大学生》是契诃夫小说中稀有的意义得到连通的作品,通过一个圣经的故事,看似无关的人共享了某种神秘的体验。不止是人,甚至时间也开始交融,生活“显得美妙、神奇,充满高尚的意义”。
难寻找的意义
意义是契诃夫小说的全部,是凌驾一切的存在。之所以人物仿佛走钢索般不停地摇摆着自己的内心所思,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生活给予得太少,而又流逝得太快。这少得可怜的给予是漫长生活中唯一的珍品。人物有时会出现某种回光返照,仿佛曾经有意义的美好的一切再度返航。可是对美好的瞬间的追忆一旦飘散,就只有对奔流而去的生活的无限哀怨。生活曾经燃烧过某种不同寻常的火苗,如今只剩下了永不复燃的死灰。
在《在朋友家里》中,当瓦丽雅突然开始朗诵诗歌《铁路》,曾经的瓦丽雅又回来了。随后她忘记了诗句,波德果陵又续上,而最后那句沉重的叹息由瓦丽雅笑着说出:“只是可惜啊,无论是我还是你,都无缘生活在这美好的时代里。”随之而来的呆板的谈话中,波德果陵希望她再次朗诵一下诗歌的时候,她只是回答自己全忘掉了,刚才是无意中念出来的。多么令人感到伤逝的瞬间啊!在美丽的海市蜃楼后发现她依旧沉沦在生活的泥潭中。生活的走向永远和最初的想象背道而驰,不存在任何救赎。
契诃夫每部小说的结尾都充满了平静的张力,因为人物意识到了生活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灭,伤口无法再愈合,错误无法再弥补,剩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折磨。乏味是我们一生的缩影。我们的一生也许仅仅只是短篇小说。所以当契诃夫的人物最为清醒的时候,也是他们最为迷惘的时候——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这也是他们最为无助的时刻,甚至有时他们居然能从死亡这个即将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得到慰藉。
契诃夫人生最后的小说《新娘》是罕见的真正明亮而乐观的短篇小说,虽然在这里也包含了对物是人非的感叹。娜嘉最终迈向了新生活,将那传统的婚姻生活远远地抛弃了,即便关于生活的意义为何她还尚不明朗。
也许文学并不需要真正地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小说中寻觅到蛛丝马迹。在《醋栗》中,契诃夫讽刺了那种庸俗的可笑的幸福,而那又硬又酸的醋栗果子便是这种幸福的象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多么无意义,而我们为之丢掉了那么多,最终还哄骗自己这是幸福。伊凡·伊凡内奇说了那段无人在意的自白(又是一个不理解的例子):不要心平气和,不要让自己昏睡!趁年轻、强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
缥缈的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和目标,那么,这个意义和目标就断然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做好事吧!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