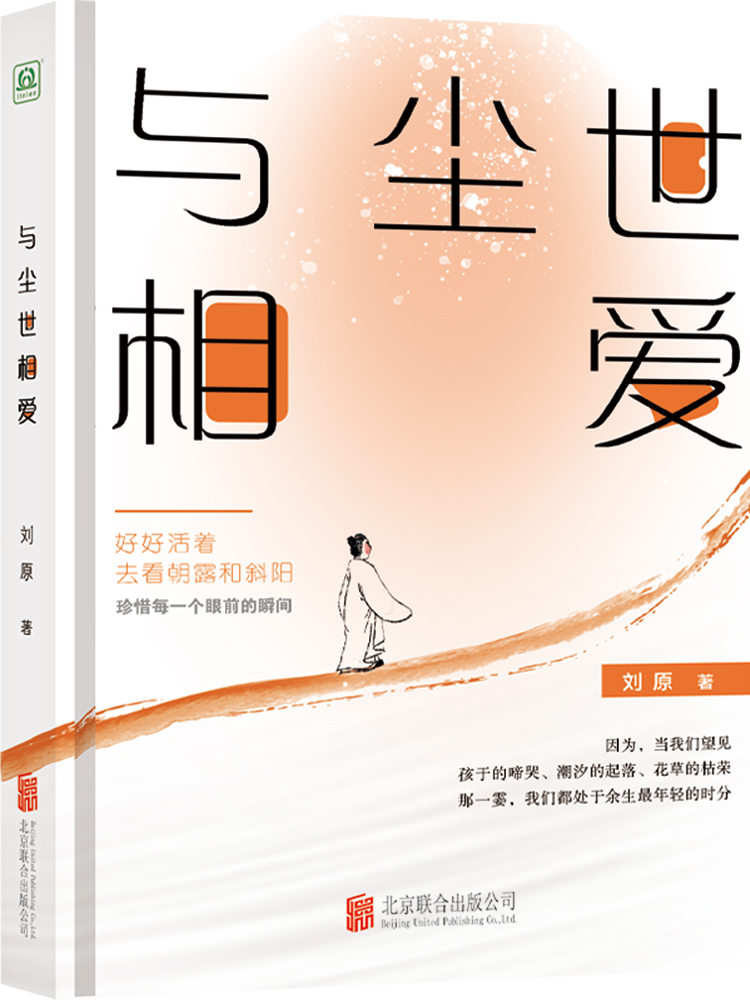仿佛只听过几记沉闷的春雷,望过几朵出走的流云,一段时光便过去了。
上一次出书,是在2011,在10年代的兔年。我迎来了三次诞生。
那个夏夜,我在报馆值夜班,给一张刚诞生的报纸签版,下班后继续在电脑前回复一家杭州杂志的采访,那时我刚出版了《流亡三部曲》。当时还唤作幼齿的婆娘来电话,问我何时下班,我说忙完便回。片刻,电话又来,我很不耐烦地说干吗,幼齿说肚子疼得厉害,我骇得头发都竖了起来,赶紧驾车狂奔回家。
流氓兔呱呱落地。从此幼齿在我的文章中变为兔妈。而我,一边继续在电脑前写作,一边娴熟地给娃换尿布喂牛奶,并且在锅碗瓢盆中成了一个准专业厨子。
再次出书,已经是20年代的兔年,流氓兔已经进入青春期,即将小升初,而弟弟流氓猴也已6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十二年的时光,轻飘飘地流远。
我很难描述这段光阴。倘若时间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当我凝视镜中的自己,望见的不仅是白发与颓唐,还有锥心的悲凉和丧乱。其实,我经历的最绝望的世事,从未出现在我的文字里,那只能独自吞咽,在长夜里独自失眠。
但我亦是有过欢愉和欣喜的。有一天,当年三部曲的编辑徐蕙蕙跟我说,不如出本书,记录一下这些年间看过的云、行过的桥、做过的菜、历经过的生离死别?
我遂允了。于是,12年后,她又编起了我的书稿。
你们都曾见过狂狷浪荡的我,说黄段子如拾草芥的我,那么,且看一看面容慈悲、在暮光里寂静一笑的刘原,被时光之锤重击之下,变成了什么容颜。
早年,我对口腹之欲并无追求,反正地王之巅旋转餐厅的海鲜盛宴也吃过,杨箕村的潲水油快餐也吃过,不止一次尝过国宴厨师的手艺,也没觉得比苍蝇馆子好多少。我属于饿过的一代,口舌没那么刁钻。但当爹之后,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各种菜系,有些菜肴甚至用十多种配料进行搭配试验,无他,只为孩子能吃得满脸油花。
所以,这本书收录了一些关于美食的文字。
我对游山玩水更无兴趣,年轻时当记者,约等于公费旅游,我却只执着于深夜码字换稿费,到哪里都没心思去玩。但有了娃之后,我的玩心却重了,流氓兔两岁之前,我已带他游历过小半个中国。其实我依旧不爱玩,只想带娃儿看看这片山河。我的童年没见过世面,17岁上大学时才第一次出省,自己缺过的,遗憾过的,希望别在下一代身上重复。我更在意的,是带这俩客家人的后裔,去见识辽远,见识美好,让他们将来择水而居,莫在乎贞洁坊一般的乡愁,心安之处即故乡。
所以,书里也收录了一些关于行走的文章。
当然,本书亦有关于生离死别的文章。此生爱过的人,终将在茫茫人世中远去,不回头,也不再相见,甚至湮没于所有的梦境里。
所有的痛哭,在长夜里都是孤独的。
所有的月光,在暗夜里都是清冷的。
时常想起纳兰性德那句诗:当时只道是寻常。
每每想起,心头便被剜一刀。童年时岸边枝头的虎头蜻蜓,少年时绿皮火车的浪迹天涯,青年时孤黄灯下的伏案耕作,当时都觉得是再平常不过的人生。如今回头望去,它们或许都是寻常的。但是——
已永不再来。
疫情这三年,沉痛过的人,啼哭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伤逝。
可是,我们都来过,见过繁花与落英,喧嚣与寂寥,狂欢与跌坐。那么,写下它,记住它。即便假装遗忘也背过身去抹一下眼角,它亦算是我们今生的孽缘了。
好好活着,去看朝露和斜阳,珍惜每一个眼前的瞬间。因为,当我们望见孩子的啼哭、潮汐的起落、花草的枯荣,那一霎,我们都处于余生最年轻的时分。
让我们继续与尘世相爱。与美好相爱。与自己相爱。
刘原
2023年4月17日于暮春长沙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