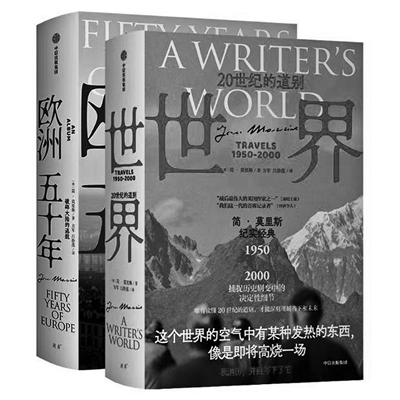主题:当我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
时间:2023年2月8日19:30
地点:线上
嘉宾:刘子超 旅行作家、媒体人
李孟苏 文化作家、媒体人
主持:刘丹亭 编辑、书评人
英国国宝级作家简·莫里斯作品集的首批两本图书《世界:20世纪的道别》和《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返航》,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这将是简·莫里斯作品在国内最完整的一次呈现。
简·莫里斯( 1926—2020),原名詹姆斯·莫里斯,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旅行文学作家。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泰晤士报》和《卫报》担任记者,前往世界各地报道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1961年艾希曼审判等。60年代中期起,他成为自由撰稿人,行走世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莫里斯出版了40多部作品,包括多部有关大英帝国兴衰的历史著作、多部虚构小说、多部回忆录,以及众多旅行文学作品和散文集。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和广博的历史素养,中东、远东、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地的历史和现实、世情和人心都在其笔下凝结成永恒的瞬间。
她是一个很古典主义的人
刘丹亭:简·莫里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前半生是詹姆斯·莫里斯,后半生变成了简·莫里斯,是一个奥兰多式跨越两性之间桥梁的人。
李孟苏:前半生,他是不折不扣非常出色的男子汉形象,他结婚,生了四个孩子。事业上的成就也非常大,作为记者,他达到特别让人羡慕的职业高度,几乎20世纪中期所有大的历史事件,他都是目击和记录者。而开始服用雌激素、做了变性手术之后,作为一个女性,她也完成得非常好。
刘子超:她的很多感觉并不是从一个单纯的男性或者女性视角出发,而是把两种视角非常微妙地结合在一起。变性以后,她跟妻子关系一直很好,两人一直相伴终老。只是从过去的夫妻关系变成了姐妹关系。
刘丹亭:她和伴侣在70年代是解决不了婚姻的法律问题的,当时只能选择离婚。但到后来,英国又允许这种同性伴侣结婚,她们又在2008年选择了复婚,后面携手走完一生。
李孟苏:她书里面写到她们在威尔士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上选择了一个墓地,她早早把墓碑刻好了,上面写着“这是一对朋友的生命尽头”,她真的是一个很古典主义的人。
刘子超:那个村子我去过,那时候她还在世。我当时在牛津读书,周末的时候租了辆车开到威尔士。
她觉得这辈子最令她魂牵梦绕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河边上的小村子——拉纳斯蒂姆杜伊,一个挺长的威尔士名字。另外一个就是的里雅斯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军服役时曾被派驻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我也算在追随她的足迹,这两个地方我先后都去过。特别是威尔士的这个村庄,特别小,有一条小河穿过一座石桥,两边是石头房子,河水冲刷着桥底下的大鹅卵石,村子的一条主路走到头大概只要五分钟时间。没有酒吧,没有商店,只有一个教堂,有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故居。房子门口会有名牌,我当时很有冲动去敲门看她在不在,但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
李孟苏:她在《欧洲五十年》和《世界》这两本书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在威尔士的农舍。房子以前很旧,有非常高的横梁,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每个人都说这房子像个桅杆很高的帆船,她也跟每一个人说,每天都有鸟来敲不同的窗户,好像想要进来。她说鸟自古以来就是死亡的象征,你听得到鸟敲窗户的声音吗?这让我想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我觉得她是一个预言式的作家。
刘丹亭:《欧洲五十年》一开始写到一个场景,在他20岁还是个军人的时候,来到的里雅斯特,在这个城市的海滩上眺望。他看到的其实不是的里雅斯特,而是这个城市背后隐约展现出身影的欧洲所有大都市——一个曾经非常繁荣的世界,一个类似于昨日逝去的世界。
我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就像是的里雅斯特之于欧洲,莫里斯也以这种个人式的经验带着我们游历世界,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人背后,在这些看似零碎、破碎的经验之后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
刘子超:莫里斯的创作其实蛮难谈的,她写的东西太多了,一辈子出了四五十本书。译成中文的现在也有好几本,但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世界》,是她五十年写作的一个结集。如果你还没看过简·莫里斯的东西,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有点像《古文观止》,有助于了解作家的一生。
特别不愿被说是一个旅行作家
刘子超:《世界》讲到她写作的开端。1953年,他报道了英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消息。在前往攀登珠峰之前,英国登山队在威尔士的一座山上训练。我去过那座山,叫雪墩山。它其实只有一千多米的海拔,但是比较险峻,经常覆盖着大雪,有点像珠峰最后一公里的感觉。山脚下有一个旅馆,他跟登山队一起住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旅馆餐厅的天花板上,其中就有詹姆斯·莫里斯——那时他还叫这个名字。
她之后写了太多书,写过西班牙,写过大英帝国的历史,写过的里雅斯特,写过牛津。《牛津》是另外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因为我一直觉得作家写自己熟悉的城市或者国家其实很难。另一本《香港:大英帝国的终曲》,气质有点哀伤。
《香港》是她晚年写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的里雅斯特》。在看这两本书时,我一直在想,她晚年在思考什么。我觉得她在的里雅斯特和香港之间找到了某种关联。它们都曾经是帝国的出海口,都曾经是重商主义的城市,都非常繁华。
李孟苏:莫里斯的写作特别感动我的是,她用很多笔墨去写一些普通人。《欧洲五十年》是我写的序,所以这本书我看得特别仔细,看了好几遍。这本书里基本上都是在写普通人,她想为历史做一些注脚,为普通人也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声音。
她特别不愿意别人说她是一个旅行作家,她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历史作家或者是历史学家。她也确实写了三部头的《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的第一本署名詹姆斯,是她在男性性别的时候写的,第二本写于她正在做变性手术期间。第三本就是以简为署名写的,这时候她成为了一个女性。她说,在变为女性以后,再回过头去看自己作为男性时所写的书,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太大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写史、写书,纯粹是出于一种知识或者是美学、艺术方面的角度,很少出于政治立场。
她说过一句话:“我们在采访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比如教皇或者某个君主、某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给他的身高增加半英寸或者是一英寸。这是我们作为记者也好,作为历史学家也好,去书写历史时特别容易受到的一个诱惑。”所以她竭力希望抹掉这一英寸或者半英寸,给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身高。
她希望能传递一个信息或者推倒一个信条,试图呈现一个事件或者故事的两面。她说:“我不想去试图歪曲任何东西,以达到某个目的。”所以她写了很多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历史上,大都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人肉背景,或者说一个“气氛组”,会被扫到历史的尘埃中。而简·莫里斯愿意在她的书里为每一个普通人留下他们的声音和事迹。
李孟苏:她曾经说过,要写一个城市,第一,要像E.M.福斯特所说的那样,漫无目的、游手好闲地去逛;第二个体验就是要去找一些诗,从诗歌里去体会这个城市。这两个都给我特别深刻的感触,以至于我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去玩,也会像她这样去学习、去体会。
她经常说,每去一个地方,她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法庭。因为在法庭上,能看到世间很多的人情,看到人性的东西。第二个特别愿意去市场和火车站。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她看东西的视角非常独特。
刘丹亭:是这样的,我觉得莫里斯本身有一些很奇特的地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介入了很多世界上非常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人类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比如说审判纳粹战犯。但似乎到了六七十年代,她慢慢从这种特别宏大的视角当中退了出来,回归到了一种可能更个体化,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更印象主义式的描写。
李孟苏:我觉得这可能跟她的年龄也有关系。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是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她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采用了一种稍微静态的方式,在家里写各个城市的印象记。这可能是她对抗走下坡路的一个办法。
还有一点,这可能跟她的性别认识也有关系。因为这个时期正好是她越来越倾向于作为一个女性,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性别身份的阶段。
永远处于一个跨界中的状态
刘丹亭:在20世纪60年代,她对父权的世界感到有一些失望,她认为包括政治、艺术等,其中都有两性对立的隐喻,似乎她越来越对这种性别的冲突和对垒的状态感到疲惫,有一点想从当中逃遁出去,以至于辞掉了那些报社工作,慢慢回归到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她开始给杂志社撰稿,用她的话来说,写作是完全出于她的爱好,是她愿意用生命的热情来做的事情。
李孟苏:作为一个女性来讲,我看她前后的东西,并没有看出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她说她写东西更多是从艺术的角度入手,更多的是审美。我看她的东西,看不出一个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她写的题材也比较中性。要是去写小说或者戏剧,她可能也会表现出很理性化的一个倾向,但她写的是非虚构,我不认为她有特别强烈的女性视角。不过,还是能看得出来,成为一个女性以后,她看待男女问题的一些方式和一些角度是变了的。
她曾经说过,更喜欢自己性格中柔软的一面,而不是坚硬的一面,而威尔士也更接近这种柔软。从离开报社成为一个自由作家以后,她也开始了寻找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她说要把自己从一个不列颠人变成一个威尔士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从男性转变为女性,所以她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她的性别认同能自洽,正好能重叠在一起。
刘丹亭:是的,好像她特别善于兼容各种不同的身份,身上融汇了各种身份的特质,她好像永远都是处于一个跨界中的状态。
在《欧洲五十年》这本书里面,莫里斯谈到了对大众旅游的看法。谈到去圣伯纳德山,刚好遇到风雪,然后就被一些修士给救了。他看到他们还是过着一种非常传统的生活,包括还养着那种特别漂亮的圣伯纳犬。但50年过后,她再回到这个地方,就发现这个地方完全商业化了。
在莫里斯刚刚开始游历世界的时候,相对来说,旅行还是属于少数人的一种特殊体验。一些有闲有钱的阶层,或者他们的职业有特殊性,比如军人或记者,他们才有可能去旅行,才会获得这种特殊的、特别激动人心的体验。随着时代变迁,大众旅行变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也使很多经验变成了一种可以复制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消费品。
刘子超: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早在19世纪,大众旅行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壮游”(Grand Tour)这个词就已经出现。那个时候英国的年轻人毕业后去欧洲大陆旅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像法国、意大利的很多地方,当时就已经相当商业化。这种商业化的浪潮在不断向东,从西欧一直向欧亚大陆深处移动。
我最近在波黑的莫斯塔尔,一个当年内战打得非常凶的地方,城市里还能看到很多战争废墟,墙上有各种弹孔、炮弹坑。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商业化的旅游也已经开始了。因为夏季七八月份是欧洲的旅游季,会有很多欧洲的游客来这边玩。可能本地也没有太多经济上的选择——民族对立情绪依旧很严重,国家内部分裂,因此外国投资很有限,所以大家就一窝蜂地把旅游业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从这一点上,你能窥见这个城市的某种真实状态。
旅行的意义就是去丰富地度过这一生
刘子超:《世界》这本书中90年代的部分,莫里斯也正好写到莫斯塔尔这个地方。莫斯塔尔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一座拱形的石桥。石桥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候建的,是莫斯塔尔最有名的古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桥在90年代内战的时候,被克罗地亚人的炮火摧毁了。现在的石桥其实是内战结束10年后重新修建的。莫里斯来到这里的时候,内战刚刚结束,这里还非常萧条。内战结束20多年后,这个地方也发展了旅游业,也商业化了。某种程度上,潮流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但你还是能从商业化的缝隙中去窥见这个地方真实的脉搏和跳动。
李孟苏:商业旅行其实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因为那时候英国发明了铁路和火车,并在19世纪迅速在全境修了非常发达的铁路网,这就带动了大众商业化的旅行,特别是工人阶级会非常兴奋。就像刚才子超说的,之前“壮游”只有贵族和有钱的工商阶层才负担得起。但有了火车以后,工人阶级发现自己也能非常轻易地到达某一个旅游胜地,比如说头天半夜两三点坐火车,到了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我就能到一个海边的小镇,看到朝阳,我也能在防波堤上和我的爱人跳舞。其实从这时候起,铁路旅行就已经在改变地球上的风景。
简·莫里斯曾说到一个图书馆,收藏有约翰·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这本书的首版。罗斯金坚决反对工业化,坚决反对铁路。他到威尼斯去,看到铁路已经修到了威尼斯。他从威尼斯坐火车穿越欧洲大陆,非常痛心疾首,说铁路侵蚀了威尼斯的泻湖,破坏了莱茵河,“特纳曾经描绘过的那些景色,我再也见不到了,非常忧伤。”
但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修铁路也好,修铁路桥也好,其实就是对欧洲的景观在做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哈利·波特电影,蒸汽火车会穿过苏格兰的一座格兰芬南大桥,这座混凝土大桥就是在19世纪末修的。100多年过去,混凝土里的盐类成分渗透出来,附着在桥体上,赋予大桥饱经风霜的岁月之美。当年施工时用了木质的模板,木材的纹理留在混凝土上,给桥体表面增加了机理。它是单轨铁路桥,仅宽5.5米,如纤巧的白练环绕山间,绕出优美的弧形。它并没有损失自然风景,反而增加了风景的维度,成为铁路线经过地区的象征。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一味哀叹商业旅行破坏了景观,其实我们可能是有一点坐在书房里不接地气才这么说。越是这样想,我越感谢简·莫里斯,因为她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让我们在看到她的书的时候,被勾起对于过往世界的一点乡愁。
刘丹亭:孟苏老师刚才说简·莫里斯记录了这样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可能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她的很多经历,还有她的很多著作都是不可能再被重现,或者再被超越的。想请你们谈谈旅行对于二位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孟苏:旅行对我来说,可能就像莫里斯所说的,我要去看看世界。只不过我还没有她那样的自信让世界看看我,因为我自己太微不足道了。
刘丹亭:您说的这种体验其实我也有。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个女作家写的一本书,她当时描述了她去伯利恒主诞堂,触摸耶稣诞生处的那颗银星,描述它的手感。当时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自己触摸看看,所以我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去了伯利恒,然后真的触摸到了。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幻梦终于实现了的感受。
刘子超:看简·莫里斯的书,你会觉得这个人的一生过得太丰富了,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让自己的一生尽量丰富地去体验,去认识世界。我觉得,认识世界最本质的手段,一个是旅行,另一个是读书。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就是去丰富地度过这一生。这是莫里斯给我最大的启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