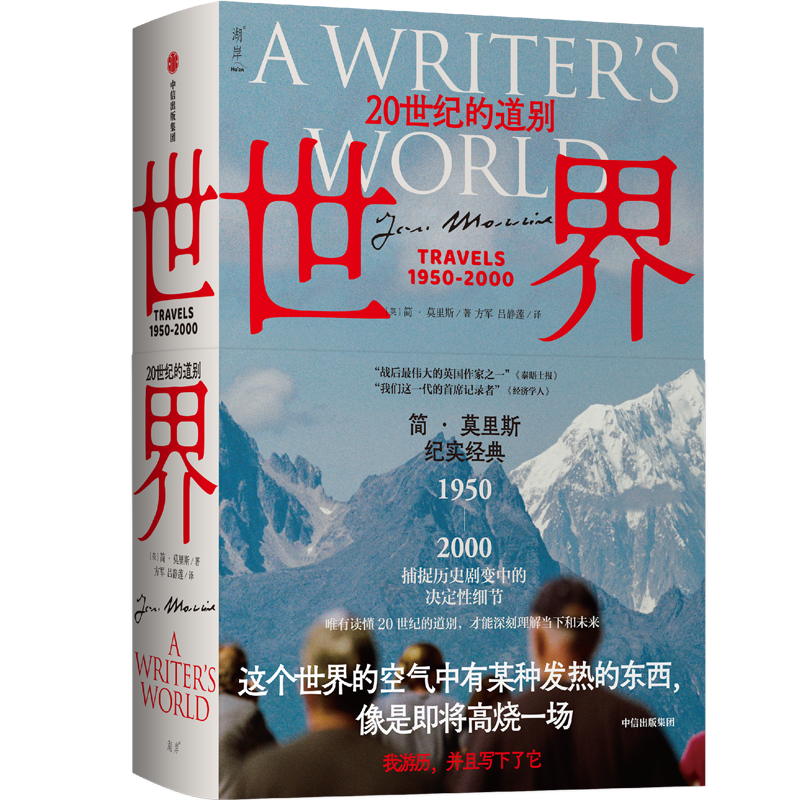《世界:20世纪的道别》采样于我所游历的半个世纪。它一边前进,一边选择自己的主题。它的题目也许暗示了这是一部更深思熟虑、更客观的作品,类似于某种回忆录——充满哲学思辨的小说家,或者从一份严肃大报退休的专栏作家,会在书中对其时代加以沉思。别给骗了哟,这个由我的报道和随笔组成的文件夹,可远没有那般慎重,也并非包罗万象。它的确镜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却是以一种浮华得多的方式。它的本质更接近于一场展览或一次表演,且关于其作者的内容至少与关于世界的同样多。它的开篇有一点震撼。如果说它的收尾显得更加谦逊,那是因为50年的书写与漫游生活将会让大多数人最终更安静一点。哪怕是鸫鸟,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带着无忧无虑的狂喜歌唱。
本书所述时期覆盖了20世纪的后半叶,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二战初停到千禧年终结。当然,按照惯例,我忍不住要说,这是历史上一段决定性的时期,但它可能并不比其他时段更具决定性。实际上,我所书写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精神也许比大多数时期更幸福、更乐观。这是冷战的时代,当人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共产主义部分被桎梏在一种无法和解的猜疑中,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别的公共焦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频频发生。核弹灭绝人类的前景使人忧虑,毒品文化无情的散播更令人困扰。环境遭受可怕的污染。艾滋病这一邪恶瘟疫出现。贫穷,甚至饥荒,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全球化的降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座星球日益加剧的美国化。人们环绕全球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许多通常是无法预料的问题。世界人口的增长给易受影响的预言性情绪投下了阴影。
但是,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害怕,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补偿这些恐惧与痛苦。例如,欧洲的各个帝国从它们遍及全球的广阔领土上后撤。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产生有益的后果,并且被许多冲突损害,但普遍看来,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承认: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宣布统治另一个国家。联合国,尽管经常表现得虚弱无能,至少是国与国之间预期的兄弟关系的一个标志。西方人正在摆脱有组织宗教的更为原始的掌控。在东方,伊斯兰教似乎大体上还是一种保证秩序的高贵的力量,而对许多人来说,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在我这半个世纪的行程中,欧洲那些争吵不休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联合。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对自然状态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半个世界的人口仍然贫苦如昔,而另一半则拥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富足。人类的第一次太空探测似乎——至少在早年——预示着美妙的成果即将到来。
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变得比他们在“二战”之前更加宽容、更加和善、更加慷慨。不论漫游何处,我很少受到威胁,也几乎从未被打劫。我们仍然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想——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我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泰雅尔·德·夏尔丹的理论仍有可能被信仰: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所有的种族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
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反应,是我自己对我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看法。这是我对世界的感受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初,我24岁;20世纪90年代末,我74岁;因此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全球历程也是一个生命的历程,从青年的落幕到晚年的开场。其中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够可靠的判断,全被生命从韶华到衰老的重大改变染了色——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过程,但在另一些方面,思考方式的任性的转换和头脑的改变也削弱了判断。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观点和价值的连贯一致,我们不仅被经验和成熟度影响,也被情绪、变幻无常的口味、厌烦和个人境遇左右。
我并不经常深深地卷入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事件中去。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这通常并非一种内省的生命,但在某个方面,自我审视也确实纠缠着我。从童年开始,我就恼火地认识到,我被生错了身体,我真该是个女人。在从军的四年里,在作为外国通讯记者的十年里,为了应付这个谜,需要一定程度的内省,虽说不上是欺骗:当我通过俗称“变性手术”的手段最终解决这个难题,从“詹姆斯”变成“简”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某些批评家宣称在我的写作中也清晰可辨的解放感(倘若你乐于自己下判断,最终的变形发生在本书《卡萨布兰卡:变性》一文中)。通常来说,这样戏剧性的桥段并不为反思性的文集提供一个核心,而在本书中它也确实没有,因为对我来说,它始终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后两者对我风格的影响远大于任何简单的性别转换。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写作者,在这半个世纪,我游历了这个世界,并且写下它。我从记者起步,当时所接受的观点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例子),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我从牛津毕业后就加入伦敦《泰晤士报》,几乎立刻开始了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当时的《曼彻斯特卫报》。那时,这两份风格突出的报纸都处在声名的顶点,富有威望,包容各种个性,它们不仅容许我或多或少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更给了我一个正面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这可耻地助长了我的自负。压根儿就是一转眼间,我就开始对全人类的问题指手画脚,并且建议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解决它们。借用马克斯·比尔博姆说他自己和牛津大学的话——是《泰晤士报》和《卫报》让我变得难以容忍,但我依然感谢它们。
尽管我是个有抱负的文人,但我也是个有抱负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从来就憎恶权威,尽管有时会被其辉煌诱惑。当我为报纸写作时,这种偏见有时鼓舞,有时压抑了我的新闻生涯,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开始靠自己漫游。我被这个广大的世界过早地变得乖戾,不想再让自己的写作拴在日常新闻上。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间,我主要忙于写书,通过卖游记给杂志(主要是美国的)让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并保证家人免于贫困。我只为两家报纸工作过,但在20世纪最后40年,我为几十本英语杂志工作,还写下35本书。
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某些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
因此,这是我的工作成果的实质。这本书中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去一个或另一个目的地的旅行。它们与最初发表时基本保持一致——不管现在读起来多么不成熟——只在读起来沉闷或篇幅过长的地方做些删减。有时我会添加阐释性的评论,并容许自己进行少量文学性而非新闻性的事后考量——比如,我觉得自己以前经常滥用分号,而且,我逐渐变得不喜欢年轻时像称呼船一样称呼城市为“她”。我删掉了让我觉得多余的直接描写的段落—―既然现在所有读者都能自己去任何地方。有时,当年的写作在政治正确性上的要求比时下低;有时,很久以前我的态度令人尴尬。如果偶尔有年代模糊之处,那部分原因是历史自有其任性,拒绝接受年代的约束,还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从不认为日期有多重要。我基本没有收录有关我家乡威尔士的文字,但是请相信我,在这本书中,几乎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某种威尔士的东西,潜伏着、微笑着,像是修道院免戒室里的绿精灵。
作为对这个世界半个世纪的反映,这个选集可能往往会是有误导性的,或者是幼稚的,但这真的无关紧要。我写的当然是这个世界,但它是我的世界——正如我自己在另一种语境中所表述过的,“这是事实吗?这就是它的样子吗?它是我的事实。尽管在现实方面,它并非总是真确,但在想象方面,它是真确的”。
文/简•莫里斯
(本文摘自《世界:20世纪的道别》,简•莫里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本文标题系编者拟,原标题-序言:这是事实吗)
来源:大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