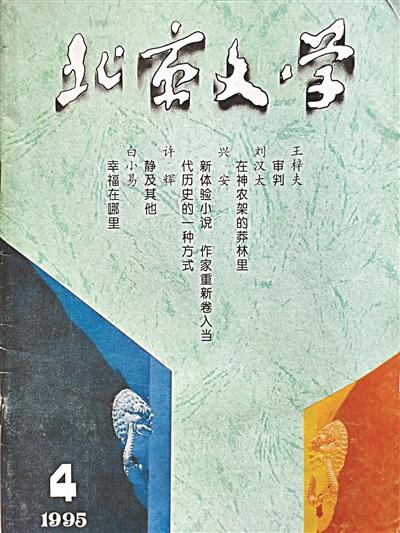2010年,《北京文学》六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所谓十五年的记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了十五年,从大学毕业,二十三岁,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岁。整整十五年。
离开《北京文学》的二十年里,我几乎没参加过《北京文学》的活动,但它像个影子一样,时常伴随着我,挥之不去。至今,经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还会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还有人甚至误以为我还在那儿任职,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参加台湾作家张大春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的读者见面会,我和敬泽、止庵等做嘉宾,敬泽那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会后某大报在发表综述的时候竟然给我安的头衔是《北京文学》主编,让我好生不自在。
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学》,它让我在大学刚一毕业,就能迅速地与文学靠得那么近,接触到了那么多我心仪的大家,同时也让我见证和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和九十年代的辉煌。我能变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梯。
除了撰写上面的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1990年代前后〈北京文学〉的几点考察》。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很多文章,都会不自觉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经历或背景。
林斤澜
“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
说起《北京文学》,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还是先说说主编林斤澜先生吧。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林斤澜先生是那种即使不在了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如今,林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四个月后,林老和李陀先生便开始主掌《北京文学》。编辑部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准备迎接新的变化。那个时候的《北京文学》阵容强大,搭配合理:作家林斤澜先生任主编,评论家李陀先生任副主编,陈世崇先生做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先生任副主任兼小说组长,编辑有作家刘恒、陈红军、章德宁、傅峰、赵李红、刘英霞,还有我和吕晴(作曲家吕远的儿子)。林老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作家,有汪曾祺、王蒙、张洁、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黄裳、章品镇、林希等。李陀先生则更多地集结了中青年作家,有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张欣辛、刘索拉、刘庆邦、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有这些老中青的国内一线作家的鼎力支持,《北京文学》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却赢得了至今被文坛津津乐道的声誉和影响。
1997年林斤澜(左二)与兴安及浙江作家钱国丹
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
有一次,我带着作家余华去看林老,恰巧林老临时有事出去了。我和余华坐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等他回来。那时余华刚刚有些小名气,长相清秀,不大爱说话。我一边抽烟,一边和他聊着闲天,一直等到天色暗下来,林老终于回来了。林老在楼门口看见了我们,连说对不起,然后一定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林老是美食家,也好喝酒,席间不断地给我们夹菜。他夸赞了余华的突变,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两篇让文坛陌生的短篇作品。林老作为短篇小说大家,在写作理念上一定与余华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辈的呵护和鼓励,他支持编辑部重点推出这两篇作品。小说发表后,读者叫好,评论界却一片沉默。但是在林老和李陀先生的支持下,《北京文学》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差不多同时,《收获》也发表了他的《一九八六年》。直到李陀先生在《文艺报》撰写了一篇重要评论《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之后,似乎才一下子唤醒了评论界。余华终于被文坛认可,且一路红火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已经不好发表余华的作品了,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了余华的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活着》(长篇《活着》的前身),已经卸任主编两年的林老,专门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最近读了余华的新作《活着》,是一篇杰作,劝我一定读读。那时候我们谁也想不到,包括林老,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发行到1000万册。
上世纪90年代刚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
1999年底我离开《北京文学》,之后与他逐渐联络少了,但在一些文学的聚会上还能经常听到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声,他对我的关注和关怀依然让我感动。2008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厚重的一大本。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能是他最漂亮的一本书。老人家非常高兴,可惜那天因为我临时出差没能亲自把书送到老人手里,后来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一次,这成了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在林老的告别会上,播放的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节奏活泼而欢快,这使我想起当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别会,播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曲调优雅而温柔。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成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
1987年林斤澜(左二)与《北京文学》的编辑及作家在山东泰山
浩然
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
1989年8月,作家浩然接替了林老,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浩然先生与林老不同,他是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农民和农村作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主政《北京文学》时期,比较多地关注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作者多是基层的远郊区的作家,他们非常熟悉当下的农村生活,但是在艺术和思想深度的把握上还是有不少欠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期刊物中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北京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在大家看来,这些作品按照《北京文学》的选稿要求,属于勉强达到发表水平,而浩然先生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出,确实让人意外,也自然引起文坛的非议。有一些作家甚至联合起来,拒绝为《北京文学》写稿。《北京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浩然先生肯定是新中国之后一位重要的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他那时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县,主编着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苍生文学》,刊名是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命名。有人甚至说,他是以《苍生文学》的标准来办《北京文学》。——这些往事我就不想深入地谈论了。我只想说,浩然是一个好人。他一辈子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关心农民,并毫无保留地帮助农村的写作者。作家刘恒(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就曾这样评价浩然:“我一直敬重他的人品。”也正是他的人品、他的善良和宽容,让他没有固执己见。
1987年兴安与浩然(左一)在《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培训班上
1993年,浩然先生感到了外界的抵触和压力,于是决定不再过问编辑部稿子的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年底的“新体验小说”这个曾引起国内文坛轰动的文学实践。这次活动将陈建功、郑万隆、刘恒、刘庆邦、刘震云、毕淑敏、李功达、徐小斌、邱华栋、徐坤、关仁山等这些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重新拉回到《北京文学》的周围。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一年时间里,《北京文学》连续发表了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刘庆邦的《家道》、刘恒的《九月感应》、徐小斌的《缅甸玉》、关仁山的《落魂天》等二十几篇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我的那篇《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纪念“新体验小说”倡导一周年》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在《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让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更让我敬佩的是浩然先生虽然不介入刊物的编稿工作,但是依然关注刊物的发展和建设。那个阶段《北京文学》正处于办刊经费不足,四处化缘,以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困难时期。我们的编辑经常会花相当大的精力去找企业拉广告、找赞助。而浩然作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者,在大众中尤其是在郊区县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有些乡镇企业就是看在浩然的面上,才愿意给我们赞助。有些重要场合,在需要他出场和站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以支持。而对青年作家尤其是基层作者的培养和扶持,他也会义不容辞。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经常组织作家聚会,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笔会,他特地从三河赶来参会。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栖湖召开的北京郊区作家笔会,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听说我们在此开会,主动来看望大家。就是在这次会上,他送给我了他刚刚出版的自选集,并给我题写了“作家靠作品活着”的赠言。
1999年底,浩然先生辞去了《北京文学》主编。2000年春节,我与作家陆涛专程到三河,给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文学》。我们两个人从上下属关系,变成了文学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彼此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然。临走,他送我和陆涛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写道:“我有幸曾在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和他共事过8年。我认为他不光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更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确实,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学界是共识的。我非常怀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在今天也许读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小说中那些充满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人物(萧长春、马立本、滚刀肉等)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喜鹊登枝》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清新、干净,富有新时代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刚刚翻身后的农民的喜悦和单纯。”这算是我与他的最后道别。
现任作家出版社编审的兴安
李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再说说李陀先生。他在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时期担任过副主编,同时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长在北京的达斡尔族人,我是少年时期来到北京的蒙古族人,两个人的老家都在呼伦贝尔,所以,我与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内心中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因为,在《北京文学》期间,他是对我影响最多的人。
李陀先生首先是个小说家,写过《愿你听到这首歌》《自由落体》等,前者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是“文革”后最早带有实验性的短篇作品之一。后来他又涉足电影领域,然后专事文学批评。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很多当时的文学事件和作家成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联。比如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关于“寻根文学”的缘起等等。他思维敏锐、敢于直言,不留情面。记得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发言,他刚刚说了几句,就被李陀一句“你说得不对”给弄得下不来台。而对他喜欢的作家,他则绝不吝惜赞美之词。比如余华、马原、格非、刘索拉等等。
1987年以后,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李锐、刘恒、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崭新的面目,陌生的叙事形式,让评论界手足无措,尤其是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处于无语状态。李陀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并希望这些曾经的“顽童”——青年批评家们坐下来,认真地读这些新人的作品。当然,他对这些“新”作家的创作也并非一味称颂,而是褒贬分明,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尤其是对两个风格相似的作家,评价竟然是天上地下。比如他喜欢刘索拉,不喜欢徐星,他喜欢马原,对洪峰却嗤之以鼻。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独立的批评精神,不应被金钱和人情左右。记得90年代,他刚从美国回国,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他刚刚入座,就有会议方给在坐的评论家们分发红包,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费。当发到李陀时,他竟然将厚厚的信封甩到一边,起身离去。
1986年至1989年初,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格非、孙甘露,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记得他的客厅很小,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
90年代以后,李陀先生多数时间在美国生活,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回国讲学或游历。他每次回国,我们差不多都会见上一面,虽然他出国后关注的重点不在当代文学上,而专心于中国当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但依然关心国内当下文学的动态与发展,多次让我推荐年轻作家的作品,发现好的作者依然会兴奋,并且极力推荐给周围的人。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近况,尤其对我近几年的水墨创作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
2018年李陀在兴安水墨艺术展上签名
2018年7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他和夫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刘禾,还有艺术评论家鲍昆专程前来观展。他对我开始的水墨实践非常吃惊,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提出了建议,他尤其对我写的旧体诗和题画诗给予了表扬。我知道,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偏好,记得那会在《北京文学》的时候,他发言到关键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背出一句古诗词来,而且引用得恰到妙处,让在座的人很是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热衷搞“现代派”的人,对传统或古典的东西一定是或者蔑视或者无知。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带球过人。这是他借用足球比赛里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运球,甚至假动作,出其不意地突破对方的防线。李陀先生就是这样,他常常会给人意外之举,在你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他甩在身后。
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年,他回国,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却被他谢绝了。他告诉我,三十年没见了,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没有必要见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见,即使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弃了这种聚会。
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比我父亲小一岁,应该是81岁的老人了,可是在我的意识里,他依然像是一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精神矍铄。去年夏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他今年就不回了,想集中时间写东西,包括他的新长篇小说《无名指》,小说在《收获》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他征求了一些好友的意见,需要做些修改。之后又是一年,今年疫情肆虐全世界,美国尤其严重。他在美国应该还好吧,我非常惦念他。
文并供图/兴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