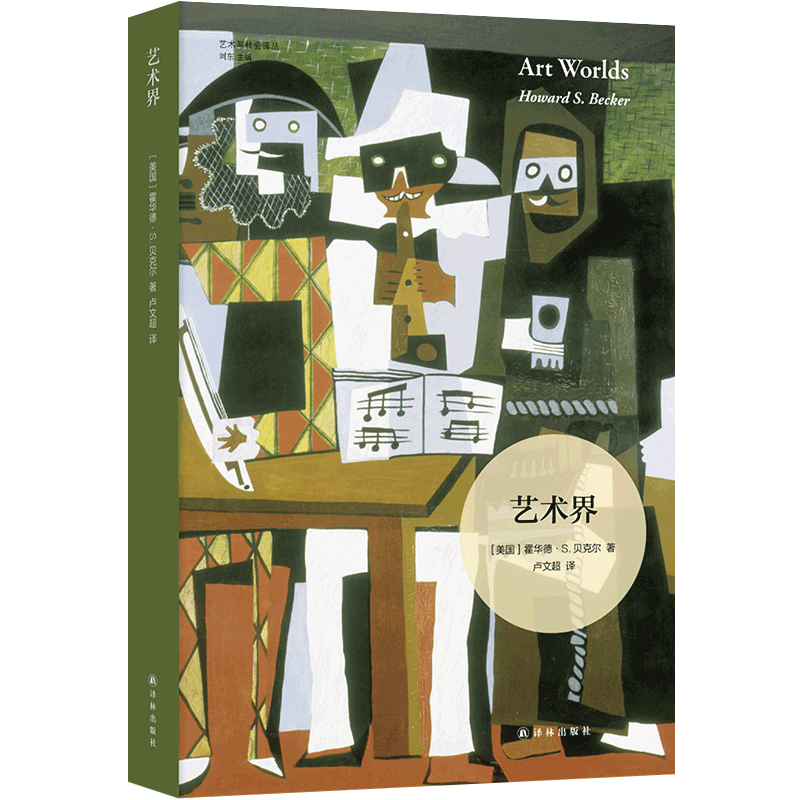经过多年的酝酿、阅读和四处探究,《艺术界》于1982年问世。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研项目”。我没有研究哪个群体的艺术家(比如芝加哥的爵士乐演奏者),或是哪个艺术圈(旧金山的戏剧界),或在此种环境下实践的某种具体艺术形式。相反,它是在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更为一般化的思考,探究的是当你准备研究任何此类现象时,都会提出的相关问题和进行的相关操作。因此,你可以说,《艺术界》正是一种对于艺术的审视之道,试图以此来提出问题以供调查研究之用。我的导师埃弗里特·休斯总是提醒我要避开繁重的理论,他说那应该是在活跃的学术生涯晚期去做的事,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我的很多想法并不适合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而更适合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一旦开始对其进行认真思考,我就别无选择了,只能看看它们会把我带向何方。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界》是经验研究,尽管里面的很多经验材料是别人为了他们各自的目的收集或创造的,而我只是用到了它们。与此同时,我也将自己的很多亲身经历用作了原始材料。对于任何一项研究来说,两者都是很好的数据来源和观念来源。
无论如何,下面就说说我的写作过程。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已完成了几项关于教育问题的大型科研项目,关注点是我和同事们所称的“学生文化”,即那些学生用来克服老师、校方行政人员和其他人给他们制造的麻烦而达成的共识。就此而言,我们已经研究了一所医学院(Becker等人,1961),一所本科学校(Becker等人,1968),以及几种职业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学徒制学校)(Becker,1972)。我十分擅长这类研究,可谓轻车熟路。我有一种感觉——当然并不准确,但那正是我的真实感受——我若进入一个新的教育领域进行研究的话,几天之内我就能知道三年的田野调查会得到什么结果。因此,我已心生厌倦。
1970年,我有一个机会逃离这个死胡同。当时,我从西北大学休假一年,到了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就在那时,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艺术界》的研究。我想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想,艺术社会学正是一个尚待开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所做甚少,百端待举,而已经做的那些,在年少轻狂的我看来,则大都乏善可陈。那时,人们能读到的关于这个话题的大部分书都是欧洲思想家写的(比如Goldmann,1965)。这些书哲学气息浓厚,致力于探讨美学经典问题,专注于评判艺术价值,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美国完成的少量相关著作则大部分都是定量研究,并没有真正触及艺术活动的组织(比如Mueller,1951)。
一个研究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具体到《艺术界》而言,可以说,在我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之前——当我十一二岁开始成为一个钢琴演奏者时——它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弹钢琴是一种经历,它为我的人生以及我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涯增辉不少,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它给了我很多,其中有我们可以合理地称为“数据”的东西:对事件的观察,对谈话的记忆。在思考中,这些切身经历都可以为我所用。
对于做研究和思考研究的成效,我遵循着休斯的做法,这非常依赖于直觉。休斯知道怎么做,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能够解释他是如何做研究的(参见他的文集,Hughes,1984)。我成长在一个方法论自觉的时期,因此,在我如何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上,我被鞭策着要有反思精神。和休斯相比,我在反思方面受到的鞭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开始一项研究时,我总是很清楚我的盲点所在,正如在我写《艺术界》时一样。我对主题的感觉模糊不清,我很确定,我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也同样确定,无论这个疑问或问题最终结果如何,我并不清楚研究它的正确方法。我总是傲慢自负,以至于在我即将研究的题目上,对现有的大部分相关著作视而不见——我并非要在这里自吹自擂,而仅仅想承认我是这么做的。
这并不是说我一点儿想法也没有。有人设想,他们自己就像一块白板一样进入一个领域,等待着观念自动“现身”。我并不喜欢这种方式,这在语法上就讲不通,话题、问题和主题都不会自动“现身”。更好的说法是我们使它们“现身”——一旦开始研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知识,由此我们将那些观念创造出来——尽管这么说有些笨拙。这意味着我们要运用每天学到的新东西,将所掌握的全部理论都用于每天的发现之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新的疑难和新的问题。我们这么做时,所借助的研究观念是赫伯特·布鲁默(1969,147—152)所说的“启发性概念”。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联,简括而言就是:理论提出问题,表明我们需要考虑什么,并指出我们的盲点;研究则回答问题,并且使我们意识到尚未念及之处,这反过来又暗示了理论的可能性。稍后,就理论和数据之间的这种来回往复,我将举例予以说明。
一旦我开始研究某些东西,在指引我的研究观念之中,有三个最为重要:
1.“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一起做事”的观念。这是我从布鲁默那里(Blumer,1969,70—77)学到的,他的表述是“联合行动”(我更喜欢说“集体行动”,但和布鲁默所说的意思相同)。这意味着,无论我研究什么,我总是会寻找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尤其是那些习惯上并不被认为很重要的人。而且,更进一步,我将论述所有和我正在探讨的话题相关的事物——尤其是将全部有形的人造物品包括在内——把它们作为人们一起合作制造的产品。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就是他们如何协调行动,以制造出相应的成果。
2.“比较”的观念。要对一个个案有所发现,你可以研究在很多方面与其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另一个个案。将两个或更多的这种个案放在一起,可以让你看到相同的现象——集体活动的同一种形式,同一个进程——在不同的地方如何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那些不同取决于什么,以及它们的结果如何有所不同。
3.“进程”的观念。即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逐步发生的,首先这个,然后那个,并且它从来不会停下来。所以,我们解释时所采用的终点只是一个我们选择停止研究的地方,而并非天然就是终点(参见Becker,Faulkner和Kirshenblatt-Gimblett,2005)。社会学分析包含了逐步地发现谁做了什么,他们如何达到他们的活动所要求的协调,以及他们的集体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
我用我在帕洛阿尔托的自由时间做了大部分基础研究,这后来就成了《艺术界》。我的研究采用两种形式——细读和个人经验。在我对艺术品如何制造所进行的观察和我对这些观察的思考之间,我进行了来回往复的斟酌(我就是这样思考理论的)。再次重申,引导我的最重要的基本观念是:艺术在某方面来说是集体性的;艺术品产生于一种进程;并且,“比较”将是我的研究核心,我总是将这种艺术形式和那种艺术形式进行比较,将这种做事方式和那种做事方式进行比较,我期待这种“比较”可以显示出研究对象的一些重要特征。
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钢琴演奏者。我曾在酒吧、夜总会和脱衣舞娱乐场所演奏。这些经历以及其他艺术经历使我意识到,艺术品是通过很多迥然不同的人的协作活动网络才成为它们最终的样子的。凭借这些经历,我的直觉告诉我,研究这种网络和活动将是探索艺术的一条大有可为之路。尽管如此,我想我仍然需要一些新的经历去思考。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所知甚少的是视觉艺术——我画画笨手笨脚,这从小学起就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参见Becker,1998,132—138)——因此,我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参加了摄影课,一种不需要画画的视觉艺术。我完全参与到摄影之中,并且学校把我介绍到当时非常活跃的旧金山湾区摄影界。对我而言,摄影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在其中,我可以探索我关于艺术界的想法。我由此对这个我日日栖居的世界产生的了解,可以说对那些我原本没有的问题和已有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
静心回首,一切历历在目。当时,在冲洗底片的暗室中,我学到了摄影家如何依赖他们(和我)从摄影器材店里买来的材料。一开始,我在爱克发公司出品的纸上学习制作摄影照片,这种纸非常讨人喜欢,名叫“神速记录”。我刚入门几个月功夫,爱克发公司就不再制造这种纸了。当我改用杜邦公司出品的“Varilour”纸时,我很快就意识到,在任何其他一种纸上冲印,都意味着要重新学习那种纸对不同的曝光和显影时间的反应。为了让我在这方面长长记性,杜邦公司也很快就不再生产“Varilour”了,我必须再次改弦易辙。(随着数字摄影的出现,所有这些难以掌握的知识都很快过时了,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当这些公司不再制造它们的产品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浑身不自在的人。很多专业人士也有相似的苦恼,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要重要得多。事实上,据我所知,很多摄影家过去经常用铂纸来冲洗照片。当铂纸不再被生产时,一些顽固分子依然使用它,但他们必须亲自制作纸张,用铂溶液对其进行光敏处理。
我也经常会利用艺术界的熟人提供的一些“数据”。我有一个朋友叫苏珊·李,她是我所在的西北大学舞蹈项目负责人,她给我讲述了舞蹈演员的故事:后台工作人员没能将舞台清理干净,将很多碎片留在上面,这导致了演员跌倒受伤。我认识一个艺术商,她偶然地告诉我一个“她的”艺术家的故事:那个艺术家将一件作品送到博物馆,但却发现作品太大了,以至于无法通过博物馆的门;又太重了,以至于博物馆的地板都无法承受其重量。
我还有很多相似的发现,我对它们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概括。好吧,在我冲印照片的经历中,我观察到了什么呢?我观察到,若艺术家习惯于使用一种独特的材料,就会对那种材料产生依赖。当那种材料断货时,例如生产商不再制造它,他们可能会使用其他一些他们并不习惯的材料,或者,他们将亲自制作已经买不到的材料。结果虽迥然不同,但摄影家不会停止工作;他们将适应这种变化。不管怎样,从我的所见所感来看,简单的功能主义是一种站不住的理论立场。它宣称,材料甲对于制造乙类型的艺术品是必需的,因此,如果甲不复存在,也就不再可能制造乙,乙将停止存在。尽管对这种理论的修正只是在措辞上稍有不同,但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材料甲不存在时,艺术家要么亲自制作它,要么找别人制作它,或者不再使用它。如果他不再使用它,艺术品就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换句话说,它并非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
这种理论结果在最大限度上成立。它并非只适合于一些特定的、归根到底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摄影冲印所需要的纸。原则上,这种结果可以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成立,即使对整体的社会也一样。功能主义一直都很想对这个现象进行归纳概括。因此,当被认作社会其他组成部分之基础的家庭形式彻底瓦解或者完全改变时,会发生什么呢?社会将会消失吗?一种严肃的功能主义或显或隐地会做出这样的预测。我认为,在铂纸基础上的摄影冲印方面成立的理论,在此也同样成立——你可以说,社会将失去以家庭为必要条件的存在形式,但是社会不会消失。它将有所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消失。
除了间或进行这种参与观察,我也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我对艺术最早的理论思考就来自社会学之外的一些领域的成果。一种随意、散漫的阅读让我受益匪浅。我从一些关于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的书中发现,它们包含的观念正好和我的理论立场相吻合。莱昂纳多·梅耶(Leonard Meyer,1956)的《音乐中的情感和意义》使用了“惯例”的观念——一种人造的,但人们普遍赞同的(我们后来称这是“社会建构的”)做事方式——去分析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使用惯常的曲调、和声和节奏来创造情感的紧张和放松,由此创造出音乐的意义。梅耶的同事,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1968)展示了在一首诗歌之中,诗人是如何相似地使用惯常手法来暗示诗歌何时结束。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60)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史大家,他曾分析画家如何使用惯常技法来呈现“真实的”树木、人物和其他物体[威廉·艾文斯(1953)做过类似的事,他曾对蚀刻和雕版艺术的技法进行过分析,我也熟读了这本书]。
“惯例”,正如这些学者所用的,指的是创作艺术的人与阅读、聆听或观看艺术的人所共有的观看之道和聆听之道,任何参与其中的人都对此了若指掌,因此这为他们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当我看到某些学者和我所论的如出一辙时——“集体行动”和“惯例”是同一回事——我就知道我可以将他们已经进行的细致研究作为我的原始材料。这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如果可以夸大来说的话,我自有一套理论来引导自己阅读。田野工作者们都知道,“抱怨”是研究组织活动的极好材料。为什么?因为组织包含了(这就是我的理论了)互动的惯常方式,每一个参与的人都知道这种做事方式。参与者将这些方式看作天经地义——它们就是我在研究艺术时所称的“惯例”——如果其他人并不这么行动,他们就会心烦意乱,牢骚满腹。他们的“抱怨”清楚地表明了在这里哪种“做事方式”被视为天经地义。毕竟,这是一个社会学家想要知道的。
由这种小理论引导着,我的阅读开始转向,变成了一种田野工作。我开始寻找原始的(或者“更加原始的”)数据。我的原理是:社会生活是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原理的引导下,我开始寻找相关的材料。那些材料告诉了我,帮助制造艺术品的人是谁——不论他们采用何种方式出手帮助。我尤其注意寻找自传材料——那些艺术的参与者写的关于艺术的书——特别是那些充满了对于组织和同行的“抱怨”的书。这些书唾手可得,几乎所有关于艺术的书中都充满了这样的材料:好莱坞的作曲家抱怨制片人,他们委托作曲家制作电影配乐,但却对音乐一无所知,并且老是提出一些天方夜谭的要求(Faulkner,1983);画家抱怨难以找到需要的材料,或者抱怨收藏家和画廊主人没有支付他们觉得作品应值的价钱(Moulin,1967);出版商抱怨作者对他们的书修改起来没完没了,而作者则抱怨出版商没有大力宣传推销他们的书。
其他的著作研究了那些在“真正”的艺术品创作中通常被认为处于辅助地位的人的活动。文学分析家萨瑟兰(Sutherand,1976)表明,出版人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的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电影记者哈默茨(Harmetz,1977)系统地探究了每个对制作《绿野仙踪》有功劳的人的贡献——制作服装的女裁缝,扮演小矮人的小个子们,尤其还有像为电影配乐的作曲家一样的核心人物。她的研究表明,作曲家不仅提供了电影具有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该负责此事的导演被数次更换),而且也提出了拍摄前半段电影的一个重要想法:故事开始时发生在堪萨斯州,内容用黑白胶片拍摄。当多萝西到达奥兹仙境之后,电影就变成了彩色片。
我仅仅是在收集奇闻轶事以使我枯燥的理论“趣味盎然”吗?绝非如此。在此,我将解释我当时采用的基本方法。现在,我仍会通过这类经验事例来发展我的观念。
就艺术来说(这对我想思考的任何对象都是一样的),我首先列出休斯所说的人物角色名单,即所有那些合乎道理地(或者甚至是看似没有道理地)被认为对我想分析的事件或对象(电影、小说、音乐或戏剧或舞蹈表演)做出贡献的人。在这里,尤其重要的就是不被习俗之见所蒙蔽。后台工作人员是创造芭蕾舞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吗?售票员和停车场服务员是吗?依我之见,很多人会认为将这些人加入重要的参与者名单并不合理。但是,没有他们,演出就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我将他们包含在内。(一般而言,最完整的名单是电影最后的致谢名单。)
制出我的名单之后,正如早先所述,我就开始寻找“麻烦”。这个方法也并不合乎惯例。很多分析家会认为,困难和麻烦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绝不会认为这对于理解一件艺术品甚为关键,甚至,在他们看来,这还不是一件值得调查的好事。但我把它们放在中心。我的假定是,通过这么做,我可以找到使艺术成为可能的基本合作形式。
随后,我就遵循着另外两个我已描述过的核心观念:进程和比较。我会描述自己是如何利用在帕洛阿尔托学习摄影的那段经历的,以此我会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讨论。那段经历塑造了我对视觉艺术品的性质的理解,以及对其他各种类型的艺术品的性质的理解。
一般而言,摄影家拍摄的照片比他们实际采用的照片数量要多得多。在我学习制作照片时,数码摄影还没有发明,摄影家会拍摄成卷的胶片;用35mm照相机(大部分摄影家用这个)的人,经常会使用每卷可以曝光三十六张的胶卷。他们通常会对同一个物体、地点、人物或事件进行多次拍摄。在极端情况下,摄影家可能会使用安装电动装置的相机(尤其是在拍摄体育赛事时),对同一个事件以极快的速度曝光很多次。在使胶片显影后,他们制作出人们所称的“印样”或“校样”,以此展示三十六张曝光的胶片。这为他们查看已完成的作品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
大部分摄影家认为,这个阶段的查看,即他们在关于同一事物或相似事物的很多照片中进行甄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将会决定,他们想要很多相似照片之中的哪一张。无论是人物及其表情,还是实物,哪一张的光线或框架或布局最能传达摄影家当下决定传达的东西。这个决策的进程,摄影家们称为“编辑”,这产生了下一个进程的原始材料。下一个进程就是从选择的底片中制作照片。
当我了解到更多的摄影知识时,我知道了冲印也包含很多相似的微小决策:你选择在对比度多大的纸张上冲印,你将纸张放在放大机的光线中感光多久,以及你将纸张放在显影液中多久——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最后照片中的差异。最终,这些差异将会很大,形成看起来迥然不同的形象,具有截然不同的意味和感染力。因此,我最初对于进程理论的信奉在此可以得到证实,它以如此清晰的方式展现在摄影家的工作中。
不要认为,我只需要了解这件关于摄影的事,就可以得出进程所扮演的角色。相反,请将我刚刚的所述作为一个隐喻,喻指我所了解的所有类型的艺术中数以百计的类似事件的总和。在这里,“比较”这种操作就登台亮相了。
在摄影家投身的编辑进程中,核心部分是选择。在关键时刻摄影家做出选择,排除了大量的照片。这会影响最终的作品。这种选择的进程会继续下去。影响最终图像的并非只有一个选择,而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选择。好吧,我心里想,让我们假定一种相似的选择进程也以相似的方式影响了其他艺术客体和事件吧。由此,随着我的阅读和非正式调查的继续,对我而言,研究的问题就变成了:对一件作品而言,谁做出了什么选择?这产生了什么效果?
另一本书对我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瑟兰(J.A.Sutherland,1976)记载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出版人和作者的关系,诸如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以及托马斯·哈代和他们的著作出版人的关系。萨瑟兰对出版公司的档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表明,出版人对他们出版的作品的介入既广泛又重要。他们建议对情节和语言进行修改,坚持采用可以卖给当时无处不在的图书租赁店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版式,并且以其他很多方式影响了他们所出版图书的内容和风格。
萨瑟兰提供的事例告诉我,在公认的艺术家之外,其他很多人都包含在编辑进程中,做出了有助于形成最终作品的选择,他们的功劳不可小觑。将此记在心里,我继续进行比较的操作。更多的例子并不难找:电影剪辑人员和给电影配乐的作曲家,画廊主和博物馆馆长,文学编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最终,我将好莱坞电影结尾的致谢名单看成我所谈论的制作艺术的合作网络的最佳象征。
比较包括两个方面:在两种事物之间首先寻找共同之处,而后寻找差异之处。这两种分析性的操作都很重要。就编辑进程而言,相似之处在于选择的观念,在于看到艺术品并非简单地一蹴而就,而是每次构造一部分,以此制造出每一部分,并使其各就其位。但是,找到相似之处就会立刻诱使人们寻找潜在的差异之处。在事例之间寻找差异——比如说,在摄影和写小说之间——产生了进程的不同形式,引入了不同的参与者,强调了不同的步骤。对摄影家来说,制作作品的物理进程更明显,所有包含的选择看上去都在他们的手中完成;就小说家而言,他们通常会写出一部手稿,它的副本由其他人用不同的机械设备和不同的生产进程制造(并非说作者对其物理效果就不会抱怨!)。比较的这两个向度对调查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敞开了以后研究要走的新路。
写作像《艺术界》这样的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进程。开始时,我并未计划写一本关于艺术的书。我只是想探索我的直觉,即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看看这将会有何收获。当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时,我开始在一个班上讲授艺术社会学,当时,这个话题还不像现在这样常见。无论是在我的阅读中,还是在我对自身经历的沉思中,对于吸引我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我每周都会进行讲授,这就形成了一个大纲,一个话题的框架。出于吸引学生的需要,我精心准备了可以在班上讲述的小故事:一个在洛杉矶建造华兹塔的人的故事使学生们都着了迷,并且成为关于特立独行者及其艺术的那一章的萌芽。
随着我对这种事例的收集、比较和讲授,我发展出一种框架,将它们以一种条理分明的次序组织起来。这时,我开始构思文章,论述进程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我写这些文章,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告诉我它们想被写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响应我接到的邀请:去这里进行演讲,去那里参加会议,为一本书或杂志写一篇文章。每一个邀请看上去都是一种召唤,召唤我做一些应做之事,尽管我并没义务去做其中任何一件事。
数年之后,我积累了七八篇文章,它们论述的是我现在看作一种统一理论的不同方面。我将写就的文章铺在地板上看:哪里还有疏漏,我应该写些什么去将其填补起来。这也是一次视觉的发现,不亚于其理性思考的成分。
最终,我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对任何作者来说,它都可能是最难回答的:我何时写完?这项研究完成了吗?这本书完成了吗?我怎么知道?难道不是总还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吗?(参见Becker,Faulker和Kirshenblatt-Gimblett,2005)
对《艺术界》来说,我并不需要担心是否做了足够的访谈或者观察。我的数据和事例只要可以涵盖足够多的情境和艺术形式,以至于我可以觉得,我并没有遗漏任何可以使我的分析框架更为复杂的东西就行了。复杂性是我所追求的,概括性则不是。或者,更准确的说,我所概括的将是什么是可能的,在一次对艺术活动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什么将是值得寻找的。所以,大体上,我仅需要决定何时完满收工即可。
我是这么解决这个难题的: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作品论述了艺术作为集体活动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进程。在这进程之中,写一本书只是一个阶段,而并非最终阶段。更确切地说,这本书是一系列工作的进展报告,这些工作还将延续下去。我的概括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毕竟是暂时的,正如所有的科学结论也不可避免地是暂时的(参见Latour,1987)。
所以,我从没有打算提供一种关于艺术理论(Theory of Art)的无所不包的论述。大写字母意味着统一、完整和确定。这从不是我对理论的看法。对我而言,理论是或多或少连贯一致的一套观念。当我对一个话题展开研究时,理论会告诉我应该去寻找什么。这正是我期待《艺术界》能够提供给我和读过这本书并觉得这种观念值得探究的人的。在库恩(Kuhn,1970)的意义上,这本书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持续产生有研究价值的观念。这么说最为合适。
这项科研一直没停过。直到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究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观念。但是,正如本书中的观念所表明的,它同样包含着其他人的功劳。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英雄般的思想家的故事:他在与世隔绝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图景,并且让其开花结果。这种浪漫主义的事情并未发生。当我写《艺术界》时,我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已在这里提到一些我曾参考过的作者;也有和我谈得来的积极投身制作艺术品的人,其中一些人我以学生或者共事者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合作过。
我并非想向求知若渴的研究者们介绍,当他们的作品完成时,他们会学到一门新的语言,找到新的同行,他们会进行更多的研究。相反,从我自身经历总结出的体会是,我们永远不会彻底完工,而只是偶尔停下来告诉我们的同行,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
编辑/韩世容